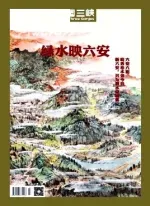松滋:将船买酒白云边
文/周 兵 编辑/柳向阳 摄影/肖佳法
南湖秋水夜无烟,耐可乘流直上天。
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
乡音俚语的松滋人,对于古诗似乎没有特别的偏爱,但不知道这首诗的松滋人不多。诗末虚无飘渺的“白云边”三个字眼,让每一个松滋人陶醉其间。
松滋城关有一青峰山,面向千里江汉平原,背靠莽莽十万大山。
青峰山上白云边,青峰山下松滋河。站在松滋河边,回望白云起处,无法不令人生发幽思古意。“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三峡与江陵之间,就是长江边的松滋。一条悠悠的松滋河道,李白曾经扁舟散发,御风漂泊而过。可去洞庭,可下江陵,两条水道虽分道扬镳,但李白经过松滋似乎是铁定的事实,不然他怎么会替松滋写下白云诗句呢?
我站着的松滋河边,是不是李白将船买酒的埠头?那番亦饮亦歌的风致,何其让人心驰神往。不唯我,其实很多松滋人有着同样的历史记忆。
查李白年谱,李白到过洞庭湖是肯定的,至于是否船靠松滋河则未必,而饮过当地佳酿一说则几乎是杜撰。稍微查阅一下就可以知道,李白的游湖诗歌不仅仅只有这一首白云诗,而是一气写了五首,总题为《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春潮涌动的松滋河,从来与李白无关。这是一个善意的谎言,知道底细的松滋人,谁也不忍心说破。
松滋河里找不到李白的影子又有什么关系,涨水的松滋河边,青草萋萋白雾迷迷。天气晴好时,河堤上的棚户酒肆间,满是喝着啤酒看风景的人。生活在此时此地的人们,不太关心这一河清水,从哪里流来,又向何方流去。
六山一水三分田,有山有水的松滋,应该是荆州辖区内地貌最丰富的县城。地形西高东低,山地、丘岗向江汉平原呈四级阶梯递降。西为鄂西山地,峰峦起伏、沟壑纵横;中为丘陵岗地,丘冈绵延,宽谷低丘;东为平原湖区,平展宽广,河渠纵横。一条松滋河,横卧其间,成为山丘与平原最绵长的分水线。如果松滋是一曲大乐章,松滋河该是一道多么优美的休止符啊。一定要到松滋河的历史源头看一看,不然真是愧对了这条天赐的水道。
一滴河水一滴泪,一粒河沙一粒血。不曾想,从故纸堆里爬出来时,我分明看见松滋河是一条血泪之河。
松滋东北,长江南岸边望去,冲出三峡后的汹涌江水,在平原开阔的河道忽然歇下来。裹挟着万吨流沙的水流一慢,河沙便沉积下来。长江干堤始建于东晋,距今已1600多年。千年间,沉沙一年堆过一年,江水一年高过一年,堤岸一年险过一年。世人皆知黄河有“悬河”,但荆江之堤,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大水时,在沙市的楼房上眺望江面的船舶,仿佛从屋顶上驶过一般。故当地至今仍有“船在楼上行,人在江底走”的民谣来形容江堤之险。
荆江两岸堤防之患由来已久。南宋初期,由于荆州、襄阳一带处于宋(朝)、金对峙区,数十年的战乱,使得这一带残破不堪,人口流亡,堤防更是无人顾及,年久失修的堤防汕刷残缺,防洪作用显著降低甚至基本丧失。堤坝两岸,江水冲出的穴口比比皆是。宋后期,虽经堤防加固,堵塞了众多穴口,但直至嘉靖(1522~1566年)以前,荆江两岸尚有采穴、油河、调弦、郝穴及新冲等众多穴口(也即溃口)存在,仅公安县沿江就有十数口。据历史文献记载统计,从明朝弘治十年(1497年)至清朝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的352年里,荆江大堤共溃决24次,平均15年一次。由于溃口洪水居高临下,江汉平原坦荡辽阔,淹没范围大,损失自然严重。一次水灾,三年难以恢复。所以荆江地区流行着这样的民谣:“不惧荆州干戈起,只怕荆堤一梦终。”
两岸夹江,手心手背都是肉。北岸内有大片开垦出来的垸田,有经济重镇沙市,有政治中心荆州;而南岸百万蚁民赖以生存的平原,似乎是一片片减轻对岸洪水灾害的洼地,似乎是一条条分洪入湖(洞庭湖)的水道。“舍南保北”成为堤防建设一种痛苦的抉择。于是,万历年间北岸堵塞所有穴口连成一线,而在南岸留下(是无奈还是故意)虎渡河口和调弦渡口向洞庭湖分流,清咸丰十年(1860年)石首乌林江段溃决,形成藕池分流。加上同治年间松滋黄家铺、庞家湾溃决,形成了“荆南四口”分洪泄流水道,长江之水沿之直下洞庭湖,北岸堤防压力大大减轻。

作为荆江水道中首当其冲的松滋段呢?作为“舍南保北”思想中被遗弃的一方呢?在《松滋县志》灾难一章中,我耳边是松滋堤溃口处的惊涛骇浪,是万千乡亲的灭顶之悲。
上善是水,上恶亦是水。清代以前的松滋,虽北临长江,但内陆河流本不多,除了西南山间一隅有洈河,滋润着南部松滋外,平原地区虽偶有河渠湖汊,但多是零星点缀,不成气候。盼水又怕水,在堤防落后的时代,“水利”其实与“水患”几乎是同义词。旱得太久的平原终于盼来了水,却成为一场又一场水的梦魇。南水洈河的山洪之患,虽也为害一方,而北水决口处,却是整整一个松滋平原。
自元代至元十二年(1275年)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674年间,松滋发生水灾63次,几乎每十年一次。而在清道光至光绪年间,松滋堤坝几乎每3年一次溃口。
查阅所有关于松滋河流形成的资料,都可以看见两个刺眼的年份“同治九年(1870年)”与“同治十二年(1873年)”。透过不远的历史,我清晰地看见,在千疮百孔的堤坝后面,在奔流冲突、恣意汪洋的江水面前,茫茫松滋平原几乎是一座没有设防的城池。松滋河溃口处冲刷出的东西两支河流,多像大地流下的两行泪痕。
荆江南堤首冲松滋段全长四十四公里,清乾隆以前由官府监督修护,时称“官堤”。监修官员只顾侵蚀堤费,不管堤防质量,所以自明嘉靖至民国末年,溃口三十余处。水患之故,半是天灾,半是人祸。《松滋县志》(1986年版)记载:“同治九年(1870年)农历六月中旬,黄家铺连溃两口,宽一千多米。调民夫堵筑,因工程巨、劳力少,堵筑不坚,年堵年溃,至同治十二年索性留口不塞,遂成松滋河。”
皆知黄河有“黄泛区”,斯时的松滋平原上,莫不是长达百里,横贯县境的“长泛区”?
直至民国十八年(1929年),八宝与涴市显示不出带的行政名称分别为“泽国西乡”与“泽国东乡”。“泽国”该是血泪铭成的地名吧。
据县志记载,黄家铺溃口后,占长江水量13%左右的江水倾泻而下,贯流整个县境东部平原,形成河槽四十多条。那时的松滋河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河流,而是一条又一条泄洪水道。历多年江洪与山洪泛滥,泥沙连年淀淤,地面一般升高二米左右。高处形成淤田,低处沦为湖泊。松滋平原第一大湖泊王家大湖形成于清咸丰十年一场洪水,第二大湖泊小南海形成于清同治九年洪水,第三大湖泊庆寿寺湖形成于清同治九年洪水……



洪水一年一度,我不清楚满堰满垱的松滋平原上,万千乡亲是如何度过一场又一场灭顶之灾的。贪婪与无能的官府,永远不是百姓的指望。四十多条河槽就该有四十多条堤坝,那该是多么繁重的修防工程啊。虽然在光绪二十六年之后的三年,长江忽然安静地歇了整整三年,给抢着修堤围垸的百姓留了一点喘息之机。但合计几百公里的堤防建设之艰巨可想而知,民间修堤中各垸之间的利益纠纷可想而知。于是,滨湖与滨河农田依然是看天下田,看水吃饭。长江稍有风吹草动,平原湖区农田便随水漫淹,俗称“寸水淹百亩”。洪水过后,依旧是四处乞讨的万千黎民。
合堤,锁住黄家铺溃口形成的两大主要支流,成为锁住四处肆虐的洪水之患的唯一选择。所有的记载中,我仍然没有发现官府的任何作为。绵长的松滋两大河道的堤坝,依然是百姓募捐修筑起的“民堤”。
松滋河西支堤。经大口、新江口至窑沟子,总长55.12公里,除原大口以上12公里旧堤修于清乾隆年间外,均由民间集资修成于光绪末年。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因内河淤沙堆高,在沈玉山等倡导下,上自庙冲河口、下至窑沟子,修筑顺河大堤。因人少工程巨,资费难筹,沈自出稻谷五十石,垛棚招夫,包修而成。1936年,在佘銮卿主持下,加固西永寺至老嘴堤防三点三公里。1942年,废马尖至打鼓台的德胜垸南堤,沿河筑堤至青峰山下。
松滋河东支堤。1912年,由大同垸士绅张暑林、张阔夫倡修,三年修竣。上自新场接官堤,经沙道观至黄家隔抵公安县。1955年县域调整,终点缩至米积台文昌宫,长30.45公里。
如果说松滋河是一条天赐水道,那么它付出的代价过于沉重了。相对于古老的长江来说,松滋河太年轻了,那段沉重的记忆太新鲜了,可即使是如此接近的疼痛,又有多少松滋人口述心传地铭记下来呢?连我这个徒劳的伤痕复原者,也写得如此平静而优雅。历史就是这样,我们把苦难剔除,只留下一些浪漫而美好的追思与凭吊。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记忆,苦难记不住,功德记不住,我们都是健忘的后人。有惊无险的1998年6月洪水,让我们这一代人算是稍微理解了江水高悬的含义。而在那一年的6月16日,洪水一次又一次超过历史记录时,我的孩子在松滋人民医院刚刚出生。
离九八洪水整整十个年头时,离黄家铺决口有了138年了。2008年的清明节,松滋河堤上,没有一个祭奠的松滋后人。实验小学组织了春游,我10岁的孩子与她的同学们一起,在河岸沙滩上快乐地放风筝。
——松滋礼俗——毛把烟、砂罐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