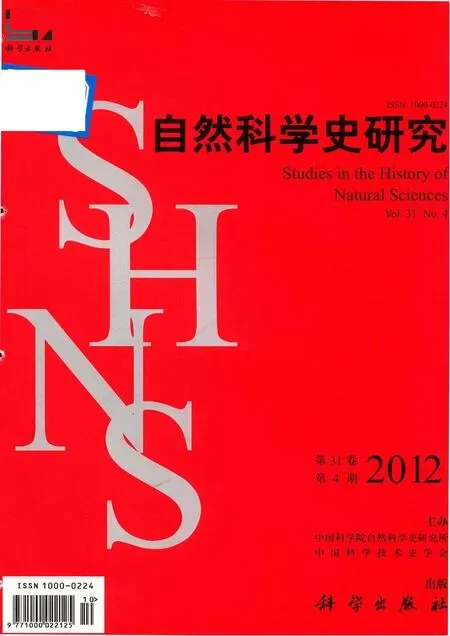冶塘考
黄学超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9),中国的冶铁业继续发展,冶铁技术也产生了一些革新,这些都颇受重视,自不待言。然而,这个时期关于冶铁的史料并不多,使相关史事略显模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不过,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深入挖掘和缀联,或许尚可对这一时期冶铁业和冶铁技术的发展得出一些新认识。本文从对《宋书·百官志》记载的冶塘冶的讨论入手,来阐明这一设想。
《宋书·百官志》载:
卫尉……晋江右掌冶铸,领冶令三十九,户五千三百五十。冶皆在江北,而江南唯有梅根及冶塘二冶,皆属扬州,不属卫尉。[1]
可见,梅根冶与冶塘冶为晋代江南大冶,具有比较重要的地位,理应受到重视。前人对梅根冶的研究成果颇有所见①相关研究如裘士京:《“梅根冶”考辩》,《东南文化》1990年第1、2合期;杨国宜、裘士京:《丹阳铜、梅根冶、永丰监考》,《文物研究》,第六辑,黄山书社,1990年;裘士京:《江南铜研究》,第四篇“六朝隋唐五代时期梅根冶及相关问题研究”,黄山书社,2004年;裘士京:《古代铸钱中心“梅根冶”在池州考》,《学术界》2011年第4期。,而对冶塘冶的说明,多仅在讲述六朝江南经济发展时一笔带过,未见对此冶本身的深入研究②裘士京《江南铜研究》中辟有“长江中游铜冶中心——冶塘考”一节,对冶塘冶进行了考证。然此节以冶塘为铜冶,不确,对冶塘地望之考证亦显粗疏,故本文不多加讨论。。通过对相关史料的寻绎与分析,笔者发现,冶塘冶的形态、地望、运作原理、兴废时间等,均仍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兹分别考述如下。
1 冶塘的含义及地望
《宋书·百官志》所谓冶塘,实为冶令之职号。笔者以为,晋宋时期,“冶塘”本是一种呈湖塘形态的特殊冶铁场所,由于诸冶塘的集中,它们所组成的矿冶群遂以“冶塘”为名,从而形成了为冶塘冶令所管辖的“冶塘冶”。今试说之。
《水经·江水注》(以下简称《江水注》)载:
(武口)南直武洲,洲南对杨桂水口,江水南出也,通金女、大文、桃班三冶,吴旧屯所在,荆州界尽此。……江水右得樊口,庾仲雍《江记》云:谷里袁口,江津南入,历樊山上下三百里,通新兴、马头二冶。①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35“江水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903~2911页。按此本“马头(頭)”作“马愿(願)”,而各本《水经注疏》俱作“马头”(如台湾中华书局1971年影印本《杨熊合撰水经注疏》第4244页,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所出版《杨守敬集》中所收录的点校本《水经注疏》第2118页),知系排印之误。今径引作“马头”。
又,《太平御览》引《武昌记》云:
北济湖本是新兴冶塘湖,元嘉初发水冶。水冶者,以水排冶。令颜茂以塘数破坏,难为功力,茂因废水冶,以人鼓排,谓之步冶。湖日因破坏,不复修治,冬月则涸。[2]
《武昌记》系六朝地记,所载当是武昌一郡之地理,则此“新兴冶塘湖”必在武昌郡境内。《晋书·地理志》载,武昌郡鄂县“有新兴、马头铁官”[3],正可与此新兴冶塘湖相对应。而新兴、马头铁官之目又恰与上文《江水注》所载新兴、马头二冶相合,是知郦注所载之新兴冶,即《武昌记》之新兴冶塘湖,当是一个通过兴修塘堰而形成的人工湖。由于《江水注》中对五冶的记载,笔法完全相同,使用“通”字颇有表示水流相通之意,故不难推知这五冶均是这样的“冶塘湖”形态。换言之,正如新兴冶可以称作“新兴冶塘湖”一样,马头冶也可称作“马头冶塘湖”,余可类推。由此可知,上述冶塘湖实际上是一种筑塘成湖以为铁冶的形态。
新兴、马头二冶显在江南,但《宋书·百官志》又言西晋时“江南仅有梅根、冶塘二冶”,不见新兴、马头之名,其中必有缘故。由于新兴、马头二冶均有冶塘湖之名,则冶塘冶或即兼指二冶。据《江水注》知,金女等三冶与新兴、马头二冶相距亦当不远,存在时期也相同,则很可能冶塘冶实是诸冶塘湖的总称,如此乃可合理解释上述史料表面上的矛盾。欲证此说,尚须从地望方面予以查考。
《太平寰宇记》(以下简称《寰宇记》)鄂州江夏县条下云:
冶唐山,在县东南二十六里。《旧记》云:“先是晋、宋之时,依山置冶,故以为名。”[4]
“冶唐山”即“冶塘山”,当因冶获名,知此冶名冶塘,即《宋书·百官志》之冶塘冶。冶唐山在北宋江夏县(今武汉市武昌)东南,则冶塘冶亦当在此。而根据《江水注》的记载,新兴等五冶塘湖亦在此处附近,为《江水注》作疏的杨守敬即将注文所载金女、大文、桃班三冶与《寰宇记》此条所载之冶塘冶联系上[5]。按,据郦注载,金女等三冶在杨桂水流域,而杨桂水大致在今武汉市东北的长江南岸。此水名后世不见,依地势推测,约可与今青山港相当。则金女等三冶或即在今青山港所沟通之东湖湖区一带。同治《江夏县志》见有“治塘渡在县东三十里”的记载[6],此“治塘”应为“冶塘”的误写或讹变,据里数,知此渡当在今东湖的东南湖面,可为之证。至于新兴、马头两冶,则当在今高桥河—樊港(古樊口水)流域。嘉庆《大清一统志》云,“新兴冶,在大冶县西”[7],当有所本,且亦与郦注所载相符,则新兴冶或即在今大冶市属樊港流域,临近拥有悠久开采历史的铁山铁矿的还地桥镇一带。至于马头冶,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载,“武昌南百八十里”处,有马迹山,[8]以里数准之,是山当在今大冶市金牛镇迤南一带。此处旧时为武昌县马迹乡,应即以马迹山为名。此乡宋代已见①宋人薛季宣《上诸司论金牛置尉札子》一文中有“本县(武昌县)金牛、马迹、灵溪、贤庾、符石五乡,在本县南”(薛季宣:《薛季宣集·札状·上诸司论金牛置尉札子》,卷26,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339页)之语,可以知之。,稍加上溯,很有可能即《元和郡县图志》所载唐开元年间武昌县所属之鄂州的三十三乡之一②《元和郡县图志·鄂州》载:“开元户一万九千一百九十,乡三十三”(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27,中华书局,1983 年,第643 页)。。可见“马迹”之名,由来甚早。按,“迹(蹟)”与“头(頭)”形极似,“马迹”地名又存在于可能为马头冶所在的樊口水上游,故不妨推测“马迹”实为“马头”之形变,马头冶正位于马迹山下的旧马迹乡所在,即今金牛镇境内。据《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之《黄石市市区、大冶市文物图》,金牛镇境内遍布年代不详的冶铁遗址[9],是为此说又添一证。

图1 金女、大文、桃班、新兴、马头五冶塘湖分布略图
五冶塘湖的地望大致可知(图1),则可回过头来看《寰宇记》对冶唐山的记载。今东湖南侧有马鞍山,方位、道里与《寰宇记》所载之冶唐山均合,由于东湖水面即金女等三冶塘湖旧址,而马鞍山临之,符合“依山置冶”的情况,故以之当冶唐山殆无疑问。又,同治《江夏县志》载,“冶湖桥在县东南四十五里”([6],99页),冶湖桥应亦因冶塘湖得名,其所在地并不能与上述任何一个冶塘湖相对应。所以,此处当亦曾存在一个与上述五冶规模相近、性质相同的冶塘湖,并且同样为冶塘冶令所管辖。此冶正在今马鞍山南麓,可知冶唐山实为冶塘所包围,很好地诠释了《寰宇记》“依山置冶,因以为名”之载。需要附带说明的是,由于这一地区铁矿储量丰富,故除以上所举之外,当时可能还存在其他冶塘,同为冶塘冶的组成部分,惜已不可具考。
由上可知,诸冶塘生产方式相同,规模不大,分布集中,统设一冶令管辖是合理的。“冶塘”一名,既能够体现诸冶的形态,也是诸冶的通名,具有很强的概括性,故临近诸冶之山、诸冶所组成的矿冶群和统辖诸冶的冶令皆因之而获名,可谓顺理成章。
2 冶塘运作原理
冶塘冶因冶塘而获称,那么,时人于此地冶铁,为何要采取这种形式?冶塘的运作原理又究竟如何?笔者在此试为一解。
《武昌记》中明载,筑塘成湖以为冶的冶铁形式称作水冶,“水冶者,以水排冶”。明确为史籍所载的水排始见于东汉初年,其工作形式是“冶铸者为排以吹炭”,“激水以鼓之”[10],实际上即一种应用机械轮轴的水力鼓风机[11]。水排的发明为铁的冶炼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其技术获得推广,并且出现了不同的应用形态。三国时韩暨“因长流为水排”[12],是凭依天然河道应用水排的例子;而筑塘成湖以为冶,则是人工改造水流应用水排的例证。
杨宽先生认为,冶塘湖“是利用低洼之地筑塘而形成的”,实际上是一种小规模水库,其兴修目的是“为了要构成一个水流集中的落差”,从而“使水流从上游高度的水位骤然落下,以激动水力工作机(水排)的水轮”([11],115页)。这是目前所见对冶塘运作原理的主要论述,也是其对冶塘之所以兴于此时此地的解释。然而,这一地区地势总体平坦,虽然不乏丘陵,但是分布比较零散,并不是蓄水制造高差的理想地形。上文所考得的诸冶塘湖所在地势低洼、地形开放,筑塘蓄水所得到的高度落差确实有限。故笔者以为,时人选择兴修冶塘湖的形式来进行冶铁生产,当另有原因。
由于铁矿产于山中,而山中河流水量小、分布稀疏,因此在山中铁产地直接运用水排进行大规模冶炼十分困难。相反,河流出山交汇,水量增大,水力容易利用。不过当地已距铁矿产地较远,欲采用水排方式生产,只得将铁矿石从山中运出,至水流量大处,方可“因长流为水排”,进行冶炼生产。然而这种方式费时费力,产量也受限,制约了水排的大规模应用,进而制约了冶铁业的发展。面对这样的局面,若在合适的所在修筑塘堰,蓄水成湖,使湖水达于山麓,便可凭借湖水较大的水量在山麓中使用水排冶铁。这样,湖水所临的山中铁矿均得近便之利,水排数量增加,生产效率提高,规模增大。上文考得的诸冶塘湖皆在山下,且多有两、三面临山者,尤其是在推定的马头冶附近,有许多冶铁遗址,这些冶铁遗址大致呈环状排列,多处于山麓地带,中间地形平坦([9],上册,128~129页)。这种地形和分布方式正印证了上文的推测,是冶塘冶铁的直接反映。可见,利用冶塘进行冶铁在当时此地具有极大的便利性,这也当是时人大规模修筑冶塘进行冶铁生产的真正原因。
3 冶塘冶铁的兴废
上文所举史料,颇有提及诸冶塘存在时间者,然其兴废始末尚未明晰,仍应专门加以讨论。
据上引《晋书·地理志》文知,新兴冶西晋已见,故《武昌记》所云“元嘉初发水冶”,不能用来作为新兴冶始发于南朝宋的证据,而应重新讨论。笔者以为,此“发水冶”可能是指重新修缮、扩大生产规模而言,也可能是“废水冶”之讹。退一步说,即使《晋书·地理志》所载有误,新兴冶始兴于南朝宋,但至迟于西晋之时已经出现冶塘,形成冶塘冶,断无疑问。
《宋书·百官志》云:“江南诸郡县有铁者或置冶令,或置丞,多是吴所置。”([1],卷39,1232页)据此,冶塘冶似当始作于吴,然尚不能遽断,当结合其他史料进一步考定。《宋书·百官志》又载西晋江北三十九冶皆属卫尉,而江南仅有的梅根、冶塘二冶“皆属扬州,不属卫尉”,为判断二冶始作时代提供了线索。基于此条记载,笔者试作一推论:西晋建立之时,更定制度,卫尉辖冶令之制盖定于此时。然而此时晋、吴隔江相峙,晋自不可能在江南置冶,故卫尉所辖冶令皆在江北。晋灭吴后,江南铁冶始为晋所有,为了统治的便利,晋政府不将江南铁冶归予卫尉,而让设于吴故都的扬州来管辖江南铁冶,以因循旧制,维持稳定。这一推论可以合理地解释《宋书·百官志》对江南二冶归属的记载。由此不难看出,梅根、冶塘二冶应是吴旧冶,冶塘的开发可上溯至孙吴时。《太平御览》引陶弘景《刀剑录》有“吴主孙权黄武五年采武昌山铜铁,作(十)〔千〕口剑、万口刀”([2],卷343,1578页)的记载,可知孙吴时这一地区冶铁业已十分发达,亦可为孙吴已作冶塘的一个旁证,而黄武五年(公元226),或正可视为冶塘冶的始作之年。
冶塘冶归晋二十余年,即发生永嘉之乱。此后,晋室南迁,“江北诸冶大都遭到破坏而遭废弃,而江南的梅根、冶塘两冶乃显得尤为重要”[13]。参以《寰宇记》“晋、宋之时,依山设冶”的记载,不难判断东晋至南朝宋时是冶塘冶铁最为兴盛的时期。《江水注》中见载的五冶塘湖,体现的当即东晋的情况,①《江水注》载新兴、马头二冶文字系引庾仲雍《江记》文,而载金女、大文、桃班三冶文字与之相类,颇疑亦本《江记》之文字。庾仲雍当为东晋或晋宋之际人(鲍远航:《庾仲雍〈湘州记〉考证与辑补》,《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所作《江记》约可断为记载东晋情状。其规模可见一斑。尽管如此,冶塘冶的重要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东晋末年,会稽王僚佐王弘向当权的会稽王司马道子进言,认为天下诸冶浪费人力财帛,建议“留铜官大冶及都邑小冶各一所……余者罢之”([1],卷42,1311页)。铜官大冶即梅根冶,而冶塘冶未在建议保留之列。虽然此议似未实行,冶塘冶应未被真正罢废,但其地位下降,已是明显的事实。
《武昌记》成书当在南朝宋①杨守敬据《武昌记》佚文断作者史荃(筌)为南朝宋人(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914页)。,则依其载,至迟在宋元嘉后不久,新兴冶塘湖就已经废弃。新兴冶如此,与之邻近的诸冶的情形当亦相类。而南朝宋之后,也的确未再见冶塘冶的记载。因此,不妨将冶塘冶铁的年代下限定于南朝宋时。②《武昌记》虽言冶塘湖废弃后当地仍有“步冶”的情况,但其规模显然不会很大,而且已非“冶塘”旧貌,且恐亦未能持久,故此处不作讨论。
冶塘冶之所以能够在此时此地兴起,有其独特的原因。首先,这一地区铁矿产量丰富,且有悠久的采矿传统,这是矿藏方面的先决条件。其次,利用水排鼓风冶铁之法已经发展有年,生产经验的积累和提高生产效率的迫切需求,促使人们因地制宜地利用这一地区丰沛的水利资源和独特的地形,发展了冶塘冶铁之法。再次,武昌一度成为孙吴政权的政治中心,政治地位的提高加快了区域经济的开发,在这种情况下,冶铁业趋于繁荣也是理所应当的。
两晋时期,冶塘生产能够维持一定的规模,应当归因于吴时大规模生产的延续及永嘉之乱使南方矿冶事业日趋发展。及至晋末,冶塘地位转而下降,至刘宋时最终废弃,应也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此时距吴已远,旧修冶塘的逐渐荒圮在所难免,新修及维护冶塘的难度亦随之增大,若《武昌记》所载的因“塘数破坏,难为功力”的现象应多有所见,致使冶塘的存在条件恶化。其次,随着时代变迁,地理环境难免有所更易,而铁矿储量有限,有可能面临着局部枯竭的状况,这就导致了冶塘存在价值的下降。再次,晋末以降,南方政权内部叛乱频仍,叛乱势力屡屡盘踞物资丰饶的荆州地区,与建康中央政权抗衡。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权自然不希望荆州地区经济实力过于强大,加上战争本身对经济生产的破坏,冶塘的衰落也就难以避免了。
4 余论
经由本文之考察可知,“冶塘”一词具多层含义,其义项之间又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孙吴时期,冶塘在武昌附近出现,是利用水排鼓风冶铁之法因地制宜的表现形式。基于此,这一带出现了许多冶塘湖,组成了兴盛一时的冶塘冶。冶塘冶在六朝前期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但在南朝宋以后逐渐废弃,兴修冶塘进行冶铁生产之风当亦随之衰落。
本文对“冶塘”的考述,尚有可发之余义,兹略举数端而言之。
《宋书·百官志》载西晋冶铁管理制度:“汉有铁官,晋置令,掌工徒鼓铸,隶卫尉。”([1],卷39,1232页)似晋代已以冶令取代汉旧之铁官,为地方冶铁管理机构。然前引《晋书·地理志》又有“新兴、马头铁官”之载,显然,“铁官”这一机构,并未完全被废弃。由前考新兴、马头诸冶为冶塘冶令所辖,不难得出这样的一个解释:此处的冶令、铁官实为两级地方冶铁管理机构,各具体的冶铁地点置铁官,而相邻之数铁官统辖于一冶令。按,西晋时江南置冶令数与江北颇悬殊,与吴时南方冶铁充分发展的状况似不协调。冶令之制始于吴(见上引《宋书·百官志》),入晋以后江南两冶令又不属卫尉,而属扬州管理。种种迹象表明,这种冶令—铁官的管理形式可能是孙吴旧制,为西晋所沿袭,仅在江南孙吴故地推行。若然,则可知西晋江南地区完整的冶铁管理层级应为扬州—冶令—铁官,亦可知西晋江南的冶铁管理模式悉因孙吴旧制,而基于这两点又可以进一步推测,孙吴时期诸冶令应统归中央某机构管理,旧说“估计冶令、丞分属地方州郡”[14]实值得重新讨论。
水排在中国冶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它的研究亦素为学者所重视。然诸家对水排的讨论,多集中在“水排”这一装置本身的外形复原、工作原理等方面,而较少对水排工作的另一要素——“水排”之“水”的形态进行讨论。本文对“筑塘成湖以为冶”这一水排应用方式的解析,当可使水排在古代冶铁事业中的应用得到更加完整的认识与了解,在此基础上,或亦可为水排的发明提供一些新的线索。世以水排为东汉初年杜诗在南阳太守任上所发明,然华觉明先生通过辨析史料,认为“杜诗是水排的倡导者,水排的发明很有可能是在他任南阳太守之前”[15],亦言之成理。按,今安徽怀宁有冶塘湖汉代冶铁遗址,与《汉书·地理志》所载“睆有铁官”[16]可相对应,该遗址的主要部分略呈弧形,“为长约2公里,宽200多米的狭长地带”[17]。无论是“冶塘湖”的名称还是冶铁遗址分布形态,都与前考冶塘诸冶一致。由于时代有异、距离太远,这一“冶塘湖”不会是本文所讨论的冶塘冶的组成部分,但是在生产技术上,却很可能与冶塘诸冶相同。若是,则至迟在西汉晚期,与后世之冶塘相类的铁冶形式便已出现。据理度之,这一形式的出现当是采用水排鼓风法冶铁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若此,则水排的发明可能更早,或在西汉前中期。据此,笔者试对水排的早期应用及其发展作一推测:由于水排的应用对周围地理环境要求较高,故其发明初期可能只在南方的局部地区缓慢发展而不广为人知,经由杜诗、韩暨等人的提倡,①杜诗任南阳太守之前,曾任职于汝南郡,而汝南郡与睆县所属的庐江郡相邻,杜诗或即于此时了解水排冶铁技术;韩暨为南阳人,对杜诗在南阳所倡的水排技术自当比较熟悉。水排鼓风法北传,更多地表现为“因长流为水排”的形式,而南方旧有的冶塘形式也应仍有传承,至孙吴时终于被大规模采用。这样的推测,不唯与前人所持先秦时期南方少数民族已经开发使用水能机械之说[18]相符合,亦与春秋战国时南方首先发展冶铁技术([11],37页)、且鼓风技术发展较快(如鼓风竖炉的发明)②Wagner D B,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Part 11:Ferrous Metallurgy.Needham J.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Vol.V,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2008,pp.107.转引自梅建军:《〈中国科学技术史〉“钢铁冶金”分册述评》,《中国科技史杂志》,2011年第1期。的研究成果相呼应。
东湖为今武汉市东郊最大湖泊,其形成与演变也素为人所关注。一般认为,东湖为一壅塞湖,“成湖时代当在自然堤和黄褐色黏土形成之后,应是全新世初期形成的”[19]。此说对东湖形成时间的判断,虽可称允当,然仍显模糊,缺乏对东湖形成过程的进一步研究。由于金女、大文、桃班三冶皆存在于今东湖湖区,其筑塘成湖的行为必是对原有环境的改造。所以可以说,三冶的兴废是东湖形成、演变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东湖湖岸曲折,塘堰修于湖中并不难为,如此则可以使水面扩大,水量稳定,以达到兴水冶的目的。据之逆推,则三冶兴修之前,东湖恐未如后世之广袤,水量亦不够稳定。据此言之,三冶的兴修使古东湖水面扩张,应无疑义,而三冶废弃之后,东湖湖岸线退缩与否亦是一值得探讨的问题。由是,历史时期东湖的盈缩就有了更多可以讨论的空间,这无疑对江汉平原湖群的研究也有一定助益。
1 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230.
2 李昉.太平御览[M].卷833.北京:中华书局,1960.3717.
3 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458.
4 乐史.太平寰宇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2278.
5 郦道元.水经注疏[M].杨守敬,熊会贞,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2903.
6 王庭桢,彭崧毓.江夏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93.
7 穆彰阿.大清一统志[M].第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52.
8 王象之.舆地纪胜[M].卷81.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2802.
9 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M].上册.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2.128~129.
10 范晔.后汉书[M].卷31.北京:中华书局,1965.1094.
11 杨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06.
12 陈寿.三国志[M].卷23.北京:中华书局,1971.677.
13 邹逸麟.中国历史人文地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278.
14 马志冰.魏晋南北朝盐铁管理制度述论[J].史学月刊,1992,(1):15~21.
15 华觉明.中国古代金属技术[M].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329.
16 班固.汉书[M].卷28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1569.
17 裘士京.江南铜研究[M].合肥:黄山书社,2004.214.
18 吴曙光,赵玉燕.我国最早开发利用水力能源的地域、时间和民族考[J].广西民族研究,2002,(1):94~102.
19 蔡述明,官子和.武汉东湖湖泊地质(第四纪)研究[J].海洋与湖沼,1979,(4):383~3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