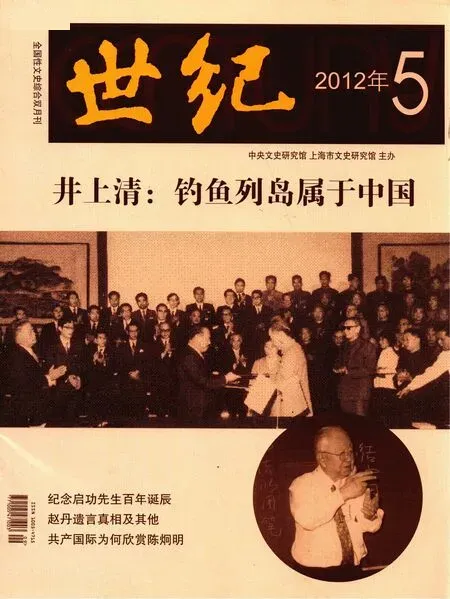心香一瓣
袁行霈
今年7月26日是中央文史研究馆第六任馆长、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启功先生百岁冥诞。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今天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纪念座谈会,共同回忆我们的老馆长为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以及他作为中央文史研究馆的一面旗帜,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启功先生经历了民国建立、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国内革命战争、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是在这个历史大转折时期出现的不可多得的学者、诗人和艺术家。他上承清末民初的传统,在学术和艺术两方面取得独特的成就,在教书和育人两方面都有楷模意义。启先生的影响不限于生前,也不限于今天,还会延续到将来。七年前他的逝世在社会各界和国内外所引起的震悼,充分证明了他卓越的地位。而七年来他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不论谁讲学术史,都不能不讲到他;不论谁讲艺术史,都不能不讲到他;不论谁讲教育史,都不能不讲到他。他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也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启先生首先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学问的博大精深,令人叹为观止。他的学术领域涉及中国的文学史、艺术史、历史学、语言学、文字学、佛学、民俗学、敦煌学、文物鉴定学等许多学科。而对清朝典章制度之熟悉、对书画碑帖鉴定之精湛,堪称独步当代。他熟谙古典文献,其学问既来自各种典籍,也来自他本人的见闻和实践,所以他的学问是活的学问,已经化到他的生活之中。在启先生那里,人即学问,学问即人,一言,一笑,一举手,一投足,莫不透露着学问的真谛。
启先生作为书法家的地位是公认的,他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书坛的领袖和旗帜。他的书法有深厚的传统根柢,他目验的古代书法精品既多,且有深入的研究,又自出机杼,戛戛独造,法度严整,满纸生辉,形成典雅与遒劲相结合的独特风格,如千仞之高岗,又如云中之白鹤;如霜下之松柏,又如拈花之少女,其外形可效而得其仿佛,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则难以企及也。
启先生的诗作,无疑是诗歌史上的创新,无论是题材还是语言,都别具一格。他说唐诗是喊出来的,宋诗是想出来的,我看他的诗是流出来的,随手拈来,皆成妙趣。他的诗中多有深刻的人生体悟,可见其豁达的胸襟和悲悯的情怀,这是最为动人之处。他曾将自己的诗集称为“俚语”,其实是十分高雅的,是放下了身段的高人与雅士之作。一味的高雅固然不易,而俚俗的外表与高雅的天骨融而为一更难。明代高启《独庵集序》曰:“诗之要,有曰格、曰意、曰趣而已。格以辨其体,意以达其情,趣以臻其妙也。”启先生的诗可谓格、意、趣三者具备,其格高、其意深、其趣真,实在不可多得。
我还要称启先生为教育家,他有独特的教学方式,那是浸润式的,像春雨一样润物细无声的循循善诱。他既授人以知识,又启人以智慧;既教人治学,又教人立身。“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两句话不仅成为北师大的校训,也是一切做教师的人应当遵守的准则。

2001年10月,中央文史研究馆建馆五十周年暨全国文史研究馆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朱镕基总理亲切会见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并作热情洋溢的讲话。图为朱镕基总理与中央文史研究馆启功馆长(左)、袁行霈副馆长(右)一起步入人民大会堂(刘建波摄)
启先生一生坎坷,幼年孤露,青年失学,中年遭难,直到文革结束进入老年后才得到施展才能的机会,可惜又患上颈椎病、高血压、心脏病、黄斑病变、前列腺炎,百病缠身,几无宁日。但他坚韧地忍受着各种苦难,笑对人生,泰然处之,时时处处以其特有的诙谐为别人带来快乐。他有菩萨的心肠、深邃的目光、严正的态度和看破红尘的笑容,可敬亦复可爱,可畏亦复可亲。他的言谈有时是饱经沧桑的警策,有时是儿童般的天真与调皮,有洞见,有禅机,有诙谐,有诗意,只需跟他一席谈话,便永难忘却。
1999年启功先生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同时我被聘为副馆长。在就任之际的馆员会上,他说自己“何德何能,获此殊荣”,而我更是深感惭愧。启先生受到馆员们的爱戴,声望很高。他带领馆员们做了一些在当时的条件下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作为他的副手,遇事辄向他请示,遵照他的意思办理,出差前后都向他汇报。虽然我早在1978年就到小乘巷他的寓所拜访过他,并得到他所赐绘画,但我不敢多打搅他,只是把他的著作一部部找来拜读,从中汲取知识和智慧。从1999年开始到他逝世一共六年,是我跟他接触最多的一段时间。我向他说:我不敢自称是您的入室弟子,但现在有机会向您好好学习了。的确,六年近距离的接触好比跟他读了“研究生”,专业的学习不多,但如何做人,处处以他为榜样。人们都知道他的和气,只有近距离接触过他的人才知道和气后面的刚正。刚正,这在今天是多么难得的品德啊!
可惜启先生没有活到期颐之年,否则7月26日将是为他祝寿的日子,现在只能从心底祝祷他在天之灵得大自在。言不尽意,上面这番话,难免肤浅,希望诸位能从中感受到一点我对启先生的崇敬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