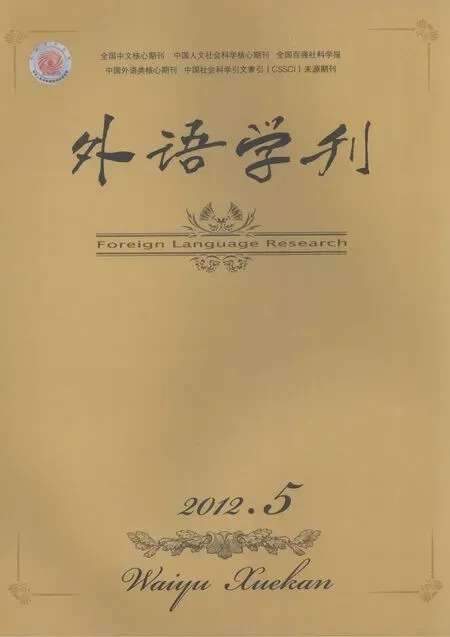隐喻性语言中的生态观及隐喻性思维语用能力的培养(1)*
王松鹤 周 华
(黑龙江大学,哈尔滨 150080;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 150001)
隐喻性语言中的生态观及隐喻性思维语用能力的培养(1)*
王松鹤 周 华
(黑龙江大学,哈尔滨 150080;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 150001)
人类进入21世纪之后,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危机,迫在眉睫的环境和生态危机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人类的言与行,从而改变我们对环境和生态的固有的认识,建立新的、科学的环境观和生态观。本文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分析隐喻性语言中所折射出的不同时期人们对环境和生态的认知观、人们的行为方式以及该思维和行为方式对生态环境所产生的影响。
认知语言学;母亲;生态;环境
1 引言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和基础。自然生态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人类的健康发展。自从19世纪工业革命以来,新的科学技术使人类如虎添翼。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人们对自然进行肆意的破坏和疯狂的掠夺。其后果是生态环境退化和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其表现为:土地沙漠化、能源枯竭、河流污染、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古人云:“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即自然因素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有明显的地域性,而人为因素(如环境污染)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则没有国界。由此给人类带来的天人之间以及人际之间的极度紧张关系是难以想象的。生态危机的后果是毁灭性的,包括地球和地球上所有的生命。
在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不断恶化的今天,解析生态危机的根源,拯救人类共同的家园——地球,已经成为很多学科关注的焦点。如生态科学、自然生态学、文化生态学、生态文学、生态翻译学、生态伦理学、生态哲学、生态语言学等。
2 “言”与“思”与“行”
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不是简单的独白,它涉及内在意识和外在世界的关系,建立在人类共同行为方式的基础上”(曾繁仁 2006:235)。洪堡特在18世纪末提出,“一种语言就是一种世界观,只有通过语言,才能形成世界观。上世纪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认为,语言不仅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而且语言也是思想的塑造者,语言决定着一个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而且,每种文化成员的世界观都被限制在他们的语言框架内”(刘润南 2012:41)。萨丕尔说过:语言作为一种结构,其内里是思维模式。杜威认为,“人类的心理存在与语言密切相关……语言能用无数的方法把记录社会结果和预示社会前景的意义凝缩起来”(贾媛媛 2012:14-15)。马克思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以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而且随时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马克思 2000:50-51)。“这种内在的尺度就是人的心理需求,在人类创造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分析这种内在的尺度和心理是全面理解生态伦理演变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易小明 赵永刚 2011:103-106)
按照Lakoff 和 Johnson的认知语言学的观点,人类在建立概念系统的过程中,以自己为中心,把自己的体验引申到其他事物上,把源于人类身体的空间范畴投射到其他范畴上,从而对其他事物进行分类和描述(Lakoff & Johnson 1980)。这样我们的世界才有了秩序,我们的文化基因才能不断地繁衍下去。作为我们体验最早、最深的母爱,我们自然会把它引申并投射到其他目标域上。例如,母亲河(江河流域的人们对养育自己或与自己密切相关的河流的亲切称呼)、母树 (采伐后保留下来拨撒种子的大树)、母校 (指自己曾从那里毕业或在那里学习过的学校)、母语(本民族的语言,一般是第一语言,即一个人最初学会的语言);mother country(one’s native country),mother ship(ship from which smaller ships get supplies),Failure is the mother of success,Necessity is the mother of invention. 在上例中,人们把“母亲”域里的“赋予生命、给予、事情最初发生的地方”等意义投射到了目标域上——树、校、船、河。人们说,母亲是第一所学校,我们从母亲身上获得了应对生活的基本知识。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而挫折、失败正是我们的加油站,就像我们跌倒后,母亲轻轻地把我们扶起,然后鼓励我们继续上路一样。
可见,人类对自然、概念、思维和语言的看法必然要打上人的烙印,正如马克思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自然界视为“人化的自然界”(humanized nature),即世界当为人眼中的世界。我们顺着这一思路完全可将语言视为“人化的语言”(humanized language)(王寅 2012:6)。所以,我们对世界的认知、理解和反应,都可以在人类的语言中找到印迹。道家把万事万物的规律统称为“道”。那么,依靠什么办法才能认知得“道”呢?“魏晋学者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对‘道’的载体——‘言’的理解。 ‘道’整合在圣人之言中,体现在器化的文字记载里……把握‘道’必须有赖于‘言’的充实,而‘道’体现于具体事物中的样式,亦与‘言’的论说有着不可分的关系。由于‘言’与‘道’的相通,使‘言’获得了与‘道’在哲学探讨上同等重要的地位。”(袁立莉 2012)
既然“言”与“道”与“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本文将在认知语言学的框架中,分析隐喻性语言中折射出的不同时期人们的生态观、行为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生态反应。
3 隐喻性语言中折射出的生态观
对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来说,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母亲都是我们的第一所学校。我们把对母亲的种种认知以隐喻的方式构造出对世界认识的基石,因此形成了以下的认知模式。
3.1 “母亲”体认模式
在北美印地安人的传说里,象征着光明的太阳神和象征着黑暗与罪恶的狼兄弟用他们母亲的身体创造了世界万物:他们的母亲在生下他们的时候就死去了。格鲁斯卡普用他母亲的身体来造成了太阳和月亮,走兽和鱼群以及人类。而那心怀恶意的马尔库姆造出了山谷、蛇和一切他认为可以使人类不方便的东西。
埃及神话则说,女神努特造成了苍穹,笼罩着地神塞勃(男性)。塞勃躺在努特下面,而努特在东边地平线处踮着脚尖站着,在西边地平线处弯下身去,伸出双臂,用手指尖支撑着身体。在黑暗中可以看见星星在她身体上闪耀,也在她伟大的、不知疲倦的四肢上闪耀。
在瑶族祭神仪式的各种神唱里也有许多记载:头便是天,脚是地,儿孙正在腹中心……
这些传说所表现的显意似乎仅仅是对宇宙起源、万物由来的解释,而其隐意乃是表现了人类深层心理结构中的对人体式的大地的符号化动机,一种使大地人体化的欲望(耿占春 1993:66-69)。可以说,通过这种模式,我们可以在自身中找到大自然的种种事物,也可以在大自然中找到我们身上的各个部件:“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受命于天也……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哀乐喜怒,神气之类也……故人之身,象天容也;发,象星辰也;耳目戾戾,象日月也;鼻口呼吸,象风气也;胸中达和,象神明也;腹饱实虚,象百物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人副天教》)
古代中医学著作《黄庭内景》和《内经》都为我们在人体内部和人体自身上描绘了一幅包揽宇宙的自然景观,展示了人体构造与宇宙的同态对应性。《内经》把人的机体与日月星宿、季节变迁、江河大地等各类自然事物和现象,看做一个同构同质和同源性的“整体”,它们具有统一的运动节奏和生命律动。空间的基本结构是五方,时间的基本结构是五季,大地的基本构件是五行,人的基本构件是五脏,这是世界的基本框架,构成了一个人与宇宙的辨证关系的符号模型。在这个世界图式中,天体运行,万物兴衰,气象变化,人体气血循环,五运六气以及五脏五官五情五色五味五音五方……相互之间存在着横向与纵向的关联。这个人体式的宇宙的符号模型所作的分类,不仅是表象上的,而且是结构与功能上的类比。比如:阴阳诸经而合之十二月、十二辰、十二节、十二经水、十二时。十二经脉者,此五脏六腑之所以应天道(耿占春 1993:77-79)。
由此可见,人体式的宇宙是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中基本的、潜藏的隐喻,或者说,正是这个原始的隐喻启迪了一种完整的智慧。这种隐喻在西方思想中可上溯到阿尔克莽与毕达哥拉斯派。阿尔克莽医生认为,人是一个小宇宙,是大宇宙的缩影;人体是世界构造的反映,人的灵魂是数的和谐。大地的4种元素:土、水、气、火;人体的4种体液:胆液质、血液质、粘液质和黑胆质,当这些元素处于自然的平衡状态时,人才能健康,生态环境才能良性地循环发展。
这是一种使自然和人联系起来的“母亲体认模式”。这种模式就像脐带把胎儿和母亲连接起来一样,它把我们人类和自然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凭借这种模式,人类得以辨认环境,认知宇宙,对自然界有了初步的认识,从而不断地认识自身和周围的世界,不断地揭示自身和宇宙的奥秘。这种模式体现的是人与自然混为一体的、朴素的、原始的生态观。
3.2 “母亲”给予模式
“母亲体认模式”——这一隐喻形式的生态观随着时代的不同,有其不同的变体和内涵。在“母亲体认模式”的认知观中,自然被表现为一种博大、富饶、神秘、包容的母体形象。这时,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和谐的、生死相恋的关系。然而,从16世纪以来,“自然从一个有灵的存在变成了象征的存在,从一个滔滔不绝的言说主体变成了沉默无语的客体……理性将自然打入沉默和工具理性的深渊”(Glotfelty & Fromm 1996:17)。“人是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正是这唯一主体的谬见使得人类狂妄自大,唯我独尊,凌驾于自然之上。”(石海毓 2012:80)这种否认大自然的内在价值,仅把其当作工具盲目使用的现象,有人认为是笛卡尔主客二分造成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后果。在普鲁姆伍德看来,现在的生态危机实质上是“理智的危机,更准确地说,是理智文化的危机”(Plumwood 2002:5)。它带来对自然生态不可逆转的、空前的损害。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泱泱大国,而且以农为主。她的发祥地被认为是黄河。她的风貌、她的历史、她的辉煌、她的品质,都在下面的诗里以儿女对母亲述说的方式表现出来。 黄河——我的母亲河……你用你甘美而丰富的乳汁哟,哺育着你的无数的儿女,任他们尽情地吮吸哟。你轻声地为他们唱着那甜美的摇篮曲,你伸出你温柔的臂膀哟,搂抱着你的儿女,任他们在你的怀中撒娇、嬉戏哟。你用身体为他们挡风遮雨,是你给了他们美好的心灵哟,是你给了他们健美的身体,你又给了他们肥沃的土地哟,你又给了他们许多、许多。你为儿女们累弯了腰哟,你为他们操劳了那么多、那么久……(http://flydragon.ccnt.com.cn/post.php?rid=3105)
这首诗首先对目标域进行了描写,然后以对称或非对称方式将源域映射到目标域上,形成语篇之间的整体互动。从语言层面上看,这首诗里隐喻的工作机制是:
源域目标域
母亲 —————————— 黄河
乳汁 —————————— 黄河水
母亲唱的摇篮曲 ————— 大自然的声音
母亲温柔的臂膀 ————— 大自然的呵护
母亲辛勤的付出 ————— 大自然无私的给予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个隐喻,且通篇都由隐喻连接而成。显而易见,它的整体结构和内涵都是古老隐喻模式——“母亲体认模式”的延伸。但从思维、文化和社会机理层面上看,它的隐喻意义又有了新的时代气息。第一,解放以后,人民当家做了主人,为了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人们开始了“敢叫日月换新装”的运动。当时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人们冲天的干劲和对新中国的热爱反映在语言里就是:“五岳在你面前没有了风采哟,昆仑山在你面前低下了高傲的头……”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一直高唱着“地大物博”的歌,不断地向大自然母亲索取:我们把山地改成梯田;毁林建房、建地;捕杀野生动物;乱排污物、废气……就像小孩子认为他的母亲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一样,我们在博大的母亲的胸怀里“尽情地吮吸”,以至于“你为儿女们累弯了腰”。
在中国古老的男权文化社会里,妇女/母亲就是贤顺、宽容、无私奉贤的符号。他们为儿女可以付出一切,却从不需要回报。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他们的这种态度使得人们常常忽略了她们的感受和需求。这种潜意识的文化构式,反映在我们对待大自然母亲身上,就是我们需要:“你轻声地为他们唱着那甜美的摇篮曲,你伸出你温柔的臂膀哟,搂抱着你的儿女,任他们在你的怀中撒娇、嬉戏哟,你用身体为他们挡风遮雨;是你给了他们美好的心灵哟,是你给了他们健美的身体,你又给了他们肥沃的土地哟,你又给了他们许多、许多。”就是无限制地索取,哪怕母亲伤痕累累。 这首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人和自然之间的模式——“母亲给予模式”。这种模式体现的是人类的贪婪、欲望的无限;反映出唯我独尊、人类中心的生态观。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语言是人给经验世界做的一套符号外衣,透过这套外衣,我们可以了解人如何构建概念系统、如何处理自身和外界的关系。客观世界决定了我们的语言构式,而语言决定了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和不能够看到什么、做了什么以及所产生的后果。
3.3 保护“母亲”模式
当人们改造自然、重整环境的欲望无限制地膨胀时,呈现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紧张的对立关系(王宁 2005:18)。这时的自然暴躁不安,以种种方式来与人类抗衡。今年中国的洪水和美国多个州的干旱就是最好的证明。
面对生态危机,人们开始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否合理,人对自然的行为是否妥当。有人认为,生态危机是人的价值观的危机。美国文化史学家、生态思想家托马斯·柏励提出了生态纪(Ecozoic Era)学说。他认为,解决自然生态平衡的最好的办法是人类要有与自然协作的精神。
随着人类的进步,环境的恶化,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古老的“母亲体认模式”又有了新意。
此时,我正躺在地球母亲的怀里,聆听着她熟悉的心跳。地球母亲用柔和的春风抚摸着我,她的笑容阳光灿烂。我想可能是今天地球母亲看到她的儿女们正在读懂她,尊敬她,这是她少有的笑容。
我一直在为我们向地球母亲无休止地索取而不安,为我们对地球母亲的种种不孝而自责……更残忍的是,我们把自私欲望的双手又伸向了自己的动物同胞们:扒了动物同胞的皮,吃了动物同胞的肉……我们还乱扔塑料废物毁坏地球母亲的面容,制造有害气体熏黑地球母亲的皮肤,砍伐森林资源裸露地球母亲的身体,排放化学污水浸染地球母亲的血液……
一向健康的地球母亲生病了,一场大病:断流、干旱、沙尘暴、大洪水、台风、泥石流……让地球母亲弱不禁风。她的病是不孝的我们给她带来的,当我们无数次听到地球母亲的呻吟或看到地球母亲的痛苦时,我们开始疾呼,我们开始心虚,我们开始收回欲望的双手,我们开始医治地球母亲的创伤……(http://www.vastman.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9072)
这同样是一篇以隐喻编织而成的文本。从语言层面上看,该语篇是一个层层推进映射模式。语块之间的整体互动体现为个体映射关系的层层推进,在这些个体的映射关系中,有一个映射关系——源域“人类”和目标域“大自然”之间的关系,统领着其他的映射关系,使整个语篇环环相扣,一气呵成。它们的映射机制是:

从思维、文化和社会机理层面上看,它反映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和旧有文化体系的转型。在古代的男权社会里,女人一直是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工具,是忍辱负重、弱小的化身。到了近代,虽然一再强调男女平等,但旧的习俗的烙印仍然根深蒂固。妇女的价值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妇女的权益不能得到应有的保护,妇女的呐喊不能得到广泛的重视。
但随着世界范围内人文思潮的涌动,人们更关注个体与个体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原本在传统文化中是对立的元素,如男人与女人、父母与孩子、个人与集体、人与自然等都被人们以一种新的视角和模式来重新审视和界定。这样就出现了上面的文本以及和该文本里类似的词语、概念、观念和行为。
我们重新审视女人/母亲,在向她索取的同时,我们尽量去读懂她,理解她,爱护她。我们不仅要她作我们的保护神,我们也要作她的捍卫者。我们曾与母亲是一体,我们现在仍然血脉相连。我们未来的发展建构在母亲给我们搭建的温暖的家庭的基础上,没有了这个平台,我们的发展将举步为艰。
我们把自身对生母博大的爱的体验和感悟投射到自然母亲身上,就产生了我们对过去人与自然对立行为的悔悟,对过去人类中心论行为的反思,因而我们要忏悔以得到内心的宽慰和平静,我们要行动以便使错误得到尽快的纠正和弥补。这是“母亲体认模式”的新形式——“母亲保护模式”,这是人与自然新的隐喻连接方式。它反映了人类尊重自然、爱护自然、保护自然以及与自然平等相处的后现代生态观。
“母亲”一词是语言大家庭中极为普通的一个词,但它却像我们肌体里的DNA一样,昭示了我们的过去,叙说着现在,预示着未来。
从对上述隐喻性语言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对自然生态保护意识的觉醒和提高。
4 结束语
语言是一种特殊实在,其本身是一种特殊在者/是者。通过研究语言,我们揭示人及人的世界,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发现人性、发展人性和完善人性(李洪儒 2011:3)。在研究隐喻性语言中,我们去寻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氛围里人们的心理要素,以反映人与自然的互动和联系。从本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出,由于人类对自然的过度索取,人与自然本应该有的天人合一的联系,有时出现了裂痕,这种裂痕持续的产生和扩展就会导致生态危机。如何让人类本能的“母与子——大地与人类”这种亲密关系重新被连接起来,使人类回归自然,从而使人类在拯救自然的过程中,回归人类的自然本性……即使人类回归自然、保护自然成为一种心理本能的反应(刘春伟 王子彦 吕雨竹 2012:92-93),这是语言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从我们的语言中剔除有负面影响的言语,如“人是万物的主宰”,生成有环保意识的话语,如广告语,“我们不生产水,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使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的意识在一言一行中深入人心,以培养人自觉的生态意识。“自觉的生态意识可以唤起人类的生态良知,使更多的人看到人类的不良行为对自然的伤害,拒绝对自然征服和占有的欲望,放弃对物质享受的过分追求,甚至放弃人的主体性,赋予自然以主体性,为人与自然的和解做出努力”(石海毓 2012:80 ),“做一位放眼全球的生态世界公民”(Heise 2008:60)。
从一个索取无度的主人到一个与自然平等相处的朋友,这是人类生态意识的深刻觉醒,也是一次人类角色的巨大转变。在这场生与死的意识变革中,语言将扮演着先行者的身份。
曾繁仁. 人与自然: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美学与文学[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6.
耿占春. 隐喻[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
贾媛媛. 面向生活的语言[J]. 外语学刊, 2012(3).
李洪儒. 中国语言哲学的发展之路——语言哲学理论建构之一[J] . 外语学刊, 2011(6).
刘春伟 王子彦 吕雨竹. 论生态文本解读的心理学途径[J] .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2(2).
刘润南. 再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J]. 山东外语教学,2012(2).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0.
石海毓. 生态文学的现实价值[J]. 山东外语教学,2012(2).
王 宁. 文学的环境伦理学:生态批评的意义[J]. 外国文学研究, 2005(1)。
王 寅. 中国后语哲与体验人本观[J]. 外语学刊, 2012(4).
易小明 赵永刚. 主义制度与正义制度[J]. 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4).
袁立莉. 宇宙本体论构成魏晋语言哲学的理论基石[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4-16-B01。
Heise, U.K. Sense of Place and Sense of Planet: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of the Global[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Glotfelty, C. & H. Fromm. The Ecocriticism Reader[M]. Georgi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Lakoff, G. and Johnson, M.MetaphorsWeLiveBy[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0.
Plumwood, Val. Environmental Culture: The Ecological Crisis of Reason[M]. London: London Routledge, 2002.
【责任编辑郑 丹】
EcologicalViewsReflectedintheMetaphoricalLanguageandtheCultivationofSemanticCompetenceinMetaphoricalThinking(1)
Wang Song-he Zhou Hua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01, China)
After entering the 21thcentury, human beings are facing all kinds of crises, of which environmental and ecological crises are so imminent that we human beings are constrained to revalue our own language and actions. Thus, we can change our old thoughts about environment and ecology, and establish new concepts and new attitudes toward n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people’s outlooks on ec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reflected in their use of metaphorical language, their behavior and the effects caused by their thoughts and behavior upon nature.
cognitive linguistics; mother; ecology; environment
H0-06
A
1000-0100(2012)05-0093-5
*本文系黑龙江省高等学校教改工程项目“中国大学生英语语用能力习得的实证研究”(JG2012010197)的阶段性成果。
2011-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