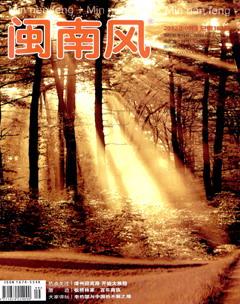不张扬的卡佛
陈再见
美国作家卡佛,如果不是小说让他名声大噪,他绝对是一个让人厌恶的倒霉鬼,出身贫寒,早婚早育,还酗酒、抽烟、破产、众叛亲离,五十岁就死于肺癌,草草结束了人生旅途。好在他还喜欢写作,留下了六十五个短篇小说。正是这六十多个小說,让他的生命不至于如他的生活那般潦倒、无望,他最终因小说而获得了另一层生命的意义。
我曾想象,卡佛生前一定是一个自卑的人,他甚至羞于谈及自己的作品,即使小说出版了,并还获了奖,他也不觉它们有多好,更别说后来还被文学界评价为一代文学典范了。他太过于平常,也知足,小说让他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里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对此他颇为感恩,把酗了多年的酒也戒掉了,大有改头换面之意,却不料多年抽烟留下的疾患还是要了他打算重头再来的小命。任何一个见过卡佛的人都会说:他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不但是卡佛本人不了不起,他的作品,其实也并不“宏大”。它们篇幅都很短,长则上万,短则一两千,然后就剩下更为精短的诗歌了。他没有写出过宏篇大著,没有创新文本,所谓的“简约主义”,不仅非他原创(有海明威在先),而且据卡佛的说法:他是“无时不刻不担心自己身下的椅子随时都会被人移走”,是生活的不稳定,让他无法静下心来写大东西,只能写短篇小说和诗歌,一气呵成,最多也就分两次写完。如此艰辛的写作状态,放在任何人身上,似乎都不能坚持多久。所以卡佛无奈地说:“有比写小说和写诗更重要的事情,明白这一点对我来说很痛苦的,但我只能接受。要把牛奶和食物放在餐桌上,要交房租,要是非得做出选择的话,我只能选择放弃写作。”显然,和生存比起来,卡佛并没有把写作看得多重要,这对于一个热爱文字的人来说,是相当残酷的。
正是如此残酷的生存现状,让卡佛的小说烙上了不一样的印记。他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的影子,或者是身边那些渺小却又顽强的底层社会小人物,比如《瑟夫的房子》里那个刚租下房子却又不得不搬家的魏斯;比如《你们为什么不跳个舞》里那个把所有家具都搬出来典卖的孤身男子;还有《马笼头》里把马笼头遗留在旅舍角落里的漂泊的一家子……他们无不来自最底层,无不经受着生活和环境的严峻考验。他们都是不被人在意的小人物,身上有着各种缺点,酗酒抽烟,在缺点的掩饰下,似乎一文不值,却又顽强的生活着。这本身就是一种生命的坚韧。卡佛看到了这种坚韧,于别人身上,也于自己的身上。他最终把所见的情景和感悟通过冷静的笔调写成了一个个短小的小说,每一个小说却都容量巨大,大千世界,可见一斑。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是卡佛的忠实粉丝,他曾这样评价卡佛的作品:不张扬。是的,当我们阅读《当我们在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和《大教堂》里面的每一个小说时,其实都有这种感觉:不张扬。卡佛写的人、写的事,都太日常了,他有些小说甚至就是直觉攫取生活中的某个场景,如实交代完毕,也不说明背景和结果,小说就那样戛然而止。那样直生生地把一个场景片段剪切下来,放在你的眼前,不作任何修饰和解释,让你去品读和感悟。如此写作,与其说是卡佛的创新,不如说是他自然的流露。
而我国近年来兴起的底层文学和打工文学,说到底,其内里和卡佛是一脉相承的。卡佛的小说,确实也值得当下我国的底层文学和打工文学作家们去借鉴、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