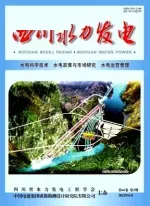走出洪水猛兽的认识误区——科学调蓄洪水解干旱缺水危局
赵鑫钰
(华电四川公司,四川 成都 610029)
1 概述
每年春夏之交,都是动植物进入生命体征旺盛期轮回的开始。天气的无常,使专业(部委、地方)防汛工作者和受益相关方高度兴奋或紧张,他们准备、忙碌、造势、放空库容,一切都是为了千秋万代、“防患于未然”?抑或履行“抗洪驱魔、消灭洪水(资源)”的神圣职责。水乃生命之源,不可缺少!既人类赖以生存最重要的资源。与其他事物一样,水也有其两面性:其温顺任人污染、摆布;其势差在没有充分引导时形成洪水,似脱缰野马、桀骜不驯!洪水是自然现象,因为人类的盲目活动招致洪水成灾。人们对水和洪水的态度大相径庭,以实用主义者的价值判断,需要时即善?不需要时则恶?恐怕相当多的认识还停留在动物般的最低需求,远没有上升到认识的应有高度。
“老子”在《道德经》中讲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於道……”。意思是:最高的“善”如水一样,水孕育万物不图回报,总是流向最低的地方,其本性就是“道”(最崇高的作为)。通俗地讲:“水以滋养和造福万物,只奉献、不索取,停在欲望(众人所弃)的最低位置,水的品德是最高的善”。
科学证实,浩瀚的宇宙中只有地球表面有水。最近,美国火星探测车“好奇”号传回的图像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面对全球普遍缺水、森林锐减、土地沙化、环境恶化、生态退化、能源紧张以及我国水问题(缺水、洪水、水污染)极为突出的现实,回归理性、重新认识水之善、命之源、水资源和水能资源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的作用,正确定位人水关系以及生存与发展的关系,善待水体、珍惜水资源、利用洪水、减少污染、开发水能,意义重大。
2 我国水资源与洪水、干旱
我国地处亚洲东部及太平洋西岸,地势总体呈现东低西高;南面临海,北接欧亚大陆,季风气候显著、四季分明。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影响,东、南部夏季炎热多雨,地表降水丰沛;西、北部受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压控制,全年大部分时间风多干燥、降雨稀少。据水文计算,全国年均降雨雪649 mm,折合水量61 889亿m3,扣除蒸发和高山冰盖不能利用,年均形成可再生淡水资源28 405亿m3。其中河川径流量27 328亿m3,地下水资源量8 226亿m3。
从全球水资源分布情况看,我国淡水资源虽然总量丰富,位列世界第六位,但因人口众多,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2 100 m3,紧位于世界第113位。由于地形、地貌、气候条件等因素影响,我国淡水资源时空和时程分布极不均衡,年内、年际间来水丰枯变化和人为因素(盲目开垦和城市化)导致水环境恶化:一方面北方地区长期干旱缺水;另一方面南方大江大河交替发生洪涝灾害。随着“温室效应”造成的全球气候变暖,“厄尔尼罗”、“拉尼娜”现象频发,加剧了降水的不均衡。
通常,水资源丰富的国家也是洪水频发的国家,我国有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辽河、松花江等七大流域,还有雅鲁藏布江、澜沧江和怒江等多条国际河流。以其宏观水势分析,北方干旱少雨,必然导致南方降雨相对增多,发生洪水的机率增大。水文资料表明,近百年来南方各流域经常或交替发生洪水。长江流域平均8~10 a发生一次大洪水、30~40 a出现一次特大洪水;如20世纪就发生3次(1931年、1954年、1998年)特大洪水,而且无论洪水的时间、密度,还是汇流总量都较19世纪前明显增大。也就是说,正是人类的不当活动加剧了洪水和缺水。史料记载:七大流域及东南沿海都是洪水的多发区,300年来七大流域曾发生数以千计的大洪水,尤其是黄河中下游洪水已导致其多次重大改道。与洪水形成共轭矛盾的是缺水,缺水的原因一方面是干旱,另一方面是水污染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人口约为5亿,60年人口净增9亿,年平均净增加1 500多万人。制度缺陷及人口政策的失误,导致盲目性、无序性、破坏性和掠夺性经济社会行为发生,使有限的资源与日俱减,自然生态不堪重负。1949年前,全国淡水资源总耗量不足1 000亿m3,进入21世纪,全国耗水总量超6 000亿m3。改革、开放后,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特别是工业化推进和城市扩张,大范围污染和工农业生产浪费严重,使干旱与淡水资源短缺的矛盾日益突出。除今年北方降水偏多外,很多地区终年缺水;不仅如此,位于长江流域的南方(云南、贵州)地区,甚至雨量丰沛的湖南、湖北、江西也频发季节性干旱缺水,局部干旱非常严重。
据统计,我国常年干旱缺水总量达700亿m3,其中农村缺水约400亿m3、城市缺水约300亿m3。为了维持生存和发展,缺水区不得不过度开发地表水、超采地下水。20世纪末,仅河北全省累计超采地下水达800亿m3、海河南系平原累计超采600多亿m3。不仅如此,北方大部分缺水区域明显出现河道干枯、湿地消失、土壤疏干、地面下沉、海水入侵、沙暴肆虐。水资源短缺,已危及到经济发展、部分地区建筑物安全以及社会的政治稳定。
3 洪涝灾害和旱灾损失
按降水分布,全年约50%的雨量集中在夏季,超70%的降雨量(来水)集中在5~9月。水资源中,总量81%的降水又集中在长江以南各流域,而此时大量的水资源却被当作“洪水猛兽”无情排弃。次年初春,又以防洪准备的名义匆忙地“腾空库容”,为各自部门或地方获取中央财政投入(建水库、修病险库)大捞好处!洪水由短时间暴雨形成,调蓄、引排不当可能形成洪涝灾害。一旦洪水致灾,人民生命财产就将遭受损失。
我国历史悠久,奴隶制、封建制时期太长,导致官员腐败、社会动荡、连年战乱、水害频繁。1949年前,由于物资匮乏、防洪设施少,人们抵御洪水的能力较弱,每次大洪水都造成人身及财产重大损失。如:黄河1843年的特大洪水;长江和淮河1931年的特大洪水;海河1939年的大洪水;珠江1915年的洪水和松花江1932年的洪水,死亡人口达数十万以上,经济损失十分惨重。建国初期,党和政府重视防洪和抗灾投入,修建了一批水库、加高了大江大河堤防,但黄河1958年的大洪水、长江1954年的特大洪水、松花江1957年、海河1963年、淮河1975年的大洪水造成的损失亦相当惨重。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实力迅速提高,各流域大江大河都建设了一批大型、以防洪为主目标的水利枢纽工程,防洪抗灾能力明显增强。20世纪90年代,南方各流域仍交替发生洪水,洪涝灾害损失高达10 000亿元(年均1 000亿元),特别是1998年长江、嫩江和松花江的特大洪水,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 500亿元。
近10年来,由于盲目推进城市化,城市扩张及房地产开发几近疯狂,大量征占农田、湖泊湿地,城市建筑新老管网不匹配,强降雨形成的涝灾损失也十分严重。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每年市政建设投资几千亿,但排水能力却只能满足一年一遇的降雨。连续数个小时的中等雨量,就能让百姓“楼上看海”。不可思议的是,几乎所有的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都在穷追猛赶、如法制“海”。当我们的人民在为经常性的洪涝灾害造成的损失“买单”之后,人民又纳税投入巨量财力修建水库等防洪设施。几十年来,水利投资逐年增加,一年投入数千亿,但全社会的洪涝灾害损失却未见减少。
除洪涝灾害造成直接、间接经济损失和每年投入的防汛物资、人力、财力外,1949~1999年间,全国已建成数十座大型水利枢纽和8万6千多座大中小型水库,总库容超过5 000亿m3。仅黄河流域就建设各类(大、中、小)水库和水利枢纽3 000多座,总库容约900亿m3,相当于黄河多年平均年径流总量的1.6倍,防洪累计投入达数千亿元人民币。另外,还建有长达数万公里的堤防和蓄滞洪区。
就在缺水地区为治理洪灾水患取得的成果欢欣鼓舞之时,多年来这些地方基本上无水可蓄。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测算,华北、黄、淮等北方地区因严重缺水每年工、农业产值损失达2 000多亿元,全国因干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5 000多亿元。以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判断,干旱、缺水造成的工农业生产、民众生活以及持续性生态恶化和由其产生的深远影响远远甚过洪涝灾害!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黄河下游多年出现断流,1997年全年持续断流竟达226 d,整个北方地区淡水资源已表现为水质型和资源型双重短缺。小浪底水利枢纽建成后,以所谓“调水调沙”稍缓断流情况,但黄河流域的缺水并没有根本改变。
推进城市化,人民还没来得及享受繁华街道、高楼大厦的兴奋和视觉冲击,缺水、断电接踵而至。全国668座大中城市中,400多座城市缺水,约110座城市严重缺水。加上工业污染、水质恶化,许多既使是沿江靠湖的城市也面临无水可用。干旱使水源枯竭、环境干化、生态全面退化,土地荒漠化,这些都逐渐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显性危机和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缺水、与水争地、水环境污染等相互作用,即将形成我国经济不可持续和社会政治失稳的重大问题。
据南京大学气候与全球变化研究院院长、中科院院士符淙斌先生的统计,20世纪是近一千年来最温暖的世纪,尤其是最近50年,全球增暖的速度是过去100年的两倍。那么,主要原因是人类活动使降雨、降雪大规模减少(干旱)所致。而且,干旱每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数千亿元。国际上许多专业研究机构以及联合国相关组织也将干旱定义为损失金钱最多的自然灾害。
4 科学蓄洪、综合利用、调洪济旱
地球上淡水资源总量基本是一个稳定值。也就是说,在一个恒长时间序列里总蒸发量应基本等于总降水量,蒸发和降水的自然循环过程即为淡水资源的形成过程。倘若总蒸发量不等于总降水量,那么,就可能出现一个情形:海洋面积不断增大或陆地面积不断增大。其实不然,既使有变化也极其缓慢。由于地貌、地势和气候变化,降雨既淡水资源的形成自然分布不均,这种失衡本身并非导致淡水资源的社会性稀缺,而是人类在试图征服大自然活动中,掠夺性的“利用”、无节制的扩张、穷凶极恶的“开发”造成。
水是生命之源,也是文明之源;更是一切物种赖以生存和人类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中,水已成为可持续发展最宝贵、最重要的资源。当今,人水关系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它反映了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其他生物种群相互依存的关系。但在全民浮躁、上下癫狂的时下,需要回归理性、重新认识和正确定位人水关系以及生存与发展的关系,深刻领悟人水和谐、人与自然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这一本质,对于构建真正的和谐社会、平安社会非常重要。
对于水的认识,从满足动物般基本需求的必要性、重要性考量,人类尚能达成共识;但对于水利与水害的转化以及水患的两个极端——洪灾和干旱,人们在不同利益驱使下缺乏统一及正确的认识。在信息泛滥和媒体“喇叭效应”的鼓噪下,有些官员及职能部门既然视洪水为猛兽、洪水成灾为诸害之首、洪水的威胁为全民族心腹之患,那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干旱使淡水资源严重奇缺、缺水导致生态恶化和经济重大损失;发生洪水时又举国上下空前紧张、巨大的防洪与抗灾投入又从未停止,为什么我们不能改变思路、寻找解决水患和水困的出路?在大江大河及生产、生活集中区域建设若干个单联或能以管、渠相互调节的水库群,使人们充分地变害为利;换句话说,就是科学调蓄洪水、综合多功能开发水资源、把季节性富裕的水或超额洪水调配到干旱、缺水地区,统筹解决洪水和干旱缺水的燃眉之急,减少淡水资源的流失和浪费。
进入21世纪,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水能资源丰富的西南诸省拟建、在建的大型水电站或水利枢纽有200多座。嘉陵江多级、金沙江(上中下游)21级、雅砻江21级、大渡河三库22级、乌江等能够参与防洪的可调节库容超过500亿m3。2010年,世界最大的防洪工程——三峡水利枢纽投入运行,总库容(高程185 m)达450亿m3,可以装278亿m3的洪水。也就是说,长江上游干、支流水库全部运行后可以消纳约1 000亿m3的洪水。1954年和1998年,长江两次世纪大洪水的总洪量都在1 300~1 500亿m3,溃堤分流洪水分别为400多亿m3和100亿 m3,“98大洪水”直到最后一刻也未启用“荆江分洪工程”,既便启用也只能分流50亿m3。从以上数据不难得出结论:只要科学调配水利枢纽和水电站库容,防洪和抗旱问题将迎刃而解。
4.1 科学蓄洪
笔者提出科学蓄洪思路的关键,就是“少弃水、早蓄水”。数百个大型水利枢纽和大库容水电站枯水期同时蓄水则无水可蓄!还会影响各电站的正常发电。几年前,三峡水利枢纽“175 m”开始蓄水时,被洪水和所谓环保弄昏头脑的官员决策于当年10月8日再蓄水,结果无水可蓄。如若坚持蓄水,下游航运无法承受。今年,经过“金钱换原则的交易”,试验性蓄水提前到9月10日;如果上游电站都运行蓄水,三峡水库仍然无水可蓄!
“少弃水、早蓄水”,并不是越早越好,而是根据中长期天气、水情预报,实时掌握来水情况,先下后上、依次开始蓄水,尽可能减少洪水期泄洪弃水。由于气象卫星云图分析和水库水文测报系统较为先进、准确,现代高科技防洪预警系统可及时发挥作用。因此,大型水利枢纽和梯级水电站的运行调度系统思路应该根本性改变,不能再按部门、行业和功能各自单独运行调度。这方面的思路,笔者几年前就向包括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领导和有关专家提出。据相关信息,水利部北京水科院王浩院士、华中科技大学张勇传院士分别牵头研究此课题。除长江流域的汉江上游和嘉陵江等西南支流在9月中可能发生较大降水外,8月底后大江大河很少出现大的来水。那么,电站群或系统性蓄水更应该提前。
4.2 综合利用
综合利用,就是在工程建设决策阶段采取多目标开发、多功能运用,充分考虑发电、生态、调水、防洪、航运等功能,尽可能控制单一目标的开发利用。众所周知,20世纪是争夺土地和为控制石油而战的世纪;21世纪则将是争夺淡水资源和控制太空及核心技术的世纪。如果说,21世纪发生大的地区冲突或战争的话,那么,很大程度上是因争夺水资源包括海洋资源引起的。人类加快了开发太空的步伐,主要是寻找适合人类生存的其他星球环境。
综合利用水资源,应该是在满足生活必需的前提下首选开发利用水能资源。因为没有任何别的能源可以取代上帝让水从自然高处向低处流动形成方便、清洁、可再生的能源。水能资源利用得当,调水解旱、防洪、航运、旅游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能源是经济和社会发展最为重要的物质条件。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广泛使用,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和经济社会的现代化,深刻改变了世界300多年来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尤其是冷战结束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加快了经济建设步伐。经济一体化与全球化,一方面带来物质的繁荣;另一方面却导致能源资源的大量消耗,使人类共同面临化石能源枯竭的压力和生态环境恶化的后果。
石油仍然是当今世界主要的能源资源。2012年,我国的石油消耗总量约5亿t,石油对外依存度近60%。“两伊”战争、美国发动的海湾战争,中日东海和钓鱼岛之争,无不是因为石油和海洋资源之争。我国是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煤炭的消耗超过能耗总量的70%。2006年,原煤生产总量约23.8亿t,2012年将达37亿t。天然气不争气,城市需求巨大,主要靠从俄罗斯联邦诸国进口。能源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更是现代文明的物质基础。而安全、可靠的能源供应和高效、清洁的能源利用,是实现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所谓“能源安全”,不仅涉及能源的资源占有、生产、储运、供给的安全,以及能源成本决定国民经济是否平稳与健康发展的安全,更涉及各国对全球能源资源的争夺以及由此引起的贸易安全、地区政治安全,甚至国家安全的问题。
水电是以水体的动能、势能和压力能通过机械转化为电能的能量资源。我国地势西高东低,水流落差较大,水能资源十分丰富。根据探查成果,我国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约7亿kW,技术可开发量为5.7亿kW,科学调度年发电量约3亿kW·h。
石油、煤炭等化石能源采一吨,少一吨,资源日益枯竭,燃烧中排放大量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温室气体;利用成本越来越高、污染越来越重。现在全球变暖、气候异常、局部持续干旱或洪水无不与此相关!
4.3 调洪济旱
调洪济旱,首先要把洪水视为资源,利用水利枢纽和梯级电站群可调节库容充分调蓄,在大型水库下游的干旱区域修建既满足水资源需要,又与江河以管、闸联通的湖、塘、库、堰;在枯水期到来之前,将其盛满,不能随意弃水。实现此目标,一个重要条件是水利系统官员应转变工作思路,水利枢纽和水电站水库的运行调度职能应该统一、协调,优先选择发电、生态、干旱缺水的调度目标,用足、用尽夏季洪水或来水。
我国的水利(防洪、抗旱)投入累计数额巨大,为什么作用发挥不够?其重要原因是政府官员和庸员太多,部门利益成为决策的首选,水利工程和防汛抗旱的水利设施产权关系不清,水资源收益和洪水、干旱受害方与其产权很少发生关系,以至于水利设施重修建、轻管护,年年投入年年修,洪旱来临难作用。水利部门借助媒体作用,夸大洪水和干旱的程度,争投资、争补助。
调洪济旱,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授设一个权威机构,协调中央水利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关系,尽可能排出因利益驱动的泄洪或调水,防止水资源的重大浪费,同时应管控职能部门和地方索要洪灾或旱灾财政拨付。据中央稽查官员介绍,这方面漏洞非常巨大。此外,调洪济旱需要受水区适当配设湖、塘、库、堰和联通管闸。这样既可以增加湿地,改善生态和人居环境,又可以开发旅游项目和经济。
5 结语
我国是人口大国,人均资源已十分匮乏,土地、淡水、石油的供给高悬着“红灯”。约14亿的人口,消费上是否要“比、超”发达的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值得商榷。我们在为啃噬上帝和祖宗留下的一点资源换得的GDP欣喜若狂时,子孙后代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正在被丧失殆尽。资源日益枯竭,能源、环境不堪需求的重负!发展面临资源等诸多制约。因此,我们应该在反思以前的发展模式的基础上珍惜资源、理性发展。
洪水和干旱是自然灾害中发生频率最高、损失最大的致灾情况。开发利用水资源,必须优先选择水资源短缺和抗旱目标及功能。水利专家林一山老先生曾动情感叹:“江水滚滚向东流,流的都是煤和油”。其实,水利的实质就是变害为利!在开发水能资源的过程中,充分实现变害为利,我们不仅要为每年不多的“超额洪水”找到出路,而且应该把所有的洪水都当作资源使其在科学调度下多发电、调水解旱、修复生态、保障航运!
笔者能够粗浅认识到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公民都应该认识到洪水的资源价值,职能部委和少数指靠洪水获得利益的相关方放弃个人或部门利益,认识到洪水的资源价值才是文献和笔者的初衷和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