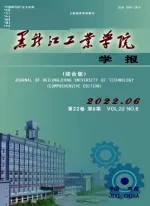初探萨义德眼中的知识分子
赵钊渠
初探萨义德眼中的知识分子
赵钊渠
作为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大师,萨义德非常关注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的群体。萨义德是接受正规西方教育的巴勒斯坦裔,这种东、西方双重身份的交织使得他更为重视知识分子应有品行,更加关注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他眼中知识分子具有独立的人格,他们具有批判意识,在公共场合代表弱势群体发出声音,他们处于流亡的隐喻状态,甘于脱离中心,处于边缘地位,是社会的边缘人和业余者,面对权势他们敢于讲真话,敢于表达自己的立场。
知识分子;责任;批判意识;流亡;业余者
后殖民主义理论大师爱德华·W·萨义德1935年出生于耶路撒冷,从出生之日起他就是个小难民,在英国占领时期,他就读于巴勒斯坦和埃及开罗的西方学校,接受的是英国式的教育。1951年萨义德随家迁入美国就读麻省高中,后分别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学位、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1963年起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讲授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萨义德既是巴勒斯坦裔的阿拉伯人,同时还是一个接受了纯正西方教育的美国人,这种东、西方身份的互相交织给予了他审视世界的特殊视角,他能够跳出传统的思维模式冷静地看待东、西方文化的关系,分析个中差异,从而有效地揭示出西方如何利用知识和文化霸权达到对东方的控制。特殊身份中隐含的张力和矛盾使他具有更宽广的人道关怀,他积极投身于巴勒斯坦的政治运动,以至被列入半打中东的死亡名单之上,同时他还批评美国的战争政策,所以他被看成是最具有争议的学院人士。
萨义德的所做所为被许多学院派人士认为是格格不入的,但究其实质却是在践行他的知识分子观。他终生致力于研究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渗透和控制,但与此同时知识分子也是一个他极为关心的论题,对这个问题他思考了二十多年。知识分子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群?他们具有什么样的人文关怀,在社会生活中他们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及他们在人类文化的发展中应该担负起什么样的责任?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萨义德亟待思考和需要解决的,1993年英国广播公司邀请他在瑞思系列演讲中发表自己的看法,借此机会萨义德集中表达了自己的知识分子观。
雷蒙·威廉斯在其著作《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中对intellectual(有知识的、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作了历史的梳理和界定,他认为“20世纪中叶以前,intellectuals,intellectualism,intelligentsia的负面意涵在英文里是很普遍的。很明显的是,这一类的用法持续至今。然而,intellectual现在通常具有中性意涵,有时候甚至用于正面的意涵——用来描述那些从事某种智力工作的人,尤其是从事一般种类的智力工作的人。”[1]在威廉斯看来,知识分子这个词本身包含有负面的意义,它给人带来的印象经常与理论、理性、冷漠、抽象等相关。当前社会上对知识分子的印象定位于“象牙塔”“一丝讥笑”等就是这种负面含义的延伸。他虽然道出了知识分子与知识的关系即从事的是与智力相关的工作,但是却忽视了知识分子所处的社会地位以及应该具有的道德责任感。萨义德在瑞思系列讲演中选择知识分子作为主题正是要克服传统思维的偏见,打破人们关于知识分子的刻板印象和化约式的类别,向大众清晰地呈现出知识分子的形象。
在界定知识分子群体的思维上萨义德受到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和班达两个人的影响比较大。他们二人在“知识分子究竟是为数众多,或只是一群极少数的精英”这一问题上持相反的意见。葛兰西定义的知识分子概念比较宽泛,他把知识分子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的知识分子包括老师、教士、行政官吏等世代从事相同工作的人,另外一类是有机的知识分子,这些人与阶级或企业直接相关,并且这些阶级或企业运用知识分子来组织利益,赢得更多的权利,获取更多的控制。按照葛兰西的看法,只要是社会上从事与知识相关的工作的人都可以看成是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广泛地参与到社会生产当中,创造技术,生产知识,带动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改变世界的面貌,这一群体不断地行动,不断地发展壮大。与此相反,班达给出的知识分子的定义则是比较狭窄的,他定义下的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德高望重的哲学家,这些人构成了人类的良知。班达认为知识分子是一个知识阶层,他们以维护世界的真理和正义的标准为己任。所以他说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活动本质上不是追求实用的目的,而是在艺术、科学或形而上学的思索中寻求乐趣,知识分子的本色在于能够在真理和正义的感召下自觉地反抗权威,保卫弱者。班达的知识分子是一群对现实持一种强烈反抗态度的才智出众的人,他们远离现实,但是又强烈关注现实,他们的人格和责任使他们“甘冒被烧死、放逐、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危险”,[2]所以这样的人是“特立独行的人,能向权势说真话的人,耿直、雄辩、极为勇敢及愤怒的个人,对他而言,不管世间权势如何庞大、壮观,都是可以批评、直截了当地责难的。”[3]葛兰西的知识分子具有广泛的社会世俗性,他们存在于与知识生产和分配相关的领域中。葛兰西和班达对知识分子认识的不同之处在于,葛兰西秉承了威廉斯的观点,他强调的是知识分子的外部表现,也就是与知识相关的身份。而班达则把自己的侧重点放在了知识分子应有的内在性,即知识分子应担负的社会责任上,知识分子必须能够代表弱势群体,敢于挑战和反抗权力,敢于向权势说真话。
在综合了前人对于知识分子的论述的基础上,萨义德表明了自己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但是他旗帜鲜明的指出,不能简单的把知识分子看成是从事某一行业的精英人员,在这一点上他的看法不同于葛兰西,他更加看重的是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扮演的公共角色身份,“我认为,对我来说主要的事实是,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4]
可以看出萨义德同样看重知识分子这一特殊人群所担负的社会责任。他意味深长地指出,知识分子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那些经常被遗忘或者被弃置不顾的人们和议题,不能轻易地被利益集团或者政府收编。萨义德立场鲜明,他不再把知识分子局限于狭窄的专业领域,更注重知识分子的公共身份,他认定的知识分子应该有自己的道德操守和坚定的立场,在公共场合对公众关心的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这种声音是代表公众和为公众所发的。这种强调知识分子为民喉舌,为公理和正义呐喊,代表社会良心的思想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明道救世”的传统有暗合之处,余英时在谈论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时说:“一方面‘道’以人间秩序为中心,直接与政治权威打交道;另一方面,‘道’又不具有任何客观的外在形式,‘弘道’的担子完全落到了知识分子的身上”,[5]可见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弘道”这一点上和萨义德眼中的知识分子是相通的。既然知识分子要带公众立言,要“为”公众,那么知识分子就需要时刻保持有一种批判意识,“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作法。”[6]知识分子依赖于一种怀疑和勇于献身于理性探究和道德判断的意识,他们知道如何善于用语言,何时以语言介入。理性的怀疑和批判是西方人文学者最重要的品质,存在主义大师萨特也对知识分子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在我看来一个知识分子正是这样的人:他既忠实于政治与社会的总体,但又不断地怀疑这个总体……如果只有忠诚而没有不满,这是不行的,这样他就不再是一个自由人了。”[7]当然这并不是要求知识分子必须以现行政策的批评者的身份而出现,而是说他们应该时刻保持着一种警觉状态,他们肩上担负的责任使他们不能被尘俗观念带着走。在萨义德眼中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是最为重要的,他认为知识分子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丧失其批判立场,即便是在民族存亡之际也必须保持批判精神,“虽然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知识分子为了确保社群生存的所做所为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但忠于团体的生存之战并不能因而使得知识分子失去批判意识或减低批判意识的必要性,因为这些都该超越生存的问题,而到达政治解放的层次,批判领导阶级,提供另类选择”。[8]由此可见在萨义德眼中怀疑和批判精神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多么重要。美国学者阿尔文·古尔德纳在其知识分子研究性著作《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中虽然将知识分子看成是一个新兴的阶级,但对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怀疑和批判精神上同样与萨义德不谋而合,他说:“知识分子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中,最深层的结构是他们对自己拥有自主性所怀的骄傲。他们认为这种自主性是基于他们反省自己,以及基于这种通过反省而决定自己命运的能力。因此任何只要求人们服从权威,或只要求人们遵从,而不容反省、自决的传统,都被视为是对我的粗暴扭曲”。[9]
知识分子具有批判意识,代表弱势群体,敢于向权势说真话,这些属性决定了他们必然要遭到权力中心话语的排斥会被边缘化,因此知识分子就面临着“流亡”的命运,但这种流亡不是古代意义上的背井离乡,被放逐到不毛之地的流亡,而是一种隐喻意义上的流亡。知识分子为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甘愿居于主流之外,不被权势收编,从而保持质疑和批判的立场。对知识分子来说流亡是一种特殊的人生境遇,它是一种中间状态,使人既不会完全与新环境完全融合从而产生安逸感,同时还会对旧环境产生美好的回忆,这种状态会时刻提醒知识分子保持独立性和批判意识。知识分子处于局外和边缘的地位使得他们可以摆脱主流文化和权力的束缚,从而能够更加清醒地分析体认文化中权力的运作模式,及时有效地为公众发出声音。流亡知识分子中萨义德对阿多诺最为推崇,阿多诺的一生都在和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以及西方大众消费主义等各种危险周旋、奋战。阿多诺将知识分子“再现为永恒的流亡者”,他身处断裂时代,拥有双重视角。他目睹世界的肮脏与残忍,却发现它是人类发展的结果,而非上天赐予的秩序。这一发现,促使他拒绝神权,甘当俗人。阿多诺在《道德的最低限度》中说出了流亡的意义:“严格来说,在当今居住是不可能的。我们以往成长的传统居所已经变得令人难以忍受:每一个舒适的特点都以背叛知识为代价,每一个庇护的遗产都以家庭利益陈腐的契约为代价。”流亡的痛苦把阿多诺从麻木中惊醒,在绝境中找到了通往自由的路,“对于一个不再有故乡的人来说,写作成为居住之地”。在阿多诺身上萨义德看到了流亡带给知识分子的快乐,流亡有时可以提供不同的生活安排,以及观看事物的奇异角度;这使得知识分子的行业有生气,但未必减轻每一种焦虑或苦涩的孤寂感。流亡意味着使知识分子成为永远的边缘人,处于边缘地带就可以离开中央集权的权威控制,在边缘就可以看到一些足迹从未越过传统与舒适范围的心灵同行失去的事物。流亡知识分子的边缘性使他们回应的不是惯常的逻辑,而是大胆无畏,代表着改变、前进,而不是固步自封。
如今的社会中知识分子面临着现代专业化的多种压力,它们挑战着知识分子的机谋和意志。这些压力包括知识专门化,社会对专业知识的认同,知识追随者屈服于权威被权威利用等。专业化压力的存在可能会导致知识分子失去独立的自主性和批判精神,沦为不问世事,只专注于专业兴趣的专家学者,或者被卷入自由市场体系成为工业机构、利益集团的资深技术顾问等。如何对抗专业化带来的挑战,萨义德提出了以业余性来对抗,他所说的业余性指的是“不为利益或奖赏所动,只是为了喜爱和不可抹煞的兴趣,而这些喜爱与兴趣在于更远大的景象,越过界限和障碍达成联系,拒绝被某个专长所束缚,不顾一个行业的限制而喜好众多的观念和价值”。[10]萨义德指出了对抗专业化的动力是知识分子自身对知识的兴趣和喜爱,是一种非功利化的动因。在他看来知识分子应该再现一套不同的价值和特有的权利,所以他说今天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个业余者,作为知识的掌握者和民众的代言人,知识分子有权对技术专业化提出道德议题。
萨义德一生都在践行他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纵观他对知识分子的论述,从中可以看出他似乎以自身为真实写照。萨义德的双重身份使他具有了隐喻流亡的境遇,他摆脱了东西方两种文化的束缚,在边缘的位置揭露出西方帝国主义如何利用文化霸权实现对东方的控制,他运用福柯的知识权利分析法透析了西方视野中的东方,揭示了文化语境中的微观权利运作模式。萨义德还与萨特一样对政治持一种介入的姿态,他长期参与民族解放斗争,并曾担任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常委。面对权势萨义德总是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和批判精神,在阿拉法特与以色列签署“奥斯陆原则宣言”问题上,他认为协定内容有如向以色列投降,出卖巴勒斯坦人的权益,所以与阿拉法特决裂划清界限,他还曾经公开声援支持因写《撒旦诗篇》而被下达格杀令的作家拉什迪。萨义德一直对知识分子的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实际上无论他的学术活动还是政治活动都是对这一议题的完美阐释。在他眼中知识分子具有独立的人格,他们具有批判意识,在公共场合代表弱势群体发出声音,他们处于流亡的隐喻状态,甘于脱离中心,处于边缘地位,是社会的边缘人和业余者,面对权势他们敢于讲真话,敢于表达自己的立场。
[1][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246.
[2][3][4][6][8][10][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单德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14-67.
[5]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论[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14.
[7][法]萨特.他人就是地狱:萨特自由选择论集[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65.
[9][美]阿尔文·古尔德纳.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M].杜维真,罗永生,黄蕙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32.
A Study on Said’s Concept of Intellectuals
Zhao Zhaoqu
Said,the great master lived in the post-colonialist times,focuses his attention on the special group of intellectual He is a Pakistan American receiving formal Western-style education.He lay more stresses on the intellectuals’basic morality and their social responsibility.According to his opinion,intellectuals should possess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and critical thinking,and be able to speak up the disadvantaged people’s demands in public.They dare to tell the truth and declare their standpoints when facing those influential people.
intellectual;responsibility;critical thinking;exiling;amateur
D01
A
1672-6758(2012)04-0025-3
赵钊渠,硕士,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邮政编码:475001
Class No.:D01Document Mark:A
(责任编辑:蔡雪岚)
——《格格不入:萨义德回忆录》略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