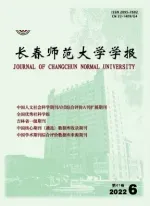《简爱》的后殖民主义视角再解读
符海平,刘向辉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广东罗定 527200)
《简爱》的后殖民主义视角再解读
符海平,刘向辉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广东罗定 527200)
《简爱》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富有激情、幻想、反抗、坚持不懈精神以及对人间自由幸福的渴望的主人公的美好形象。但是随着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发展,作品中的“疯女人”也逐渐受到关注。“疯女人”被设定为一个沉默的主体、丧失话语权的他者,这充分彰显了一种帝国主义有预谋的知识暴力的意识形态。本文在后殖民主义视角下对《简爱》进行重新解读,旨在挖掘隐藏在作品内部的帝国主义话语,进而认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在文学作品中的渗透。
后殖民主义;话语权;他者;帝国主义
《简爱》(Jane eyre)是19世纪英国著名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它被认为是夏洛蒂·勃朗特“诗意的生平写照”,是一部具有自传色彩的作品。读者对其评价基本上是:《简爱》阐释了这样一个主题,即人的价值就是尊严和爱。文中的简,人生追求有两个基本旋律:富有激情、幻想、反抗和坚持不懈的精神;对人间自由幸福的渴望和对更高精神境界的追求。《简爱》通过叙述孤女坎坷不平的人生经历,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不安于现状、不甘受辱、敢于抗争的女性形象,反映一个平凡心灵的坦诚倾诉的呼号和责难,一个小写的人成为一个大写的人的渴望。与此传统评价视角不同的是,后殖民主义著名代表人物斯皮瓦克说:“如果用小说的叙事动力这样的术语来讲,简是如何从反家庭的地位走向合法家庭的地位的?是活跃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那个话语场。”[1]163“阅读19世纪的英国文学,不可能不想起曾经被看作英国的社会穿教团的帝国主义,是代表英国人的英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再现产品中,文学的作用不应该被忽视。这两个明显的‘事实’在以往的19世纪英语文学的阅读中一直被遗忘着。这本身就是帝国主义事业持续胜利的明证,它被移植或扩散为一些更为现代的形式。”[1]158本文正是以此作为出发点,试图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去重新解读这一著作,挖掘隐藏在作品内部的帝国主义话语,进而认识帝国主义霸权意识形态在文学作品中的渗透。
一、《简爱》的叙述与社会空间
“我们必须阅读经典的文献,也许还有现代和前现代的欧美文化的全部历史,以便把这些著作中沉默无声的、在意识形态中被作为边缘的东西挖掘出来,加以伸张、强调,使它发出声音。”[2]89因此,在阅读《简爱》这一经典巨著时,读者应该把对作品叙述方式和作者创作的社会空间的了解紧密结合起来。正如同时代的许多经典小说中会提到海外属地一样,《简爱》提到了印度。印度之所以在《简爱》被提及,是因为英国的力量使得这一巨大的领地能够被顺便提到。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在英法文化的每个角落,我们都可以看到帝国事实的种种暗示。但是,在英国小说里,帝国比别的任何地方都更有规律和更经常地出现。在当时,英国小说是英国社会中唯一的美学形式,并获得了主要表现者的重要地位。由于小说在“英国事务”问题上占有了如此重要的地位,从一定意义上来看,英国小说参与了英国的海外帝国。可以说,帝国在其中每一处都是重要的背景。“在欧洲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帝国具有多重功能,作为一个被编纂的,即使只是边缘可见的虚构存在,它是一个参考系,一个界定点,是一个合适的旅行、聚敛财富和服务的背景。”[2]85在文化领域的大部分里,英国充斥着关于帝国使命的厚重的、几乎是哲理性的意识。这种为帝国的扩张需要所创立的与军事、经济和政治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能够保存并扩大帝国而不必浪费其精神上、文化上或经济上的资财。这种帝国主义具有两种不同却密切相关的方面:“一方面是一种以力量掠夺领土的思想。另一方面,它通过在帝国主义的受害者和维护者之间确立一个自发的、自我肯定的正当权威体系,来推行一种模糊或掩盖这种思想的实践。”[2]94可以说,帝国主义与小说是相互扶持的。一方面,帝国是构成小说的叙述权威模式;另一方面,则小说作为帝国主义倾向基础的一个复杂的意识形态结构。
二、《简爱》的叙述方式:帝国主义公理性叙述方式
作为一部女权主义经典文本的《简爱》,尽管夏洛蒂·勃朗特在文中树立了一位有着强烈个性、敢于追求自我、独立主动的崇高女权主义形象。但是从另一视角来看,“不仅在英国的文学研究中,而且在对那个伟大的帝国主义时代的欧洲文学的研究中,我们就可以给文学史创造出一种叙述方式,那就是现在被称为‘第三世界’的那中‘世界化’的方式。第三世界被看作一种遥远的文化,既是被剥削的对象,又拥有着需要发现和阐释的丰富完整的文化;……这一切使得‘第三世界’成了一个能指,使我们忘记那种‘世界化’。”[1]158正是这种“第三世界”的世界化方式为我们重新阅读《简爱》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在《简爱》中,简是众人关注的焦点,而那个住在阁楼里的疯女人却超越于读者的视野之外。与对简的正面描述不同的是,疯女人伯萨·梅森的形象是通过她丈夫——罗切斯特从反面叙述的,她是一个被扭曲的人物形象,读者根本找不出正面论据来分析她的形象。如果我们能从传统视域中走出来,通过对罗切斯特那种反面叙述进行反思,我们不难戳穿他那片面的夸张以及揭示他那虚伪的嘴脸,从而还伯萨·梅森以清白。在作品中,罗切斯特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他说他父亲是一个贪婪的人,一方面由于疼爱他的哥哥罗兰,而把全部财产都分给大儿子,另一方面又不忍心看着小儿子受穷,于是帮罗切斯特找了一位西印度群岛种植园主的女儿伯萨·梅森为妻,以获取三万镑的嫁妆。在罗切斯特去牙买加迎娶自己的准新娘之前,他声称这一切他都不知情,他父亲只告诉他伯萨·梅森是当地有名的美女。在这件事情上,他自己是“无辜的、浅薄的、没经验的”。但罗切斯特很清楚的是:因为当时的法律剥夺了已婚妇女支配嫁妆的权利,嫁妆只能由丈夫掌管,所以结婚之后,他理所当然地成为妻子嫁妆的实际支配人。对此,他并未提及婚后对嫁妆的处理情况。他只是说:“四年后我足够富的了。”他通过继承哥哥罗兰的遗产,使他有了摆脱依靠妻子的托辞,伯萨·梅森的嫁妆在四年后对他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但是罗切斯特回避了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一个身无分文的大学毕业生在没有得到父亲任何经济支持的情况下,是如何度过这四年的呢?事实只能是:他完全支配了妻子伯萨·梅森的嫁妆。婚后的罗切斯特因为伯萨·梅森的遗传性疾病发作而宣称妻子是个疯子,于是残忍地把她关在阁楼里,把她推进了苦难的深渊之中。在此,罗切斯特虚伪、邪恶的形象立刻展示在读者面前,作为丈夫,他不去好好地照顾有病的妻子,反而一味地宣称自己是婚姻的受害者,一味地给伯萨·梅森抹黑。而事实上,伯萨·梅森被紧闭之后,罗切斯特变成了一个腰缠万贯的新贵族,游历欧洲寻找漂亮女人,过了十年的放荡生活。罗切斯特用动听的言词掩饰自己,用恶毒的话语扭曲妻子的形象。但是他那华丽的言词并不能掩盖其对妻子伯萨·梅森的财产、人身的经济和性剥削。罗切斯特的一面之辞就是对伯萨·梅森“缺席审判”的话语场。罗切斯特的这种反面叙述和主导话语充分彰显了夏洛蒂的帝国主义公理性的意识。它可以一定程度上激发起读者对历史上帝国主义叙事的愤怒。文本中的伯萨·梅森是一个“他者”,作为一位来自殖民地的女性,伯萨·梅森被剥夺了她本应有的话语权,被残酷地囚禁在阁楼上,以疯子的形象出现在读者的视野中,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伯萨·梅森是受双重压迫的属下妇女的代表,既受父权制的压迫,又受帝国主义知识暴力的迫害,她是沉默的主体。她是“被动的,没有参与能力,被赋予了一种‘历史的’主体性,最重要的是,就其自身而言,它是非活性的,非独立的,非自主的:可以被接纳的……‘主体’已经被异化,在哲学的意义上——也就是说,除了自身与自身的关系外——被他人所假定,所理解,所界定。”[3]126夏洛蒂·勃朗特通过把伯萨·梅森置于沉默的主体、丧失话语权的他者的位置,这是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充当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话语先导。她所建构的殖民主义的故事是一个相互的过程,其中,欧洲力量在巩固帝国主义的至高无上的自我的同时,引诱殖民地人们与其同谋以构成被殖民者自身作为他者和无声音的或从属的主体。伯萨·梅森的作为自我的主体立场在文本中被帝国主义话语彻底涂抹了,这种霸权话语被殖民者保护主义叙述化。这种叙述方式的构建展示了比赤裸裸的压迫更加阴险的一个过程,因为在这里,被殖民者经说服而把主人编造的知识内化成一种自我认识:“他(欧洲代理人)通过强制他们把外来者驯化成主人而把绝不仅仅是未被刻写的他们自己的世界建构一新”,这个过程生产一股使“被殖民者自视为他者”的力量。
夏洛蒂·勃朗特以一种独特的想象力,通过一系列家庭和反家庭因素的组合勾画出《简爱》的发展轨迹。小说中的简是达到目标的反家庭的角色;罗切斯特和妻子(伯萨·梅森)是合法家庭的代表;而简和罗切斯特则是反家庭的代表。小说通过几个序列,将简从反家庭的地位移到合法家庭的地位。但对于简身份的转变,夏洛蒂·勃朗特作了一种知识暴力的安排。即伯萨·梅森必须放弃自己的权力,将“自我”演化成那个假想的他者,放火烧掉房屋,烧死自己。这样伯萨·梅森这个阻碍简从反家庭的角色过渡到合法家庭地位的绊脚石就被成功地搬走了,简也就名正言顺地和罗切斯特组合成合法家庭,成为合法家庭的代表。作者只有通过这种安排才能使简成为英国小说中女权主义个体主义的英雄。“这是帝国主义一般知识暴力的寓言,是为了殖民者的社会传教团的光荣而设置的殖民地主体的自我祭献的构想。”[1]168这正是活跃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为简从反家庭的地位走向合法家庭的地位提供了那个话语场。而在传统视角上,伯萨·梅森常常被解读为一个自我牺牲的妻子的代表,如果我们熟悉英国殖民者在印度推行的寡妇应当牺牲的法律知识,我们就会意识到这个启示的重要意义。作为疯女人的她在《简爱》中的作用就是使得人与兽之间的界限模糊起来,并因此削弱她在法律条文或法律精神之下的应有地位。“帝国主义的语言侵略抹掉了一种被殖民者自我的刻写,她的死被解作帝国主义的一般知识暴力的一个讽喻,是为了美化殖民者的社会使命而建构的自我殉身的主体。”[1]210夏洛蒂·勃朗特倾向于将导致殖民地妇女失语的压迫性戏剧化;伯萨·梅森的“疯”在作品中设定为先天的存在,这其中蕴含了白人自由主义与这种失语现状的共谋关系,即英国人将第三世界妇女的代表伯萨·梅森构造为失语者,并持续对印度及它的历史进行殖民书写。
三、结论
简从社会边缘进入家庭和社会的中心,作者给了她充分的话语权。而萨·梅森在文本中设定先在的“疯子”,成为一个彻底丧失话语权的“边缘人”、“他者”,这是由于她的社会存在状况的原因,必须植根于她的经济和文化边缘的客观的“非身份”立场。夏洛蒂·勃朗特对于伯萨·梅森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对小说叙述方式的操纵,完全从英国殖民者视角对她进行了帝国主义的描述,这是一种帝国主义有预谋的知识暴力的意识形态。这充分彰显了作品在后殖民社会构成中的关键作用,强调了它们在影响革命和恢复功能方面的首要性,她也强调了作品在欧洲征服印度并使其殖民化过程中的先导作用。“英国人在个人、位置、文化及语言方面的权威性,通过教育和批判机构,它向他者持续不断地揭示和重复对他/她的变性的最初的征服、消灭、边缘化或自然化的过程,好像是天经地义的、没有文化根基的、普遍的、自然的事情。”[1]320对伯萨·梅森这位第三世界的妇女的非人格化的分析所异化的不仅仅是启蒙时代关于“人”的观念,而且也向事先给予的人类知识意象的社会现实的透明度提出了挑战。正是享有文化特权的西方精英把理论语言作为他们制造加强自己的权力——知识方程式的“他者”时所用的一种权力手段。语言、文本、作者权威性以及它们当中运作的话语场,成为《简爱》一书的一个掩盖的线索。叙述模式与政治压迫的同谋关系,使我们能够揭示出在对殖民地人特别是妇女实施持续的压迫时,作品所扮演的丑恶的政治角色。
[1]罗钢,刘象愚.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美]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3][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A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 onJane EyreAgain
Fu Hai-ping,Liu Xiang-hui
(LuodingPolytechnical College,Luoding527200,China)
Jane Eyreshows us the good image of theprotagonist who is full of passion,fantasy,resistance,unremitting spirit and desire for the happiness and freedomofthe world.Bu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post-colonialism,the"crazy woman"of the text also gradually become the focus.“Crazy woman”is set to a silent subject,a others who loss of the right of speaking,it fully reveal a kind of a ideology of imperialism premeditated violence of the knowledge.under the viewofpost-colonialism,This article is tointerpretJane Eyreagain,tryingtodig in the imperialism discourse which are hidden in the works,and knowthat imperialismideologyis penetratingin the literature works.
post-colonialism;discourse,otherness;imperialism
I106
A
1008-178X(2012) 04-0088-04
2011-11-24
符海平(1982-),男,江西永丰人,罗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从事英美文学和伦理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