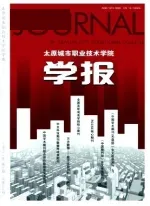魏晋文人情诗的情感探析
刘云云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 400700)
魏晋文人情诗的情感探析
刘云云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 400700)
魏晋时期,文人情诗经历了繁荣期,并体现出缘时而发的情感起源、感而不伤的情感发露、情志合一的情感内蕴三个特征。
魏晋;文人情诗;情感探析
魏晋时期,政局混乱,人命草芥,连年征战,文人在生活上遭到前所未有的煎熬,思想上更是漫无所归,儒、释、道,唯心论与唯物论,诸种教义皆畅行无阻。“一种真正抒情的、感性的”纯“文艺”伴随着魏晋时期理性而思辨的哲学产生了,反映在诗歌创作上,则体现了鲜明的个性色彩、题材的丰富多彩、文学技巧的卓然纯熟以及艺术风格的多样化。所以,魏晋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无疑具有重要的地位,为中国诗歌黄金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并且代表了当时文人独一无二的气质包孕。而魏晋文人在情诗上的成绩十分突出值得一著:不仅出现了第一次以情诗为题的诗歌,也经历了情诗的繁荣期。这个时期的爱情诗歌,从情感起源到情感发露再到情感内蕴,都具有独特价值和时代意义。
一、缘时而发的情感起源
魏晋时期,文人长期处于群体性悲剧的耳濡目染中,并且自身也是朝不保夕,真可谓命运多舛。这样哀鸿遍野、生灵涂炭的时代使文人举步维艰,生活在一种巨大的悲剧束缚中。而他们对生活的认识以及思考又比常人更为敏感更为深刻,所以导致了文人的生存饱受精神和物质的双重考问。“中国文人生命的危险和灵魂的郁闷,无过于魏晋”。文人对这种时代整体的苦难的感受,远远强于其他时代对于生不逢时的彷徨苦闷以及个人失意的忧伤与叹息。生命群体悲剧的不可抗拒性随着不断地阅人历世而更加根深蒂固,文人的人格不断地被弱化,到最后,只能在自己擅长、自己做主的诗歌创作中寻求安慰。甚至可以说,正是他们的痛苦以及他们亲眼所见之痛苦使他们不得不拿起笔来,遁入到另一个自己幻想的世界中,以换取短暂的自我人格体现。
正是这种遁入使得魏晋时期被今人归纳为文学自觉的时代,文人纷纷借诗歌抒写一己之情,表达诗人的独特个性。理论界也曾提出“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即文学应该是阐述人的心灵的,甚至可以说是私人的情感。这在魏晋时期就已经得到实践。处于儒学式微的魏晋时期的文人冲破儒学束缚而回归到抒发个人情感的文学单纯性上来,文学更加多样化、更加活力,表现在诗歌上,就是诗歌真正散发出“诗性精神”。于是,我们今天看到了大量大胆直言私人情感的诗歌,这些诗歌不再束缚于传统的政治教化的藩篱,他们大多因循“小我”的情感线索。比如亲情,左思在《娇女诗》中别出心裁地表达了自己对两位女儿的关爱。而爱情作为人类情感的集大成者,更是在魏晋时期出现了极其繁荣的高潮,出现了一大批的感人肺腑的爱情诗作。由于建安后人们自我意识的觉醒,认识到自己是有独立性的精神个体,更是无遮无碍地表达了自我对爱情的渴望以及感知。
与此同时,玄学的流行以及社会对人个性及欲望的认可,也使得文人都大胆追求情欲爱欲,重德轻色这一天平发生了倾斜,尚美之风逐渐流行于士族文人之间,如曹植的《洛神赋》、《美女篇》中对佳人的赞美和挚爱。《列子》杨朱篇也充分渲染了那种纵欲的快乐主义,这也显示了当时人们追求官能的享受,这其中当然包括女色。而“好色”的流行使女子闯入文人的文学舞台中,并获得文人情真意切的描摹以及褒奖。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连接男女关系的爱情获得文人的关注,从而演化成诗篇。
魏晋时期的文人情诗都不是西方那种无缘由地呐喊式抒情,而是借事表情,大多承借现实事件,如离别、被弃、悼亡等。这也是当时对汉乐府现实主义文风继承与发扬的结果。在现存的魏晋情诗中,极大部分是由事而发的感情激荡:他们或者处于离别之思,如徐干《室思》;或者有感于君心不再,如傅玄《西长安行》;或者悼念逝去的爱人,如潘岳的《悼亡诗》。无事呻吟的爱情诗篇几乎很难得见。魏晋时期是整个中国古代史最为悲剧的时代,生命是极其脆弱的,生离死别和被抛弃乃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因此,魏晋文人情诗也是对现实社会的描摹,对真实事物以及外部世界进行真实体察和客观处理的结果,这也是一种主观与客观的另类面对。
由此可见,正是魏晋这个时代的总体特征才促成了情诗在当时的繁荣地位,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当时文人的脉脉情怀,一洗古人不善言情的面目。
二、感而不伤的情感发露
魏晋文人的情诗虽然像其他古诗一样“长于咏唱一种有缺憾的爱”,总是怀有那种戚戚然的隐约悲痛,但这种悲恸却依然没有达到“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激情壮烈和“执子之手与之携老”的信誓旦旦。诗人总是暗自盘算着,内心充满了不安全感,于是便有了“路险不得征,徘徊不能去”的踟蹰和“君行殊不返,我饰为谁容”的怀疑。这种情感是节制的甚至是胆怯的,以至于我们在魏晋情诗中看到的总是点到为止的爱情表露,更谈不上爱情宣言。
除了传承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使文人在表达爱情上显得畏缩和中庸外,这种不确定、不决然的情感特征也缘于魏晋文人重视词采技巧。从曹子建因词采而得名后,后人皆仿之,使得诗人竭尽所能培养驱使辞藻的能力。正是因为对于辞藻的过度挖掘,使诗人的感情便没有那种震撼的直指人心的力量。我们在欣赏那个时代的情诗的时候,总是要拨开重重的精雕细琢的辞藻才能最终看到诗人的情感,这样的情感当然就大打折扣了。在潘岳的《悼亡诗》中,虽然诗人的感情历来为人们所称道,但是却需要“透过他的思力的安排”才能感受到诗人的亡妇之痛,诗人深谙于并且热衷于词采,在诗末采用了“庄子击缶”的典故,我们不得不怀疑诗人抱定的是“庄缶犹可击”的愿望,而不是怀念佳人的感怀伤逝。
这种感而不伤的态度也受到当时爱情观的影响。魏晋时期战祸不断,男性劳动力大量消耗于战场,这无疑使女子在日常生活中的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得到提升。与此同时,文坛上活跃着许多妇女,如左思之妹左芬、魏文帝之后甄宓等等,徐陵编撰的《玉台新咏》就收录了许多魏晋时期女性作品。由此可见,此时女子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直接表现在对女性贞节观的宽容。魏晋时期无论地位显赫还是平常女子,再婚现象十分普遍。所以,那个时代的爱情观可能并没有传统的“一女不事二夫”那么不置可否。既然女子都已经不再强调忠贞不二,那么男性当然更不会为爱情而呐喊和坚守。所以,那个时代的文人为爱而深有感触是普遍正常的,但是这种感触并没有达到肠断心催的程度。这种感而不伤的情调是流动在魏晋文人的情诗中,信手就可拈来。例如傅玄的《车遥遥篇》诗云:
车遥遥兮马洋洋,追思君兮不可忘。君安游兮西入秦,愿为影兮随君身。
君在阴兮影不见,君依光兮妾所愿。
这首诗是作者代由女子口吻借由离别阐发了对君的思念,无疑体现了诗人自己的爱情观。初次读来感人至深,可是当我们仔细研究末二句,就可得知诗句中话中有话:你如果走光明的道路,我就对你不离不弃,但你若不义,我就要弃君而去了。原来“愿为影兮随君身”的深挚思慕只是一时的甜言蜜语,“我”的追随是有条件的,所以这种感情虽然发露出来却并没有到为爱而痴狂的地步。魏晋文人不惧表达一己之私情,但却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将这种感情发挥到极致,他们只是停留在表现的阶段,并没有体现出其他情歌那种沉溺谷底的哀伤和为爱疯魔的宣泄。深陷于这种精神上的困顿,魏晋诗人并没有提出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宣言,他们不可能有“故作不良计,勿复愿鬼神”的决定,他们也不再殷殷期盼“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的长相厮守。在时代痛苦所赋予的命运中,他们甘愿沉沦于这种情感的适度表达,也不再去拯救什么。魏晋文人对于爱情有着自己的想法,并且已经付诸笔端,这已经开创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齐梁时代艳情诗的基础。
三、志情合一的情感内蕴
传统的“诗言志”理论使诗人胸怀天下,为国家兴衰而殚精竭虑,他们所关注的主要目标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诗言志”使诗人的观念升华,拥有更多的壮志豪情与时代精神,而不屑于一己之私。而魏晋爱情诗恰恰更接近一己之私,表现在两个方面:个人的爱情理想与个人的政治理想。我们简单概括为小我的“志”与“情”,这个“志”与“情”并不是宏观上,而是微观上的概念,都属于个人情感的范畴。
利用爱情诗来表达个人的政治理想,这是源于屈原的香草美人手法。深受传统儒家的教化使命,文人与生俱来地怀有家国天下的情操,他们想要实现这样的抱负,就必须积极地“入”世。他们不可能忘却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虽然自知无望,他们也会在心灵的深处期待自己满腹才华可以获得君王赏识,从此“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可是在魏晋这个特殊的时代,政治已然绝望,文人所表达的政治理想不过是垂死的挣扎。曹子建后期由于受到哥哥和侄子的压制辗转颠簸流离于各地。他的情诗主要抒发他在压制之下时而愤慨、时而哀怨的心情,表现他不甘被弃置、希冀用世立功的愿望。例如《七哀》诗云:
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
曹植自比贱妾,那份家国天下的壮志豪情已经到了如此卑微的地步。他虽自知功名无望,却仍像怨妇期待归人一样期待自己的政治理想能够得到实践。用爱情诗表达政治理想也大多隐蔽了诗人的无尽心酸,这种不可明说的愤慨和哀怨,只能化作卑微无奈的怨妇情结,随着时光而消逝。所以,曹子建终未偿愿、郁郁而亡。
南北朝时期的梁代钟嵘《诗品·序》曾经提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非长歌何以骋其情”的说法,开始重视“情”在诗歌中的地位,可是这种“情”早在魏晋时期的爱情诗中就有了长足的体现。遍布于世的动乱、冲突和恐怖,使文人锐敏地感受着人生的无常、世情的险恶,政治不敢妄谈,生命更是没有保障,既然现实已经没有出路,满腹的才华反而会招来杀身之祸。他们只能转而表达个人的情感,去追求属于个人生命的真实的喜怒哀乐。中国社会以家庭为单位,男性在周旋于时代性的悲剧漩涡后的虚脱与疲惫,更需要休养生息,需要娱乐和松弛,即投入到心灵最后的港湾,也就是那千依百顺的妻子以及自己尚可做主的家庭生活。或许在那个时代,只有情感的奢靡才能让文人品尝到人世的生气和温暖,才能让文人感受到自己的存在感。所以,爱情的渲染同时也是心灵的投宿,爱情诗歌更是时事维艰下的生命焦虑者的逃亡。张华的《情诗其五》也是远游旷夫恋妇的言情之作,描写游子思妇的哀愁无限以及爱情带给人的存在感。郑振铎说张华:“其情思却终是很恳切坦白,使人感动的。”而这种恳切坦白的情思正体现张华作为一介文人在情感上的自省以及逃避世俗的立场。
然而,纵观魏晋文人情诗,诗人所表达的并非单纯的“志”与“情”。单纯的言情诗歌,还是比较多地存在于民歌中,文人带有与生俱来的教化使命,他们不可能忘却,但迫于现实转而逃离。人生来就是复杂的,所以他们所表达的情感内蕴存在着个人政治理想以及爱情理想,从中不难发现那个矛盾纠结时代文人的出与入的徘徊。正是这种矛盾构建了魏晋文人情诗志情合一的情感内蕴。或许我们也可以说,文人在爱情诗中找到了“志”与“情”的平衡点。他们一方面念念不忘建功立业,另一方面又留恋软玉温香的爱情港湾。而这种复杂的情感内蕴,也使魏晋情诗多了一些民歌的清丽脱俗,多了一些文章的经国不朽。
魏晋文学在浩瀚千年的中国文学史中始终属于独一无二的地位,而在文人情诗的发展上,更是处于提纲挈领的地位,不仅第一次出现了署名的文人情诗,也出现了文人情诗的繁荣喷发。由于时代的悲剧整体性以及文学自觉意识等种种原因,魏晋文人大胆表达内心的爱情。但是这种感情却是相当节制的,他们感而不伤、发而不露,不仅忠诚于内心,也继承了中国含蓄温婉的诗歌传统。在这些精彩纷呈的爱情诗篇中,我们除了可以体会到诗人爱情的内心激荡外,也可以看出诗人对香草美人手法的继承,在诗歌中展现了他们的政治理想,可以说是情与志的完美统一。魏晋情诗不仅开启了齐梁艳情文学的繁荣场面,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唐诗宋词中的糜情之作奠定了基础。
[1]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刘大杰.魏晋思想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3]叶嘉莹.汉魏六朝诗讲录[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4]胡晓明.中国诗学之精神[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
[5]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6.
[6][梁]刘勰.文心雕龙[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7]宗白华.美学与意境[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8]赵志坚.魏晋南北朝妇女再婚考述[J].山东大学学报,1995,(1).
[9]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0]吕德申.钟嵘诗品校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11]仪平策,廖群.情系何处——中国古代文人情诗的文化剖析[J].求是学刊,1996,(6).
[12]陈寒鸣.躲闪与放肆-传统艳情文学的心态特征[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3).
I206
A
1673-0046(2012)3-017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