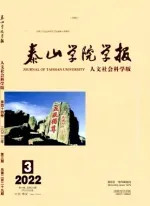《南齐书》的文体构成及其语料价值
黎平
(贵州大学 中文系,贵州 贵阳 550025)
《南齐书》是南朝梁代萧子显所作的史书,是研究中古汉语的较好的语料。其所录文献基本上是南朝齐代的作品,史书的作者和史书的内容可以说是同一时代的,而正史又较少有被删改的可能,因此语料时间和内容的可信度都很高。它所反映的语言处于中古中期,时间跨度大约在100年左右,可以看作是一个共时平面,因此语料所反映语言现象的系统性强。本文从另外一个角度即文体的丰富性来讨论《南齐书》的语料价值①。
一、文体构成分析
从整体来看,《南齐书》是史书中的纪传体。但这个“体”,是史书的体例,不是“文体”所指的体裁。一本史书只能有一种体例,但可容纳各种文体。《南齐书》包含的文体丰富多样,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散文,一类是韵文。它们的区别在句式和韵律上。散文大多句式长短不一,不押韵,不讲究节律;韵文则句式工整、押韵、讲究节律。因此,在功用上,韵文擅长“表情”,散文擅长“达意”。
散文有五种体裁:诏令体、议论体、记言体、叙述体和说明体。这主要是从文章的用途来分类的。韵文有三种体裁:四言体、五言体、赋体。这主要是从韵文句式的角度来分类的。
1.诏令体,即皇帝、太后等的诏令。例如:
诏曰:“承之禀命先驱,蒙险深入,全军屡克,奋其忠果,可龙骧将军。”(卷1《高帝纪·上》)
上敕之曰:“吾前后有敕,非复一两过,道诸王不得作乖体格服饰,汝何意都不忆吾敕邪?”(卷40《庐陵王子卿传》)
2.议论体,即史臣的评论(“史臣曰”)、大臣的奏折以及书信等。这些多为议论性的文字,所以称为“议论体”。例如:
(嶷……又启曰:)臣自谓今启非但是自处宜然,实为微臣往事,伏愿必垂降许。(卷22《豫章文献王传》)
(顾欢……上表曰:)伏愿稽古百王,斟酌时用,不以刍荛弃言,不以人微废道,则率土之赐也,微臣之幸也。(卷35《顾欢传》)
史臣曰:郁林王风华外美,众所同惑。伏情隐诈,难以貌求。(卷4《郁林王纪》)
太祖固让,与渊及卫军袁粲书曰:“下官常人,志不及远。”(卷23《褚渊传》)
3.记言体,即书中人物的对白。例如:或戏之曰:“谁谓庾郎贫,食鲑常有二十七种。”(卷34四《虞杲之传》)
僧虔涕泣曰:“吾兄奉国以忠贞,抚我以慈爱,今日之事,苦不见及耳。若.同归九泉,犹羽化也。”(卷33《王僧虔传》)
4.叙述体,即本纪、列传中史臣的叙述性语言。例如:
太祖高皇帝讳道成,字绍伯,姓萧氏,小讳斗将,汉相国萧何二十四世孙也。何子酂定侯延生侍中彪,彪生公府掾章,章生皓,皓生仰,仰生御史大夫望之,望之生光禄大夫育,育生御史中丞绍,绍生光禄勋闳,闳生济阴太守阐,阐生吴郡太守永,永生中山相苞,苞生博士周,周生蛇丘长矫,矫生州从事逵,逵生孝廉休,休生广陵府丞豹,豹生太中大夫裔,裔生淮阴令整,整生即丘令儁,儁生辅国参军乐子,宋升明二年九月赠太常,生皇考。(卷1《高帝纪·上》)
5.说明体,即“志”中史臣的说明性语言。例如:
天符瑞令,遐哉邈矣。灵篇秘图,固以蕴金匮而充石室,炳《契决》,陈《纬候》者,方策未书。启觉天人之期,扶奖帝王之运。三五圣业,神明大宝,二谋协赞,罔不由兹。夫流火赤雀,实纪周祚;雕云素灵,发祥汉氏;光武中兴,皇符为盛;魏膺当涂之谶,晋有石瑞之文,史笔所详,亦唯旧矣。齐氏受命,事殷前典。黄门郎苏偘撰《圣皇瑞应记》,永明中庾温撰《瑞应图》,其余众品,史注所载。今详录去取,以为志云。(卷18《祥瑞志》)
6.四言体,这类主要有庙堂歌辞、史臣的“赞曰”等,这些韵文大多是四言一句。例如:
皇帝升坛,奏登歌辞:报惟事天,祭实尊灵。史正嘉兆,神宅崇祯。(卷11《乐志》)
7.五言体,这类主要是民间歌谣等。例如:
永元元年,童谣曰:“洋洋千里流,流翣东城头。乌马乌皮袴,三更相告诉。脚跛不得起,误杀老姥子。”(卷19《五行志》)
8.赋体,这类主要是文人写的赋、铭之类。例如:
浮海至交州,于海中作《海赋》曰:盖言之用也,情矣形乎,使天形寅内敷,情敷外寅者,言之业也。(卷41《张融传》)
二、文体差异及其价值
《南齐书》中各种文体语言风格存在显著的差异。有的文体句式大多较短、变化较多,语言生动活泼、浅显易懂,对话感强,明显体现出口语风格;有的文体则句式整齐、长句较多、修饰较多、关联词较多、述论性强,同义词语极多、同义表达形式多,有时语义较为含蓄隐晦、甚至好用典故,体现出典型书面语的言语风格。文体与言语风格间的对应性也必然导致文体和语体之间有很强的对应性。吕叔湘先生曾说:“以文章体制而论,用语体最多的是记言之文,其次是记事文和说明文,又其次是抒情文和议论文。”[1]吕先生这里所说的“语体”,指的是“口语体”,也即通常所说“言文”的“言”。在研读《南齐书》的过程中,我们对吕先生的这种说法深有同感。《南齐书》的记言体“言”的成分最多,诏令体和议论体“文”的成分最多,而叙述体、说明体则介于二者之间。
《南齐书》丰富的文体为语言研究提供了一些便利,其主要体现是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古代文献中的语体分析。这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南齐书》独特的语料价值。
文体和语体之间有很强的对应性。我们对语料中的文体加以区别,将不同风格的文体中的语言项目作为取样的对象,进行相关的数据统计和频率分析,这样就可以得出语言中区分“言”“文”语体的重要参数。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统计语言现象在几种不同风格的文体中的分布情况,然后相互比较,以分析考察项目的语体属性。这种研究方法,可以称为“文体分布比较”法。
例如:我们对《南齐书》几种文体中人称代词、总括副词、处所介词及牵涉连词这四种二级词类的分布频率和功能进行了考察,由此可以看出它们在语体属性方面表现出的明显差异。从分布频率和功能上看,第一人称代词比较明显地分为两组:“我、身、侬”和“吾、余、予”;总括副词也比较明显地分为两组:“皆、都”与“并、悉、咸”;而处所介词引导的介宾短语,做状语和做补语这两种功能在文体中的分布也存在着对立。据此,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在语体属性上,上述三个方面中前者大致属“言”,后者大致属“文”。
通过语料中的文体的区分来研究语言成分的语体属性,这一作法无疑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我们过去进行语体属性的判断多凭语感。“凭语感来定性”是语言研究中常见的一种“内省法”,而当代的人们对于古代汉语,缺少的正是这方面的语感。即使是一些造诣很深的古文家,也不能保证他们具有与古人一样的语感,他们对于古人言语的理解也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失真”。这一方法即使在现代汉语研究中也常常会导致因语感差异而各执一词的尴尬局面。因此,我们认为,用可操作可验证的文体分布数据分析代替传统的“内省法”,可以说是方法上的进步。
“文体分布比较”的研究不仅可以从共时的层面帮助我们分析语料中的语体差异,而且可以从历时的角度帮助我们及时捕捉到某些语言演变规律的信息。我们知道,语言作为一种交际工具,其演变只能是渐进的。新的语言现象出现时,不可能一下子在言语社团全面展开,只能是先在某种语体中零星出现。《南齐书》文体的丰富性导致其语体较为全面,这样它就有可能及时记录到某些能代表语言演变规律的实际语言的新变化(尽管它也会有较大程度的遗漏)。例如,我们从《南齐书》中可以看出,人称代词的“身”在此期流行一时。
“身”的出现最早是在口语之中,是颇为“粗俗”的语言成分(有点类似于“老子”),因此一般文献中很少出现,就连同时代口语性较强的佛经中也很少见到。而在《南齐书》中,“身”共出现了12次,其中作主语7次,定语4次,兼语1次,均在记言体中。
从另一方面说,《南齐书》是一部正史,它的写作应该较少受到作者个人语言风格的影响,这样,它就能在较大程度上避免言语中的个体变异现象。因此,它所记录到的语言的新变化可信度比较高。这些体现发展变化的成分,在当时的语言中应该既是新的同时又已经是较为稳定的语言因素。这一点跟同时期的汉译佛经相比显现得尤其突出。在译经过程中,由于原典的影响和译经者水平的限制,这种受个体因素影响的言语变异现象会较多出现[2]。佛经中出现的许多属于言语变异的现象,很显然不能体现基于全民的语言的演变规律。因此,今天的研究者不应该把佛经中的言语个体变异和语言的演变混为一谈。与此相比,我们更可以看出《南齐书》一类正史在其中某些文体里所体现的语言变化信息的重要性。
三、史书语料的局限性及其应对
当然,我们在充分重视《南齐书》语料价值的同时,也应看到其局限性。总体上说,《南齐书》中“文”的成分要比“言”的成分多。在全书近20万字的文字中,属记言体的只有3万余字。不仅如此,另外在这3万余字的记言体中,也还存在这些特点。
一是在《南齐书》接近口语的语体中,“文”的成分还占有相当比例。例如:人称代词中的“吾”早在东汉佛经中就已罕见[3],在此期的佛经中也大体如此。但在《南齐书》的“记言体”中,“吾”的频率大体是“我”的四分之一。虽然口语中也有某些正式场合会用到“吾”,但即使将这一情况考虑在内,“吾”的频率也还是偏高。《贤愚经》中“吾”的频率在同期佛经中是很高的,但也不超过“我”的十四分之一。总括副词中的“并”也是这种情况,在《南齐书》的使用频率远高于同期佛经。因此无论是历时的考察还是共时的比较,《南齐书》“文”的成分还是较高。做正史语言研究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语言事实,通过对《南齐书》语体差异的语法表现的考察,我们对正史语言的“文”的特征有了更加具体的认识。
二是在《南齐书》接近口语的语体中,有些新兴成分的比例还很低。例如:总括副词中的“都”,在《百喻经》中的使用频率超过了“皆”,但在《南齐书》中却远低于“皆、并、悉”。处所介词此期有些新生的成分(如“著、到”)在《南齐书》中却难觅其踪影。这可以明显地看出《南齐书》在反映实际语言新变化方面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滞后性。同样是做正史语言研究,何亚南通过对《三国志》及《三国志裴注》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结论[4]。他认为《三国志》的某些语法特征在历时轴上与某些更早的文献相比显示出了较大的滞后性,与几乎同期的《裴注》的共时比较它竟然也有某种程度的滞后性。看来,研究史书的语言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史书这类语料在汉语史上的地位,也有助于我们认识一部完整的语料中存在着“言”与“文”之间的较强的不平衡性特征。
三是《南齐书》中“言”“文”语体在诸文体中有相混的情况。例如总括副词中的“皆”与“并、悉、咸”等,在典型书面语体中就有较为严重的相混现象。人称代词中的“我”混入典型书面语体时与“吾”等发生冲突,以至于它在典型书面语体中的句法功能频率高低格局产生变异。这又给我们对“言”、“文”语体的分析设置了障碍。必须使用一定的方法才能分离出其中的“言”、“文”区别,虽然这些差别是由于作者不经意中流露于文本的而具有很高的语料价值。有严重的“言”、“文”相混,说明史书的语言虽然的确存在着不同语体中所显现的“言”、“文”差异的两极,但在更大程度上却表现出了书面语体中的大面积交叉。这种大面积交叉不仅反映了正史语言所走的“中性”语体的发展道路,还反映了更多的非语言因素对史书语言语体风格的影响。这些非语言因素包括历来重文轻语的文章观,史书编写中的“正统”史学观[5]。
正史中的这种“文”多“言”少,及一定程度上的“言”、“文”混杂现象,给我们的“文体分布比较”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因此,我们在利用《南齐书》等史书来进行汉语史的研究的同时,还应该充分参考同期的其他语料。同期可资比较的语料,如《百喻经》、《贤愚经》、《杂宝藏经》和《世说新语》等可作为记言体的参照和补充。这些语料的时间都稍早于《南齐书》。《贤愚经》共13卷,元魏时(公元445年)慧觉等译[6];《杂宝藏经》共10卷,元魏(公元472年)吉迦夜共昙曜译[6];《百喻经》共4卷,萧齐(公元492年)求那毘地译[6]。这些语料的口语性,学界已有定论。吕叔湘先生[1]曾说:“初期的小说本来全文都近于语体,如《世说新语》是很好的代表。”方一新、王云路对此也有过论述:“由于多种原因(诸如为了便于传教、译师汉语水平不高、笔受者便于记录等),东汉以至隋代间为数众多的翻译佛经,其口语成分较之同时代中土固有文献要大得多,并对当时乃至后世的语言及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7]
[注 释]
①文中引例所据的版本是中华书局点校本《南齐书》(王仲荦点校,1972年1月第1版)。
[1]吕叔湘.文言和白话[A].吕叔湘语文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朱庆之.佛教混合汉语初论[A].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论丛》编委会.语言学论丛(第24辑)[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3]许理和.最早的佛经译文中的东汉口语成分(蒋绍愚译)[A].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论丛》编委会.语言学论丛(第14辑)[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4]何亚南.《三国志》和裴注句法专题研究[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5]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M].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6]吕 澂.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A].吕澂佛学论著选集[C].济南:齐鲁书社,1991.
[7]方一新,王云路.中古汉语读本[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