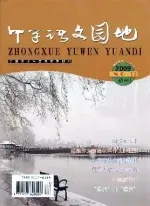梦失乐土
——论《边城》的幻灭感
赵 洁
1921年,一个叫沈岳焕的年轻人拖着疲惫的身体终于走到北京的前门时,他穿越了千山万水。从凤凰到汉口,从汉口到郑州,从郑州到徐州,从徐州到天津,从天津到北京,这个怀揣着与他的年纪不相符的沉重的少年,期待着上苍的眷顾,能让他有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他已经没有太多的奢望,只是想能够上大学,或者能当一名警察。
这时候的他还不知道,这一段少年的经历、这一份命运的沉重,会决定他用生命的激情与灵魂的感悟构建的湘西世界,这个用文字编织的亦真亦幻的世界,必将是一个充满挥之不去的幻灭感的世界。
1923年,沈岳焕改名为沈从文。这个来自于山野、走过万水千山、心中充满梦想与期待的年轻人,从此开始用他那独具审美特性的眼睛,描绘着他心中那个与现代文明社会渐行渐远而又与现实的湘西并不完全一样的乡土乌托邦。一方面,他试图在文本中挽留湘西的神话,努力构建一个充满自然人性与牧歌情调的世外桃源;另一方面,他又敏锐地预见到湘西世界无法挽回的历史宿命,从内心里知道其实这不过是一个业已失去的精神乐园。这个世界山青水秀,汉子勤劳纯朴,女人自然率性,他们身上涌动着勃勃的生命力,平凡的生活充满了无畏的勇气、缠绵的爱情以及上苍赋予的人性的勃发……然而,这个世界又是充满矛盾的,以沈从文的敏锐,他清醒地看到了自己笔下乌托邦的虚空。所以他总是以极其恬淡的语调渲染出最美的田园牧歌,而往往又以那不动声色的无常之手,使一切美丽在转瞬之间消逝。当我们还在费力地猜测他的用意时,他却躲在别人看不见的角落无奈地苦笑。从他的苦笑中我们知道,这世界并非乐土,或许这世界根本就没有乐土,有的只是宿命和幻灭,而且是最令人扼腕叹息的宿命和地久天长的幻灭。
永远回不来的梦境
1934年发表的《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展示给读者的是湘西世界和谐的生命形态。小说描写了山城茶峒码头团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与摆渡人的外孙女翠翠的曲折爱情。青山,绿水,河边的老艄公,16岁的翠翠,江流木排上的天保,龙舟中生龙活虎的傩送……《边城》中的一切都是那样纯净自然,展现出一个诗意的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然而,这一切都不过是一个永远也回不来的梦境,美好的一切最终只能存留在记忆里:天保与傩送一个身亡,一个出走,祖父也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死去,一个顺乎自然的爱情故事最后却以悲剧告终。在《边城》里,自然、人与社会是相互共存、融为一体的,呈现出一派和谐的富有诗意的气象。湘西封闭的地理位置和优美的山山水水使世代生活在这里的苗人养成了既野蛮强悍又憨厚淳朴的个性,边城人在自然中生长,爱这自然,更信奉这自然。翠翠,这个由竹篁的“翠色逼人”而得名,食天地之精华、受大自然造化的乖巧女孩,她是自然化的边城人的代表,也是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的女神。“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和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翠翠长大了,情窦初开的她喜欢把野花戴在头上装扮新娘子,喜欢摘象征着爱情的虎耳草。翠翠和爷爷、黄狗、渡船,还有那一片溪水相依为命,一同送迎日月,一起共度晨昏,这是一幅多么令人神往的美丽画卷。
《边城》里有关翠翠的描写特别动人和有意味,沈从文费了不少的笔墨来表现翠翠朴实真挚的情爱、情窦初开时对爱情的朦胧向往以及渴望幸福的健康情怀,“茶峒人的歌声,缠绵处她已领略得出,她有时仿佛孤独了一点,爱坐在岩石上去,向天空中一片云一颗星凝眸。”翠翠的灵魂因为梦中一种美妙的歌声而浮起来了,仿佛如烟的水雾轻轻地各处飘着,忽儿连着天上的云,忽儿接着地下的水,仿佛在问:哪里是可以落脚的地方啊?哪里又是生命永久的停驻?这美妙的歌声不仅包含了一个纯情女孩关于人生的全部美丽和梦想,实质上也是作家本人理想的寄托,我们分明地看见,在湘西这片清灵的山水间,在这个让人心绪惴惴的梦境中,翠翠的灵魂浮起来了,沈从文的灵魂也浮起来了。
《边城》的故事写得很美,美如童话。在这里,人世的苦难、内心的挣扎是没有的,有的只是人性的美和淳朴的民风。在这里,沈从文以他幽雅的笔创造出一个个闪耀着神性之光的理想人物,既是对人性中庄严、健康、美丽、虔诚的一种赞美,同时也是沈从文身上浓得化不开的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情怀的一次宣泄。正如他自己所说:“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的理想的建筑。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然而,纵观《边城》这个关于湘西苗民的“民族寓言”式的经典文本,随着故事的层层展开,它的整个调子也由和谐逐渐向变奏推进。在汉族封建文化的浸染和城市现代文明的侵蚀下,无可奈何的变化在悄无声息地进行,和谐的传统变调了,淳朴的人性堕落了,美好的风俗消亡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边城》又是一支悲哀的风俗挽歌。沈从文知道,由于现代文明已经渗透到边远偏僻的湘西,封闭的心灵已经渐渐地被侵蚀,昔日宁静和谐的生活环境与淳朴善良的民风都将难以维系,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也是脆弱的湘西文化在夹缝中生存的宿命。正如他自己所说:“生命在发展中,变化是常态,矛盾是常态,毁灭是常态。”面对这不可抗拒的破灭,他又能做什么呢?“惟转化为文字,为形象,为音符,为节奏,可望将生命某一种形式,某一种状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通过长长的时间,通过遥遥的空间,让另外一时另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无有阻隔。”他所能做的不过是以文字的形式构筑一座供奉人性的小庙而已!而更可悲的是,偏离时代主流的沈从文最后的结局却是连构筑小庙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他只得去研究古人的衣饰,在窥探和感悟人类另外一种形式的生命存在和延续中,销蚀他自己的生命……
永远回不来的梦境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我们读《边城》,读的是一个淡淡的故事,做的是一个破灭的春梦,或许还有感动,却不是因故事里人物的悲欢离合而感动,我们只是感动这梦境的逼真,让我们在日益平庸的生活中还有心灵停歇的片刻,为梦醒时继续这人生旅程提供必需的勇气,仅此而已。
摆不脱的宿命
在《边城》这个悠远的爱情牧歌中,人们恬淡自守,“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绅士还更可信任。”沐浴着湿润与和谐的水边小城,蓬勃着人性的率真与善良,文明社会古旧的礼法与习俗并不能阻挡自然人性的勃发,一切似乎都自然而然地按照应该的形式刻画着生命的轨迹。可是,这里发生的故事却并非如它的风土人情那样静穆平和。无论是翠翠,还是她的父母,冥冥之中总是摆不脱宿命的纠缠,尽管她们美丽、恬静、充满灵性,但她们的人生却同样的令人悲哀,他们的生命时时刻刻有一种发自肺腑的痛在缠绕。当生活中的各种情感都顺乎自然向前发展时,却有着这样那样的阴差阳错与偶然。由此,这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在爱情之外更容纳了现在与过去、生存与死亡、恒久与变动、天意与人为等诸种命题,在甜蜜而哀惋的糖衣下,充斥整个故事的是一种无奈的宿命感,就象沈从文自己说的:故事中充满了五月中的斜风细雨,以及那点六月中夏雨欲来时闷人的热和闷热中的寂寞。而这一股莫名的人间惆怅,似乎正是沈从文要传达的主旨,在一种渺远如春梦的意境中,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了他无法掩饰的对世界本体的忧郁之情,幻灭的感觉由此而生了。
在《边城》中,作者并没有直接叙述翠翠父母的爱情与死亡,而是从间接的叙述中,通过爷爷和杨马兵的回忆来让我们知道当年那个故事的。在翠翠这个温暖恬静的爱情梦的后面,她父母的非正常死亡始终就象一个符咒,时时笼罩在翠翠的头上,使得老船夫“因为翠翠的成长,使祖父记起了些旧事,从掩埋在一大堆时间里的故事中,重新找回了些东西。这些东西压到心上很显然是有个分量的。”这无形的“分量”也正是让人难以轻松的原因,翠翠会步她母亲的后尘吗?还是她会找到自己的幸福?
从爷爷的回忆中,我们知道当年翠翠的母亲也是个活泼、天真,“乖的使人怜爱”的摆渡女孩,她让人喜欢让人爱慕,连杨马兵也是给她唱歌的追求者之一,而翠翠母亲只爱那个 “穿起绿盘云得胜褂,包青绉绸包头”的绿营屯戍兵。他们“一个在半山上竹篁里砍竹子,一个在溪面渡船上拉船”。她不象翠翠那么害羞,她的爱热烈而执着,胆子大到公然在青山碧水间与情郎对歌。可是,这样一个生命力旺盛的姑娘为什么会放弃生命呢?还有那个强壮的戍兵,他放弃生命的理由又是什么呢?沈从文给我们留下了想象的足够空间,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去猜测,但是无论原因是什么,他们在相爱之前就一定是知道这个结局的,他们的命运早就横在前面等着他们了,那是他们分明绕不开,却又一定要尝试,终于还是没有能够过去的一道坎儿。也正是这道坎儿,才让我们真正心灰意冷地觉悟了什么是人生摆不脱的宿命。
在《边城》的故事里,好人不一定得到好报,有情人并不都能终成眷属。外祖父在雷电暴雨的夜晚身心交瘁地离开了人间,天保驾船离开了茶峒,不幸淹死,傩送也因此出走,只剩下翠翠一个人开始了遥遥无期并可能永无结果的等待。这等待,是翠翠的宿命,也是沈从文的宿命,更是一种饱含了伤痛的文化的宿命。
《边城》在讲述自然风俗美、人性美的同时,人物的命运和结局却是非团圆的、悲剧式的。因而,沈从文看似和平与淡然的背后却多了一份张爱玲式的苍凉和孤独,一个写人性美,一个写人性恶,看似截然不同,却又殊途同归,都有着对世事难料、命运无常、现实无奈的感叹与沉思。当我们用心体会《边城》文字背后的深刻意蕴时,这就已经不是一个人或两个人的苍凉与孤独了,掩卷而举目四顾,悲哀如影随形,我们总是不能明白,风雨过后,有什么还留在我们的身边,又有什么值得永久地眷恋……
“美丽令人忧愁”的境界
宿命的故事中,翠翠是主角,也是宿命的承载。因为这个缘故,翠翠点滴的生命充盈着残酷的美丽,沈从文用心地剥开这宿命的惆怅,展现给我们的是一派“美丽令人忧愁”的境界。《边城》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算做翠翠这个活泼兔脱的生命来到世间,在对现实世界的一步一步、一点一滴的认知和解读中获得灵魂体验的记录。这记录,其实也是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逃不出宿命的羁绊而挣扎的记录,只不过沈从文记录得很巧妙,明明是滴血的心灵在震颤,却让人在震颤中感觉到如歌的温馨,心甘情愿为了这超乎生命底线的震颤而付出一切。山水阳光浸染出的翠翠,美丽而天然,对世界充满好奇。人生刚刚开始,她不懂的永远比她已经懂的要多得多,于是她四处吸取着新鲜的经验,“大把的粉条,大缸的白糖,有炮仗,有红蜡烛,莫不给翠翠很深的印象,回到祖父身边,总把这些东西说个半天。那里河边还有许多上行船,百十船夫忙着起卸百货。这种船只比起渡船来全大得多,有趣味得多,翠翠也不容易忘记。”而过渡的新嫁娘,乡绅女儿手上的麻花银镯子,都使翠翠羡慕。象所有的女孩子一样,一天天长大的翠翠一不小心就受到了爱情的冲击,就象一大张洁白的纸,忽然有人在上面画了她不懂的画,她既惊奇又委屈,然而“翠翠不能用文字,不能用石头,不能用颜色把那点心头上的爱憎移到别一件东西上去,却只让她的心,在一切顶荒唐事情上驰骋。她从这分隐秘里,常常得到又惊又喜的兴奋。一点儿不可知的未来,摇撼她的情感极厉害,她无从完全把那种痴处不让祖父知道。”就象祖父的老不可避免一样,翠翠的成长也是不可避免的,在爱情的快乐与痛苦此消彼涨的过程中,她脆弱的心灵之弦被命运之神随心所欲地拨动着,忽然有一天,“屋后白塔已不见了。这一惊非同小可,……才知道白塔业已坍倒,大堆砖石极凌乱的摊在那儿。翠翠吓慌得不知所措,只锐声叫她的祖父……祖父还不作声。原来这个老年人在雷雨将息时已死去了。”时间是最折磨人的机器,时间不会因为祖父的死去而停滞。在过渡人的捐助下,白塔又造起来了,翠翠的日子还要一个个过下去,虽然还是等待着那个曾经月下轻歌的年轻人,可是此刻翠翠的心中,已经是别一样的乾坤了,她淡然而自在,不再是早前的一味惊喜和痴迷了。祖父不是白白死去的,他的死为觉悟的翠翠带来了新的自由和尊严,而这自由和尊严,正好满满地承载着沈从文对新人类的全部希望。
一开始,翠翠的成长似乎是她母亲的翻版,好象一个老旧的故事又重新被演绎。她一天天地长大,祖父也一天天开始为她的命运而担心。翠翠不会唱歌,甚至遇见喜欢的人也“同小兽物见到猎人一样,回头便向山竹林里跑了”,这就让人更加担心这个柔弱女孩的命运了。孤独中早熟的翠翠比普通女孩子更渴望爱情,而命运之神似乎也特别垂青于她,与傩送的初次相遇就两情相悦、坚定不移了。一个是非他不嫁,一个是非她不娶,都对对方充满了信心。当天保也喜欢上翠翠,甚至托人做媒时,弟弟却自信地说:“‘大老,你信不信这女子心上早已有了个人?’”在这之前,他们既没有互对山歌,也没有月下相会,只是凭着直觉相信这爱情的坚决。可是,年轻而稚气的翠翠还不懂,越是美好的东西被破坏的可能也越大,越是坚决的东西往往越容易遭受痛苦和磨难。当我们看到王团总要用一座新碾坊作为陪嫁,看中了傩送时,不由更加担忧起来,渡船竞争得过碾坊吗?这个担忧还没有平息,又传来大老落水身亡的消息以及顺顺父子对老船夫的误解,这接二连三人事的变动破坏了原来平和的境界,翠翠的命运变得前途未卜了,难道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悲剧吗?雷雨之夜,祖父去世了,船总顺顺在安排完祖父的丧事后也愿意把翠翠接到他家去,事情似乎峰回路转,傩送只是因为父亲逼他接受碾坊而赌气出走,而现在只要他回来不就皆大欢喜了。可是,“到了冬天……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甚至他“也许永远不回来了”。翠翠的眼泪还没有掉下来,旁观的人早已经双眼朦胧了。命运难道真的就这样捉弄人吗?那个月下轻歌的年轻人,你有什么样的理由不回来?
老旧的故事演绎到这里,本来就该结束了。当一切外在的原因消失之后,命运就充当了审判的角色,可怜的翠翠只能接受宿命的判决。但是,翠翠毕竟不同于她的母亲,她的生命已经开始觉醒。她拒绝了去船总家,而是自有主张的在那里等着爱人,因为他“也许明天回来”。这种等待的本身就是这个柔弱的女孩对命运的反抗,这等待让我们感到了灵魂的震荡。傩送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不知道,可是翠翠一定会等待下去,这种等待或许是一天,或许是一辈子。翠翠的等待也许是劳而无功的,可是这等待的本身就是充实而幸福的。她不象她的父母那样只能在永恒的天国里寻求庇护,而是勇敢地站在众人的面前等待着自己的幸福。她比她的父母更勇敢,她对命运的反抗也更激烈。我们读《边城》所有的惆怅惘然也终在翠翠的等待中得到了涤化,人的存在或许真的是悲剧性的,可是人存在的方式和过程却是威严而崇高,令任何力量也不敢轻视的。在这“美丽令人忧愁”的境界中,我们或许不懂人生的归宿究竟是什么,然而我们知道,对宿命无畏的抗争才是我们选择突显生命意义最好的方式!
幻灭的精神家园
在《边城》里,沈从文用三分之二的篇幅编织了一个美奂美仑的世界,然后在不到三分之一的篇幅里匆匆地交代了这种美无法实现的结局。这种美丽的残酷和梦想的破灭,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悲剧美学风格,表面上看恬淡明丽,本质上却是悲悯壮烈,这种内外的矛盾构成了极大的张力和冲击力,悲剧的不可避免性增加了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的美丽,而美丽的残酷和不复存在又加重了小说的悲剧意味,使读者轻易地就陷入了无边的怅惘。沈从文用他的笔让我们细细地体味着人生的残酷和无奈,却又让这漫长的人生充满了温存与美感,也许还会有一些孤寂或者忧伤。不论是翠翠,还是翠翠的父母,也无论是天保、傩送,还是摆渡老人和船总顺顺,所有这些在“美丽令人忧愁”的境界中来来往往的人物,在经历了一场如痴如醉、荡气回肠的悲情洗涤之后,留给我们的是一种美丽、一份崇高和一抹神秘的韵味,在我们的心头久久萦绕,咽不下,也吐不出,成为我们心中永远的一个结,一个缠绕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结。
我们读《边城》,翠翠的故事其实只是一个无关宏旨的载体,重要的是故事后面太多的梦想以及这梦想无可挽回的幻灭。《边城》的故事充满了人类的友善和道德的完美,然而沈从文在《长河题记》里说:“《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30年代,湘西根本就不存在《边城》这样的美好领域。”到这里,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了,小说《边城》以自身的存在构成了一种强烈的象征,它不仅象征了沈从文心仪神往的湘西世界无可挽回的必然衰落,而且暗示了他一向追求的重塑民族形象、重铸民族精神的良好愿望的无可奈何的破灭。同时,它还隐含了沈从文为民族、为整个人类的未来而焦虑的深深的忧患意识。在故事中,沈从文终于还是让那座象征着“正直素朴人情美”的白塔在风雨之夜倒塌了,塔的倒掉由此预示了一个田园牧歌神话的必然终结。这个诗意的终结,既是沈从文内心一个崇高而至美的梦想的幻灭,同时也是人类找寻精神家园最后努力的幻灭。白塔的坍塌,翠翠选择了无尽的等待;湘西世界的幻灭,沈从文选择了逃离;失去了梦想,我们这些沉醉于《边城》故事的人还有没有信心从容面对漫长的人生旅程?
在这个漂浮的越来越多、永恒的越来越少的世界,我们选择突显生命意义的存在方式,有很多时候真的是身不由己。可是,固执的沈从文终于还是义无返顾地逃离了30年代的文学主流,以至于在当时及以后相当长的一段岁月里倍受冷落。这是他自己选择的方式,这选择需要足够的勇气与定力。在此后的岁月中,他逃避,只是因为不愿在污浊中迷失自己;他淡泊,只是因为不愿为尘世的繁杂所牵挂。很显然,他的文学理想是寂寞的,这寂寞一如翠翠的孤独与寂寞;他的前途又是宿命的,这宿命也一如翠翠的挣扎与宿命。在《边城》故事的结尾,孤苦伶仃的翠翠怀着一颗“软软,酸酸的心”等着“也许永远不回来,也许明天回来”的傩送,这意味深长的等待包含了多少令人心痛和颤栗的迷惘啊!在这伤痛隐喻的背后,沈从文的孤独与其说是逃离,不如说是穿越,他穿越了政治,甚至某种意义上也穿越了文化,而直接达到了某种关于人类本体意义上的抽象理解。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让他的名字成为一座永久的丰碑!
不管怎样,最伟大的虚构就是最伟大的真实。沈从文承认《边城》是个悲剧,他说:“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这一来,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故事上,方得到了排泄与弥补”。出走湘西的沈从文终于找到了属于他的世界,一个充斥着虚无的世界,也找到了他宿命的流连。但是,他并没有向宿命妥协,而落入一种荒凉自闭的情景。相反,他有理想,有一份真实的期待,有一座高高的“希腊小庙”。这一种逃避与挣扎,使他超越了以往任何小说家的浅薄,而他对整个现实世界的理解和阐述,推动着人类对生命本质的无尽探索,所有这些,都将成为人类新的集体意识,汇入人类整体经验的河流而历久不衰,尽管也许我们并不知道这河流的归宿会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