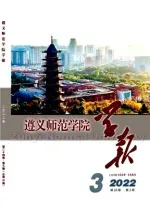美育:人性的复归之路
黄守斌,周 帆
(1.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系,贵州 兴义 562400;2.遵义师范学院,贵州 遵义563002)
美育的目的在于陶冶情感,净化灵魂,健全人格,培育完整的人,是教育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知识经济与工业化的背景下,美育呈现边缘化的趋势,人的问题诸如拜金、享乐、单面性等关于人性的异化成了严重的时代病。以美育实现对人性的救助开启人性的复归,是当下教育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美育边缘化与人性异化
加强审美教育在国内外得到了很多学者与教育家的关注。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早就对美育的意义及路径进行了极有见地的论述。著名美学家席勒对美育进行了系统化的理论构建,使人类再一次认识到美育的重要意义。席勒指出“古代社会人是一个具有完美人性的整全的人,工业文明之所以使人性分裂成为碎片,就在于人的情感为欲望所同化。”[1]王国维基于西方美育教育思想认识到美育对国内教育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具备真善美之三德……美育者,一方面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2]“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之有高尚纯洁之习惯。”[3]美育使人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故而高尚纯洁。虽然美育对人格的高尚、人性的完美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现实中美育还处在边缘性的尴尬境地。
在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大潮的冲击下,我们今天教育中的人被遮蔽了,教育不是成“人”教育,而是以消解个体理性自律的“成才制器”的规训化教育。一切都以市场为导向,教育的目的就是让学生有朝一日成功地在市场上出卖自己,人异化成了以物质衡量的商品。这里弗洛姆对其有深刻的描述:“人不仅仅出卖商品,而且还出卖他自身,他把自己也当作是某种商品。……像其它任何商品一样,是市场在决定着这些人的特质的价值,甚至决定着他们整个存在的价值。假如某人所具有的特质在市场上卖不出去,那这个人就毫无价值、分文不值。”[4]人的价值的市场化判断加速了学校基于市场价值的人的培养进程。加之工业文明的推进,人远离自己成为机器的一个部件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人类单面性的物化存在充溢整个人类社会,自由自觉的劳动成了节日的奢求。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写道:“要是我们必须用一句话来说明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的话,我们就会首先叫它是机器的时代……同样的习惯不仅支配着我们的行为方式而且支配着我们的思想和感情方式。人不仅在手上而且也在头脑里和心里机器化了。”[5]机器化提高生产率,人类可享受的东西越来越多,但是它带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我们有丰裕的物质,却没有愉快的生活。我们比以前更富有了,然而,我们缺少自由;我们比以前消费多了,然而,我们却更为贫乏空虚;我们有了更多的原子武器,然而,我们却越发不能防卫了;我们受到了更多的教育,然而,我们却越发缺乏批判性的判断力和信念;我们有了更多的宗教信仰,然而,我们却变得更加实利主义。”[6]在实用技术决定一切的工业文明中,个人成了无个性特征的机器,从而失去了主体性的本真存在,缺失了自己个性的丰富性,对社会控制的无情无义而无能为力,成为工业文明的奴隶,机器翻身成了奴隶主,主客的倒置成为了时代的常态,人类本体精神的客居直接降低了人的幸福感。
人文关怀的缺失引起的人性异化成了教育界与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柏格森一针见血地指出:“理性先天的具有不能了解生命的特性。因为工具理性是生命视角的向外,一切都以功利和实用作为评判价值的基点,作为人的本真存在的非功利的活生生的生命因理性工具无限扩充而没有了地盘,窒息的生命呼吁对科学与工具理性加以限制,至而开辟生命世界的诗性空间。精神生命的归乡成了当下人类共同的诉求,远古祖先朴实的诗性智慧成了拯救人类精神匮乏的灵丹妙药,当然它也是人类通往真正的人的世界的唯一桥梁。”[7]教育的片面性使诗性智慧处于尴尬境况,至而社会风气败坏、道德人性颓落成了当下社会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审美教育的边缘化所造成的。“当我们竭力耕耘于科学时,却忽视了伦理学,关于人类精神的心智及情感如何适应公民生活……它在我们手中几遭遗弃,甚至荒芜。”[8]可见培育人类精神的心智及情感,实现人性复归为当下教育紧迫的时代任务。
二、情感:人性复归的基点
美育对完美人性的复归有着基础性的建构意义,是因为审美教育的出发点在人的情感的培育。情感是人类心灵活动的形式,具有基于个体体验的特性。理性有了情感体验而沉淀为思想和灵魂,这种思想与灵魂使人具有灵动的人性,主要在让人回归自己和超越自身两个方面。
情感是以个人体验作为出发点的,并在爱与恨、情与仇、乐与喜、悲与欢等具体的情感状态中得以体现。它是建立在个体心理这一层面上的感性认识,伴随着具体情境中具有个性化的感觉、记忆、意愿、联想与想象等,是基于个人这一相对的封闭性中构筑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世界。由此,人在自己的情感体验中呈现了自身的历史性的当下存在,生活的那份诗意情趣全面展开。认识活动人总是以理性的固有路径寻找答案,社会性的无比强大人难以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久而久之人缺乏情感生活而显得枯燥乏味、精神空虚,因为作为认识的主体没有“变社会的评价为自我的评价。”[9]缺少自身内在体验的参与,主体成了认识活动中不是客体的“客体”。人作为一个精神的存在物,能使自身在内的一切都成为他的认识对象,使人成为人的正是这人的精神,也就是说在认识活动中没有自我的评价是不完整的认识,对人类精神高地的构建是不利的。马克斯·舍勒对精神一词作了一个有深度的界定:“精神这个词包括理性概念,另外,除了观念思维之外,它还包括对原始现象或本质内容的特定直观;同时,它还包括诸如善良、爱、悔恨、敬畏、心灵的惊奇、极乐、绝望和自由抉择等意志和情感活动。”[10]也就是说精神是一个整体性的存在,有社会的也有自身的个性体验。每一个社会人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每一个人又都包含了人类历史的全部内涵,精神有了自身的情感体验才富有诗性逻辑。诗性逻辑是自身的觉醒与发现,它抒写、描绘真人的真情实感,实现人对人以及对自身价值与尊严的肯定。而工业文明中占主导地位的工具理性对此基本无动于衷,实现人性的复归就成了难题,其危害是可想而知。“理性文化塑造的工业文明导致了自我的迷失,在现代生命是患病了,病于工业和机械主义的破坏人性,病于工人的非个人性,病于分工的经济学谬见。”[11]现代生命的患病是机器、物性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僭越。面对精神生命的贫乏,生命之美的衰败,尼采对此感慨颇多:“真的,我的朋友,我漫步在人中间,如同漫步在人的碎片和断肢中间……我的目光从今天望到过去,发现比比皆是:碎片、断肢和可怕的偶然,可是没有人。”[12]在碎片中我们难以找到自己的存在,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属于自己的真正的实质性的存在,人自然沦落为漂泊他乡的永久的客者。我们应实现精神对肉体生命的超越,复归精神的家园,在自身心灵深处拷问灵魂、反省行为提升人生的境界,找回本真的自己。
人的社会性存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人通过穿越自身的有限性而实现与他者的有效对接。作为生命存在的个体胜利进入他人的空间而意识到他者的存在,在这种社会性的情感体验中孕育了推己及人(物)的体验路线,做到“投身于旁人和众人的地位上,把同胞的苦乐当作苦乐。”[13]而对于一个冷漠的人他无法体验别人的喜、怒、哀、乐,更不用说基于与他者相似的情感体验而奉献自己的那份真情。这样的体验是超越自身在关系中实现的体验,是以主体的诗性智慧与客体敞亮为基础的,审美的大门由此而展开。审美是在关系中展开一种主客交融的情感体验。美学家狄德罗指出任何与人相关的美都是相对的,都要从一定的关系来断定。人的社会性关系成了揭开审美奥秘的一个重要维度,可以说“关系是真实人生唯一的摇篮。”[14]那么培养能够自律、善于与他人协调和替他人着想、热爱自然具有完美人性的人,也是离不开这种社会性的关系体验,通过主体与客体以朋友似的亲密关系而实现“我与你”的诗性逻辑。人作为一个在社会中构成的具有整体性的复合体,无论是社会性消融人的个性还是人的个性忽视了社会性都是不圆满的。情感生活支撑起了人性优美的大厦,它不为无节制的财富积累和物质享受所牵制,有效地冲破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这种以“爱”为基础的情感体验,是一种内在的深层的社会他者的影像和自身的体验的结合,而这二者永恒的完美联姻是情感,情感教育的最好路径非审美教育莫属。
三、美育:丰厚情感的基础路径
美育是基于情感的教育,情感的丰厚能使人在心灵的空间建立起一个生态的场域滋养人性,不时地体验那份“没有利害观念的自由愉快”,这种体验“既没有官能方面的利害感,也没有理性方面的利害感来强迫我们赞许。”[15]在这种无利害的关系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不对等地位消融了,变成互敬互爱中进行静观、对话的朋友关系,在精神上得以愉悦的同时人性品格也得到进一步的升华。由此社会中某种功利性就能化为自觉的力量,实现了自律与他律的和谐统一。这一切的实现是通过审美教育培养审美之人,其核心是在提高人对优美与崇高这两种典型的美的形式的感受能力实现的。
优美在形式上符合均衡、对称、比例、秩序、节奏、韵律及多样性统一等原则,主要表现为单纯、和谐与完整。博克从人类的生理心理出发,把人的基本情欲分为自体保存和维持种族生命的生殖欲及群居本能两类,后者就是优美,“是物体中能引起爱或类似于爱的情欲的某一性质或某些性质。”[16]如形体的小巧、色泽的鲜明、比例的和谐等。它们能使我们在不经意中对其产生喜爱之情,也正是因为这种喜爱之情使人心甘情愿地为之奉献自己的一切以至于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这基于“爱”的情感正是组成优美人性的内核,有了它人与人之间就会互相理解、同情。对于学生,尤其是以形象思维为主的少年儿童来说尤为重要,如果他们缺乏了这种根植与内心的爱的体验,日后将变成冷漠无情之人,以致产生嫉妒心理,更为严重的是对他人与社会的仇恨。这种人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一切以物性价值作为评判的准则。因为他难以体验也不愿去体验如流行歌曲《爱的奉献》所说的“只要人人都奉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只有通过对美好事物进行有效的审美教育,培养对美好事物的喜爱之情,才能实现“我与他”的主客二分模式向“我与你”主体间性的跨越。这一教育模式的认识在当下成了很多学者关注的焦点。教育家布贝尔曾大声疾呼:“教育的目的不是告知后人存在什么或必会存在什么,而是晓喻他们如何让精神充盈人生,如何与‘你’相遇。”[17]确实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为重要的是整个人的形成,应该以审美的方式引导学生去充实人生的精神,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与信任。而作为一个整体的人,人性品质固然是重要的标志,审美教育通过以品格为导向培养的是一种具有富于爱心与共生意识的“生态人”。这种富于共生意识的生态者正是由于“爱”而拥有了“诗性智慧”,其生活的方式与原则自然地遵照了“诗性逻辑”。用马克斯·舍勒的话说就是:“最深切地根植于地球和自然的幽深处的人,产生所有自然现象的‘原生的自然’中的人,同时,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的人。”[18]这样的生态之人与美的对象多了几份静观、对话意趣,多了几分天人合一的审美体验。“人看花,花看人。人看花,人到花里去;花看人,花到人里来。”[19]如此的审美情趣是人性完美的生态人在“主客”和谐共在中体验的那份精神愉悦与轻松。
除了美感,崇高是审美教育中更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崇高是一种“有赖于心灵做出努力或反应来同气派宏大或力量无穷的气象展开某种竞争。在这种努力或反应中,主体觉得自身肯定有了比通常经历的更深刻的精神力量。”[20]在表现形态上正好与优美相反,它以令人恐惧的形式与人形成对立的态势,对人的心理构成巨大的威胁,使我们深刻体验到自身的渺小,在强烈的震撼中它能激活人的生存意志而呈现出抵抗之力。康德举例对此进行了描绘:“好像要压倒人的陡峭的悬崖,密布在天空中迸射出迅雷疾电的黑云,带着毁灭威力的火山,势如扫空一切的狂风暴……,使我们的抵抗力在他们威力之下相形见绌,显得微不足道。但是只要我们自觉安全,他们的现状越可怕,也就越有吸引力;我们欣然把这些力量看做崇高,因为他们把我们的力量提高到超出惯常的凡庸,使我们显示出另一种抵抗力。”[21]在崇高对象的面前心存敬畏的同时,人实现了精神的升华,使我们获取一种超越惯常的抵抗力而战胜生活境遇中的艰难险阻,从而使人性显出阳刚之美,至而与阴柔之美的完整结合塑造人性的完美。西方对此尤为重视,“在种族历史和个人成长过程中存在一个完全的野性本能阶段:只有经历过低级阶段,才能进入高级阶段;只有领悟到过去的残忍,才会领略仁慈、善良、正义。”[22]这些对我们今天的教育界仍有现实意义,尤其是当下中国基础教育中由于女教师所占比重大,并极力倡导“以和为美”的境况下,男学生性格女性化严重,人性过于柔化而缺少血性之美,这是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只有通过“崇高”教育,人才能获得自由和尊严以及心灵的完整性的超越,这种超越不仅仅是停留在愉悦,而且包含一种基于敬畏的责任感。人只有在对自身有限性的超越中才能达到人生的真正家园:“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均无限隔,人可以安居其中,怡然自得。”[23]从而实现本真人性的复归。
结语:
美育是基于情感把人培养成一个完整的、具有诗性智慧的人的教育。其中优美与崇高是审美教育中重要的两部分,人缺乏了对美的感受能力,人的感性和理性之间的矛盾就难以调和;而崇高感的不足,人就会多了几分柔性而缺失阳刚之美而沉溺于感性之中而忘记自己的尊严。当美与崇高达成了契合无间,美育才能作为一个整体,在对物质有限性的超越中,实现人性的复归。
[1]席勒.美育书简[M].徐恒醇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4.51.
[2]王国维.论教育之宗旨[M].北京:中国教育出版社,1996.146-147.
[3]蔡元培.蔡元培美学文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70.
[4]弗洛姆.逃避自由[M].陈学明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161.
[5]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M].董乐山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97.59.
[6]弗洛姆.人的呼唤—弗洛姆人道主义文集[M].毛泽应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80.
[7]柏格森.诺贝尔文学奖全集[M].北京:三联书店,1983.178.
[8]维科.维科论人文学教育[M].张小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40.
[9]雅科布松.情感心理学[M].王玉琴译.哈尔滨:黑龙江出版社,1998.154.
[10]马克斯·舍勒.人在宇宙中的地位[M].陈泽环译.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43.
[11]周国平.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115.
[12]尼采.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M].楚图南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5.143.
[13]雪莱.为诗辩护,19世纪英国诗人论诗[M].刘若端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29.
[14]布贝尔.我与你[M].陈维刚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24.
[15]康德.判断力批判[M].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出版社,1964.46.
[16]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237.
[17]布贝尔.我与你[M].陈维刚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60.
[18]马克斯·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M].罗缔伦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226.
[19]金圣叹.鱼庭闻贯·金圣叹全集[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
[20]鲍桑葵.美学史[M].张今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9 6.
[21]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370.
[22]刘晓东.儿童精神哲学[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299~300.
[23]张世英.进人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