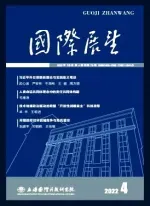中日关系进入新的历史转型期——兼论两国增强战略互信的路径选择
吴寄南
中日关系进入新的历史转型期
——兼论两国增强战略互信的路径选择
吴寄南
中日两国在明显增多的不和谐噪音中迎来了邦交正常化40周年。人们注意到,近年来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巨大进展的同时,一些结构性的矛盾与对立逐渐凸显。中日两国缺乏战略互信已成为影响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最大障碍。一定要从战略高度认识和把握中日关系的大局,扩大两国共同战略利益的交汇点,克服彼此间的隔阂和疑虑,将中日关系推进到新的阶段。
中日关系 历史转型 战略互信 路径选择
1972年9月,中日两国在克服重重困难后终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揭开了两国关系的新篇章。40年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持续开展交流与合作,取得了令人欣喜的巨大进展。但是,从近年来两国间风波迭起的现状来看,中日关系距离孔子所说过的“四十而不惑” 似乎距离甚远。本文拟就中日关系进入转型期后的基本特征、导致两国间矛盾与对立日益增多的深层原因以及如何增强两国的战略互信,提出一些粗浅的想法。
一、中日关系进入历史转型期的主要特征
回顾邦交正常化 40年来的历程,中日关系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成长期”、“磨合期”和“转型期”。第一阶段指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两国全面开展交流与合作,“中日世代友好”是两国民众耳熟能详的一个口号。第二阶段主要指冷战结束后的90年代。随着两国交流交往的不断深化,彼此间的龃龉与对立也日渐凸显。第三阶段则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最初10来年,也许还更长。这是两国重新定位和调整相互关系的重要历史转型时期。
新世纪头10年里,中日两国在各自加快经济、政治转型过程中先是相互进行战略摸底,继而围绕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发生了战略对峙。从2006年10月起中日两国高层进行了名为“破冰之旅”、“融冰之旅”、“迎春之旅”和“暖春之旅”的一系列互访,两国关系一度出现全面回暖的趋势。但是,新世纪刚刚进入第二个10年,以2010年9月的钓鱼岛撞船事件为标志,两国关系再次出现了不和谐噪音此伏彼起,龃龉与对立增多的局面。
近年来,中日关系呈现出如下三大转型期的特征:
第一个特征,两国间交流、合作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彼此都已成为对方不可或缺的战略伙伴,但国民间却出现相互疏远和亲近感下降的趋势。
首先看经贸关系。1972年,中日双边贸易总额只有区区10.8亿美元,2011年却跃为3428.9亿美元,增加300多倍。而且,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中日双边贸易额占日本外贸总额的比例几乎是第二位的日美贸易总额的2倍。日本在华直接投资累计金额超过了800亿美元,是中国除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外最大的外资来源地。2011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额达63.3亿美元,比上年增加55%,创历史新高。中国对日本的直接投资也方兴未艾,2007年至2010年,对日直接投资累计金额增加了20倍。目前,中国是日本国债最大的持有国,而日本启动日元与人民币实行直接兑换,在主要发达国家中首开先河。
两国间的地方交流和人员交流也呈欣欣向荣的态势。目前,中国各省市与地方各都道府县乃至市、町间缔结的“友好城市”共有 250对,分别占中国对外结好城市的首位和日本对外结好城市的第二位。1972年两国的人员往来不到1万人,两国间甚至还没有一条直通航线,2011年两国的人员往来增加到528万人次。其中,日本来华人数为365.8万人次,中国赴日人数为162.3万人次。每天都有100多个航班往返两国的20多对城市间。据日本法务省统计,到2010年底,在日中国人已达65.7万人,超过在日韩国人、朝鲜人的总和成为最大的外籍居民群体。而在中国长期居留的日本人也有13余万人。其中,上海是海外日本侨民最多的大城市。
但是,与这种交流、合作的扩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两国国民感情出现了逆向发展的趋势。日本内阁府每年发表外交舆论调查。被调查者对中国有亲近感的比例在1980年约为78%,仅次于美国;上世纪90年代大致保持在50%左右;2010年却跌至20.0%,创下这项调查开始以来的最低记录。2011年12月公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是26.3%,仍属历史最低水准。①(日)内阁府:“外交舆论调查”,2011年12月5日发表,见内阁府网页:http://w ww8.cao.go.jp/survey/h23/h23-gaiko/2-1.html。2012年6月20日,《中国日报》社和日本言论NPO共同实施的第八次“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结果正式揭晓。调查结果显示,两国国民对对方国家的亲近感都降到了8年来的最低点。中方调查显示,对日本印象不好的占64.5%,低于2011年的65.9%,但高于2010年的55.9%。日方调查显示,对中国印象不好的占84.3%,比2011年高出6个百分点,比2010年高出12.3个百分点。中方调查显示,认为中日关系“非常好”或“总体来说比较好”的比例为42.9%,比2011年下降11.6个百分点。日方调查显示,认为中日关系“非常好”或“总体来说比较好”的比例仅为7.4%,比2011年的8.8%还要低。由于受样本数和设问的限制,民意调查的数据是参考性的,但严峻的现实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②“2012年日中联合舆论调查”(记者招待会资料),日本言论NPO、《中国日报》,2012年6月20日,第5、24页。
第二个特征,两国高层密切往来,政治领域的对话日趋制度化,并就长期、健康、稳定发展中日关系形成了一系共识,但两国间矛盾、冲突逐渐由感情对立趋向领土主权之争。
从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的天皇皇后和中国国家主席分别访问了对方的国家,这是2000多年的中日交往史上所不曾有过的。两国政府首脑一级的互访以及在国际会议期间的会晤呈日趋频繁的局面,建立了一系列对话和磋商机制。40年来,两国间先后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1972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78年)、《中日联合宣言》(1998年)和《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2008年)等4份政治文件。这4份政治文件是两国领导人政治智慧的结晶,是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础。
世界上任何一对双边关系的发展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中日关系也不例外。两国从邦交正常化以来一直是在风风雨雨中前进的。不过,以往两国间的对立多由历史认识问题而起,例如修改教科书,将对华侵略改为“进入”、参拜靖国神社,美化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等等。这些事件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也违背了日方在邦交正常化时有关的表态。但相比之下,围绕钓鱼岛主权归属的争端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中国方面无法妥协和容忍的。2010年9月发生的钓鱼岛撞船事件,日方非法拘捕中方船长,甚至扬言要按照日本的国内法进行审讯,蓄意制造日本“法理占有”钓鱼岛并行使司法管辖权的既成事实。这自然引起了中国的强烈反弹。两国间战略互信随着日本加强对华防卫态势,陷入轮番下跌的恶性循环。特别是2010年底,日本出台了新的《防卫计划大纲》,提出“动态防御”的概念,将防卫重点转向临近台湾及钓鱼岛的所谓“西南诸岛”。2011年度的《防卫白皮书》更是将中国定位为地区安全的“忧虑事项”。进入2012年后,日本挑衅中国的频度和力度明显加强,诸如默认反华分裂团体“世维会”在东京召开“四大”、热炒“购买”钓鱼岛以及酝酿对钓鱼岛实施“国有化”,等等,均触及到了中国核心利益的“红线”,将两国关系推向冰点。
第三个特征,两国关系的发展日益超越双边关系的局限,共同为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作出贡献,但两国间的战略博弈也逐渐从双边关系的领域溢出到了地区和全球层面。
早在1972年邦交正常化时,两国领导人就明确表示,两国的邦交正常化,发展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也是对缓和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贡献。1978年8月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规定:中日“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1998年11月发表的《中日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则强调“中日两国作为亚洲和世界有影响的国家,在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方面负有重要责任”。2008年5月问世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更进一步地提出:“中日关系对两国都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肩负着庄严责任。”显然,两国领导人已经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彼此作为亚洲主要大国的责任,中日关系已开始超越双边的层次。
事实上,邦交正常化后的这40年里,中日两国共同为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主要是联手抑制苏联对亚太地区的扩张,防止地区冲突的扩大;90年代则是共同推动印度支那半岛由“战场”走向“市场”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进入新世纪以后,两国在推进“10+1”、“10+3”以及中日韩三边关系的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而且,两国不仅各自关注和投入湄公河流域的开发,而且从2008年起每年都召开副部长级的中日湄公河政策对话,在援助该地区的环境保护、保健卫生、人才培养等领域加强政策协调和相关合作。此外,中日两国在肯尼亚开始实施共同的援建工程。有关对援助拉美的中日政策磋商也已揭开帷幕。
但是,与两国在地区和全球层面的合作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近一时期日本某些政要正试图将中日间的分歧与对立引向多边舞台,甚至在国际范围内拉帮结伙、牵制中国。2012年6月2日,野田内阁的防卫副大臣渡边周在新加坡香格里拉会议期间,声称中国的军费增长幅度让周边国家感到不安,是日本的“威胁”。这是日本政要第一次在国际会议的场合公然鼓吹“中国威胁论”。与此同时,日本在外交和军事领域展开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活动。首先是在深化日美军事同盟的同时,加大在军事上拉拢韩国的力度,拼凑针对中国的“亚洲版北约”。尽管日韩情报合作协定陷入难产,但近期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高调参加美韩在黄海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旨在增强美日韩三边同盟中的日韩“短板”;其次,提升与菲、越、印等与中国存在领土纠纷的国家的双边关系,从首脑互访、举行联合军演,到提供巡视船,训练海上警备力量等。日本的政治家和主流媒体并不讳言这些动作是为了“牵制中国”。两国间的战略博弈显然已从双边关系的领域溢出到了地区和全球层面。
种种迹象表明,迎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的中日关系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风险。如果听任上述这些消极因素蔓延滋长,势必会迟滞和影响两国间日趋密切的经贸交流和民间往来,使中日关系偏离正确的航向,出现停滞不前甚至漂流、倒退的局面。
二、中日关系中消极因素滋长和蔓延的深层原因
中日关系在即将步入“不惑之年”时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扭曲现象,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人们比较容易理解的,自然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侵华战争的后遗症。这种负的历史遗产造成两国民众间严重的信任缺失。受害的一方总是怀疑加害者是否真正悔罪、认错,而加害者则担心受害的一方会不会“秋后算账”。不过,从根本上来说,中日关系之所以会在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又会出现龃龉增多、风波迭起的局面,应该说是两国在变化了的国际国内环境下相互重新定位和调整关系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具有一定结构性特征的问题。
从深层次看,中日关系中消极因素滋长和蔓延可以归结为以下三大因素:
1.中日两国处于力量对比发生“世纪逆转”后的心理调适期,日本国内日渐抬头的对华惊愕、嫉妒、警惕和怀疑的思潮导致少数政治家在处理对华关系时采取非理性的行动。
在新世纪的头 10年里,中日两国的力量对比呈逆转趋势:中国迅猛崛起,越来越有自信,而日本则逐渐被中国追赶乃至反超,越来越缺乏自信。2010年由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首次超过日本而成为极具象征性意义的一年。虽然中国的人均GDP还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但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仍引起了强烈的心理冲击。日本学者将2010年称为“世纪逆转的一年”。问题还不仅仅如此,从上世纪 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一直处于增长乏力甚至持续滑坡的局面,“失去的十年”演变成“失去的二十年”、“失去的三十年”。与此同时,日本政局也不断出现动荡,内阁更迭犹如走马灯一般频繁,民众中弥漫着一股强烈的挫折感和失落感。英国BBC的调查表明,中国民众是受访亚洲国家中对未来的经济前景最乐观的,而日本则是受访亚洲国家中对前途最感悲观的。①“BBC调查:62%中国人对经济前景乐观”,《环球时报》,2011年11月6日。
中日两国的GDP排序易位后,双方都需要经历一段心理调适期。如果说中国一下子还不习惯被推到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央,缺乏思想准备的话,日本人则不敢相信一二十年前还远远落后于自己的中国,居然会硬生生地夺走日本“世界第二”的桂冠。在震惊之余,难免会产生惊愕与嫉妒相交织、警惕与疑虑相纠结的反应,他们既担心中国可能对日本过去的侵略行径进行“秋后算账”,也担心强大起来的中国重新将日本贬为自己的附庸。用一位在日华人学者的话来说:“日本的对华心态正处于这样一种复杂而扭曲的状况”。②朱建荣:《丰田在中国的求索——奥田硕与朱建荣对话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8页。这就导致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非常容易引起摩擦与对立的敏感时期。
近年来,日本社会出现的一系列乱象都与这股思潮有关。漫步日本的书店,陈列在畅销书柜台上的热门书籍要么是渲染中国危机重重、即将崩溃,要么是强调中国威胁日本和世界,是新的“亚洲盟主”、“超级霸权”,等等。而报刊和电视报道中则大量充斥着有关中国的负面报道,以渲染中国的落后与失败取悦读者和观众。政治家们则动辄对中国说硬话、狠话,将自己包装为对中国敢说敢为的“斗士”来凝聚人气和支持率。从2010年钓鱼岛撞船事件后一些政治家的激烈反应来看,日本的政治家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已经失去了原本还有的那么一点点自信和从容,甚至连起码的外交礼节也置之脑后。例如,时任外相的前原诚司指责中国在钓鱼岛撞船事件后的应对是“歇斯底里”。③“前原发言让中国气愤难平”,《朝日新闻》,2010年10月23日。几十年来日本外相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说过这么重的话。进入2012年以后,日本朝野的不少政治家在钓鱼岛问题上竞相升高指责中国的调门,鼓吹在岛上兴建灯塔,驻扎自卫队,强化日本非法占有的态势。
2.民主党执政团队中“少壮派”集团推行外交冒险路线,用提振民意支持的国内政治需要绑架日本的外交政策,致使日本执政当局在处理对华关系时陷入一味强硬的死胡同。
2009年9月,民主党取代自民党掌控了日本的最高权力。但是,这个成立仅仅13年,又长期在野的政党严重缺乏执政经验,多数人只熟悉民生问题,对外交和安全保障问题比较生疏。这就给党内的“少壮派”集团特别是松下政经塾出身的政治家提供了施展拳脚的活动空间。民主党两大派系“凌云会”、“花齐会”的主帅前原诚司和野田佳彦都是松下政经塾的毕业生,他们麾下也有不少松下政经塾的同门弟子。松下政经塾诞生于1979年,以“培养建设新国家的日本领导人”为宗旨,其毕业生多半以信奉新保守主义著称,与自民党内的“鹰”派议员的政治理念毫无二致。松下政经塾毕业生中担任国会议员的共有38人,其中28人在民主党。2009年9月民主党掌权后,仅鸠山内阁中就有 8名松下政经塾的毕业生出任大臣、副大臣和政务官,远远超过他们在民主党议员中所占的比例(7.08%)。而且,前原诚司任国土交通大臣,野田佳彦任财务副大臣,都是位高权重的。菅直人继任首相后,前原改任外务大臣,野田则升任财务大臣,在决策层内的地位进一步上升。2011年9月,野田佳彦接过菅直人卸下的担子,成为历史上第一位松下政经塾出身的首相。
松下政经塾出身的政治家共同的特点是年少气盛,血气方刚,擅长演讲,惯于作秀,但最大的弱点是缺乏社会历练,行事莽撞而不顾后果。例如,前原诚司于2005年12月以民主党代表身份访华,竟不顾起码的礼节在北京发表演讲称中国是日本的“现实威胁”。2010年9月发生钓鱼岛撞船事件后,前原身为指挥海上保安厅的国土交通大臣,亲自下令逮捕船长,扣押审讯,是这次事件的始作俑者。①“前原:是我下令逮捕的”,《朝日新闻》,2010年9月28日。菅直人改组内阁时,前原改任外务大臣,继续用在野党时期惯用的冲撞路线来应对这场风波,一味强硬的结果导致中日关系急剧降温。野田佳彦是松下政经塾第一期毕业生,在民主党“少壮派”中堪称“老大”。他在就任首相初期以“泥鳅”自诩,在处理对华关系时比较谨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鹰”派政治家的色彩日渐显露出来。最典型的例子是他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日韩第五次峰会期间,在与温家宝总理会谈时居然提出要和中国讨论“人权问题”。这是背负侵华战争包袱的日本历届首相刻意回避的话题,野田却毫无顾忌地说了出来。此外,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提出“购买”钓鱼岛的主张后,野田始则回避表态,继而推波助澜。特别是在小泽一郎率众出走后,民主党执政团队面临的政治压力日益加大,政治运营陷入困境,野田便铤而走险,在 7月 7日这个极其敏感的日子宣布了将对钓鱼岛实行“国有化”的方针。这固然是为提升民意支持度、化解政治危机的对策,也是他一贯主张强化对钓鱼岛“法理占有”的必然结果。野田罔顾中日关系大局,挑衅中国领土主权的核心利益,导致中日关系再度跌回冰点。
3.日本执政当局配合美国高调重返亚洲,加紧构筑防华、遏华战略联盟的需要,在美国的怂恿、支持下,加大了在外交和安全保障领域“对美一边倒”的力度。
中日两国间横亘着一个日美同盟。这就使得中日关系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双边关系,而一直是与美国息息相关的。日本是美国在亚洲的主要盟国,在外交和安全保障领域从来都是唯美国马首是瞻的。中美关系发展顺畅,日本就有较大的活动空间,而一旦中美交恶,日本就不得不与中国拉开距离甚至踩上一脚。美国在处理与中日这两个在亚洲拥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大国关系时,一向是以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出发点的。一方面,美国处心积虑地要在中日两国间保持适度的紧张。防止这两个大国走得太近,导致自己在亚洲被“边缘化”;另一方面,它又担心中日两国的分歧与对立严重失控,甚至擦枪走火,使自己卷入一场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中。不过总体而言,美国对盟国日本更放心一些,也更接近一些。在中日美构成的三边关系中,日美这一边自然要比另外两条边要短一些。这也是美国为什么要对倡导“疏美入亚”路线的鸠山由纪夫百般施压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原因。换句话说,日本在发展对华关系上究竟能走多远,完全取决于美国。
奥巴马上任后,鉴于过去10年美国深陷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减少了对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经济增长最快最富有活力的东亚地区的关注,开始逐步将战略重心向东亚转移。在美国眼里,已崛起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中国是唯一有能力挑战其霸主地位的竞争对手。但由于中美两国经济上相互依存,双边贸易额仅次于美国和加拿大,加上美国自身的硬实力软实力明显下降,它已经不能单独遏制中国。于是,它便采取拉帮结伙的办法,构筑防华、遏华的战略联盟。策略之一是强化它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的双边军事条约;策略之二是借口维护所谓的“航行自由”,唆使东盟中的个别国家将南海问题多边化、东盟化和国际化,压缩中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空间;策略之三是利用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经济战略伙伴关系协定”(TPP),打乱“10+3”、“10+6”的进程,对正在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巨大影响的中国进行牵制。美国高调重返亚洲的这三大策略,招招与日本有关,而日本的当权者也是亦步亦趋,紧紧跟上。
近一时期,日本国内在中日关系上的噪音明显增多,其源盖出于美国“重返亚洲”的这一战略调整。自然,美国对日本在外交和安全保障领域的“对美一边倒”也予以奖赏和鼓励。即以钓鱼岛问题为例,美国过去一向小心谨慎地避免介入。1972年2月,时任总统安全助理的基辛格曾明确提出,让钓鱼岛问题沉寂下来最符合美国利益。1996年,美国驻日大使蒙代尔表示,美国在有关钓鱼岛的争端中不会选边站,钓鱼岛不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①《纽约时报》,1996年9月15日,转引自http://d.hatena.ne.jp/asobitarian。但是,2010年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国防部长盖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等政要却异口同声地宣称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美国将“非常坚决地支持我国在该地区的盟友日本”。同年12月,日美两国在毗邻钓鱼岛的九州岛大分县海域举行了以夺取被占岛屿为名的两栖军事演习。2012年,美国更破例允许日本借用美军在毗邻关岛的提尼安岛派驻由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组成的联合部队进行训练和演习,并有意将其升格为自卫队的常驻基地。②“日媒称日本自卫队将首次在美国领土设驻留基地”,2012年4月19日,见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j/2012/04-19/3831005.shtml。这显然是给日本当权者“对美一边倒”路线的一种奖赏。
三、未来增强中日战略互信的路径选择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互为对方最重要的周边国家,也是对各自发展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国家。中日两国不仅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共同的挑战和课题,在促进东亚地区的稳定和繁荣方面也存在着共同的利益诉求和战略需要。如前所述,《中国日报》和日本言论NPO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出两国民众对对方国家观感严重恶化、普遍不看好双边关系的现状。但是,这次民意调查也传递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中日双方的被调查者中认为中日关系“非常重要”和“总体而言比较重要”的分别占到 78.4%和80.3%。①“2012年日中联合舆论调查”(记者招待会资料),日本言论NPO、《中国日报》,2012年6月20日,第28页。这应该是未来改善两国关系最深厚的民意基础。
鉴于中日两国缺乏战略互信是影响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最大障碍。那么,怎样在两国隔阂和疑虑加深的情况下增强战略互信呢?
首先,要加强两国高层间的信息沟通,避免战略误判。
中日两国应该通过领导人互访以及政府间的各种磋商机制,包括正在酝酿建立的海上联络机制等平台,展开多层次、多渠道、高密度的信息沟通。彼此将自己的战略底线清晰地告诉对方,坦承回答对方的质疑与关切点。除政府首脑外,两国的知识精英、意见领袖也应展开密切的信息交流、思想碰撞和战略对话,就双边关系和各自内外政策及国际形势加强沟通,准确地对对方国家进行战略定位,客观、理性地评价对方国家的发展趋势,消除各自对对方国家发展方向的不安感、不信感。总之,要尽量摆脱相互猜疑,避免形成“安全困境”。这是避免战略误判,缩小“信任赤字”的关键。
其次,要忠实履行两国间的政治承诺和共识。
忠实履行两国间的政治承诺和共识对提升彼此间的战略互信至关重要。回顾这40年来中日关系的跌宕起伏,凡是忠实地履行了两国间的政治承诺,双边关系就前进,反之就会出现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就以当前中日间对立最尖锐、也最容易引起对抗的钓鱼岛争端问题为例,邦交正常化谈判时中日两国领导人曾就钓鱼岛问题达成“暂时放一放、留待以后解决”的重要谅解。①唐家璇:“继往开来,共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新局面”,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单位联合召开的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2012年6月23日。见http://www.mfa.gov.cn/chn/gxh/tyb/zyxw/t945274.htm。1978年10月25日,邓小平在东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再次提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个问题。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个问题。……我们认为两国政府避开这个问题是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十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一代人缺少智慧,谈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下一代人肯定比我们聪明,一定会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②田桓主編:《戰後中日關係文獻集(1971-1995)》。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第249頁。正是由于两国间有着搁置争议的默契,中日关系在这些年来才取得喜人的进展。然而,从2010年钓鱼岛撞船事件以来,日本政府背离了两国间达成的谅解和共识,转而采取否认争议的强硬立场,严重扰乱了中日关系的大局。当务之急,是要回到中日关系的“原点”,拿出不逊于前人的政治魄力和勇气,排除干扰,管控分歧,提升中日两国间的战略互信。
第三,要彼此照顾对方的核心利益和战略关切。
关于这一点,邓小平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考虑国家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③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的谈话,引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30页。我们在把握和处理中日关系时也要有这样的胸襟和气魄。要照顾到对方的核心利益和战略关切,要照顾对方的舒适度,要耐心开展对话,坚持通过协商解决,不应无谓地激化矛盾。不能唯我独尊,一意孤行,甚至为谋求眼前的、狭隘的政治利益,把对方逼到不得不出手反击的地步,给两国关系带来干扰和伤害。
第四,要推动两国民众的相互理解和友谊。
中日友好归根结蒂是两国人民的友好。两国间的战略互信也必须构筑在民众间相互理解和友谊的基础上。目前,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和社会都处在重要的转型期,社会思潮日趋多元化。互联网的发展不仅加快资讯的传播速度,也终结了传统的信息单向传输模式,使得“草根层”的声音越来越对舆论导向和政府决策发挥影响。但两国意见领袖和大众传媒在舆论导向上仍拥有不可替代的影响。能不能以客观、理性、包容、深入的报道修正两国民众的认知误差,关系到两国民众间能不能增进相互理解和友谊,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营造良好的氛围。在当今中日间矛盾与对立相对凸显的时期,两国政府一定要注意准确地反映民意,引导媒体扩大对对方国家的善意报道,促进两国各阶层人士广泛开展民间交流,超越狭隘的民族情绪,逐步增加对对方国家的亲近感和信任度,夯实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民意基础。
历史经验证明,中日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损”。长期友好合作是两国唯一的选择。所以,两国为增进战略互信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从战略高度认识和把握中日关系的大局。在中日间四个政治文献的基础上,不断扩大两国共同战略利益的交汇点,克服彼此间的隔阂和疑虑,努力实现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目标,共同为东亚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
s
Sino-Japanese Relations Entering into a New Transitional Period:Discussion on the Choice of Path to Strengthen Mutual Strategic Trusts
WU Jinan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
D822.331.3
A
1006-1568-(2012)05-0001-13
China and Japan have celebrated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normaliza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apparently growing discordance. Noticeably, the great progress the two countries achieved in their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in all realms in recent years came along with highlighting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and antagonism. Lack of mutual strategic confidenc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s become the largest obstacle to the otherwise sound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China and Japan must read and grasp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from a strategic point of view, expand the convergences of their common strategic interests and overcome the estrangement and suspicion between each other, before they will advance 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to a new stage.
-- Китай" --" --верный шагк углублению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 国际展望的其它文章
- 发展融资体系概览
- “欧洲形势与中欧关系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