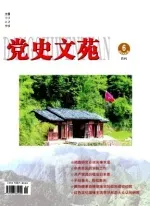军事统帅的人格力量是部队战斗作风的灵魂
朱和平
85年前的南昌起义,是在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革命后,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为挽救革命,向国民党打响的第一枪。这次起义像一声春雷,使千百万革命群众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严重挫败后,又在黑暗中看见了高高举起的火炬。南昌起义虽然大部分失败了,最后仅剩下我的爷爷朱总司令带领的800多人。但正是这800多人组成的最后火种,艰难奋战,最终成为我军的基础,战斗力的核心。
为什么南昌起义能保留下最后的火种?多年来,许多党史、军史专家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有党对军队的领导,有江西和两湖地区农民运动的基础,有国民党军阀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都为当时十分弱小且缺乏军事经验的共产党人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今天,我从亲人的视角,仅从爷爷的人格力量这一点作些分析。
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钢铁般的意志
10月3日,周恩来宣布起义失败。恰恰是南昌起义的失败,使爷爷面临历史的机遇。爷爷在南昌起义时没有基本部队,主力第十一军8个团由叶挺指挥,第二十军6个团由贺龙指挥,爷爷当时是第九军副军长,只是空架子,手中的部队只有教导团的3个连加南昌公安局的2个保安队,共500人。三河坝分兵是第二十五师(周士第、李硕勋)和部分第二十四师人员。当时部队已溃败,起义时成立的各级党组织到10月已崩溃,所有师、团领导人均已离队,军事干部只剩下第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政治干部只剩下一个团指导员陈毅。林彪当时说:“现在部队不行了,一碰就垮,与其等部队垮了当俘虏,不如现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在这最艰难的时刻,只有具备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钢铁般的意志,才能力挽狂澜。当时,爷爷坚定地对大家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也失败了!但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他还说:“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会有办法!”
陈毅后来说:“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朱总司令的伟大!”陆定一评价爷爷:“当危难到来的时候,他就表现出革命军人的真价值。他坚如磐石,定如山岳;为人之所不敢为,行人之所不敢行。”
我军主要高级将领很多出自这800多人或者是后续加入到这支队伍中的同志,正是由于他们在危难之中共同树立起了坚定的理想信念,才能使他们走过千山万水,身经百战,屡蹈死地而后生。他们已不是普通的军人,在跟随爷爷多年的耳濡目染中,已经把爷爷的这种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战胜困难的坚强意志,融化在自己的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并且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
清醒的头脑和过人的智慧
爷爷是一位头脑清醒并具有大智大勇的军事统帅。在南昌起义前,他已对中国革命特别是军事斗争有了深刻的认识。爷爷后来在延安时说:“(1913-1915)我用以攻击敌军而获得的绝大胜利的战术,是流动的游击战术,这种战术是我从驻在中法 (越)边界跟蛮子和匪徒作战的经验中得来的。”1925年爷爷在苏留学,曾回答教官:“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4月20日即杀害了爷爷的挚友孙炳文同志。南昌起义前,爷爷曾专程去武汉看望孙夫人任锐,遇房师亮,房问:“怎么办?”爷爷坚定的回答:“上山打游击!”从这些可以看出,爷爷对未来共产党将要进行的武装斗争,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既有理论上的探索,也有实践上的积累。他的游击战争理论和实践,是在南昌起义十几年前开始的。
三河坝保卫战是会昌之战后爷爷独立指挥的战役。此次战役,爷爷以三四千人的兵力,阻击装备精良的蒋介石嫡系钱大钧部2万余人。爷爷果断放弃三河坝镇,把阻击战阵地巧妙地放到韩江对岸,利用江面天险,与敌激战3个昼夜,最后在敌人三面合围的情况下,率领剩余部分批次顺利撤出包围圈,胜利完成了掩护主力进军潮汕的战役目的。这次战役是一场“非常精彩的、形败实赢的胜仗,创造了中国战史上的一个奇迹和典范”。
三河坝脱险后,爷爷开始调整我军的战略战术思想。通过上堡整训,确立了“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也就是打游击战的问题,并把“一线式战斗队形改为人字形战斗队形”,等等。在战略方向选择上,他并没有带部队去攻打大城市,而是与范石生合作,积蓄力量,并把目光盯住湘南地区。1928年1月21日,爷爷率部智取宜章,拉开了湘南暴动的序幕,随后一鼓作气,发动石坪战役,用1个团的兵力一举歼灭了赫赫有名的许克祥的6个团。石坪战役不仅扭转了我军被动局面,更使游击战与运动战的理论与实践基本成型,并首次打出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的旗号。虽然只有短短的3个月,但是湘南暴动建立了6个县苏维埃政权,涉及20多个县,100多万人口,并初步形成了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农民赤卫队三位一体的武装力量格局,部队编成3个师、2个独立团,为后来的朱毛井冈山会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朴实的作风和身先士卒的风范
爷爷在加入共产党之前,曾在旧军队中打拼十多年,对旧军队中官商勾结、兵匪一家、欺压百姓、打骂士兵等恶习深恶痛绝。加入共产党后,爷爷一直在为如何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而努力探索。爷爷认为: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必须要同旧军队有本质的区别,不仅要解决为谁扛枪,为谁打仗这个根本问题,而且还要建立起新型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对内对外关系。
在南昌起义前,爷爷利用创办军官教育团的机会,改革旧军队的用人制度,在挑选中下层军官时,先经过测验,再到广场逐个考试军事实地的指挥能力,然后按他们的实际成绩,分别委任相应的连、排职务。这种量才任用的做法,杜绝了旧军队中的裙带关系,也为后来红军的各级指挥员的培养积累了经验。据当年参加过军官教育团的徐震球回忆:“朱德对学员非常关心,吃饭同大家一起在大食堂里,晚上查夜给学员盖被子。教育团实行说服教育,严禁打骂,军官、学员一律平等。星期六野外演习,往返五六十里,朱德有马不骑,让给体弱或临时生病的学员乘坐,自己同大家一同走路。处处以身作则。”军官教育团不过三四千人,在南昌起义2万多人中仅仅是个零头。但正是以他们为骨干的队伍,在起义后异常艰难困苦的环境下没有溃散。
在爷爷的带领下,我军从南昌起义前夕就开始形成“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经过后来的“赣南三整”,军队中的党组织进一步加强,编制进一步精干,作战思想更加明确,又增加了做群众工作的内容,使我军具备了人民军队的雏形。从那时起,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军从最高统帅到普通一兵,基本上都是同等的生活待遇,这一新型的内部关系,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与国民党的军队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抗战期间,爷爷作为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八路军总司令,和普通士兵过着同样的生活,身上并无一文钱。1937年9月27日,他给前妻、我父亲朱琦的养母陈玉珍奶奶的信中说:“我们的军队是一律平等待遇,我与战士同甘共苦几十年,愉快非常,我为了保持革命军队的良规,从来没有要过一文钱。”当他从自己的外甥许明扬口中得知他的两位母亲(生母和养母)都健在,已过八十高龄,四川老家正值荒年,难以度日时,心中万分焦虑,无奈之中,只能写信给他川中好友戴与龄借款200元钱寄到家中,并告知:“我十数年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此。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你作捐助吧!”戴与龄接信后才知道,爷爷这位令日寇闻风丧胆的八路军总司令竟如此两袖清风,连救助老母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内心感动不已,当即筹足200元钱,送到爷爷的老家。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支军队,特别是一支装备很差、没有后勤并以步兵为主的军队,最高军事统帅的人格力量往往会成为这支部队战斗作风的灵魂。毛泽东在评价南昌起义时曾说:“这支部队十分原因中,有九分是靠个人的领导才能得救的!”
85年后的今天,我作为朱总司令的孙子,能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领导和专家学者们一起,共同学习、缅怀和研究我军在创建初期的这段历史,倍感亲切。希望能从老一辈把握历史机遇的传奇经历中有所启迪,在新世纪、新阶段,把握新的历史机遇,在党中央领导下,努力推进我军的现代化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