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怎样写散文
○赵勇
有一次,冯小刚见刘震云腰里挂着一串钥匙,便手指其腰间,郑重其事地说:“摘下,像一大队会计。”(参见冯小刚《我把青春献给你》,P16)记得读到这里时,我会心一笑,马上想到自己多年也是一个大队会计。为了淡化会计形象,我裤兜里装一串,裤腰里别一串,分而治之,很见成效。
大概因为如上原因,今年8月见到张暄时,我对他腰间的那串钥匙产生了浓厚兴趣。那串钥匙拴在钥匙链上,浩浩荡荡,叮叮当当。心中不免暗想,这哪里是大队会计,分明是在公社当差嘛。我问他何以有这么多钥匙,他就给我讲那些钥匙的去处:哪串钥匙通向家里,哪串钥匙在办公室落户,还有哪串、哪串……好家伙,他居然在裤腰带上建起了分类系统,实在是高。
我要谈张暄的散文集《卷帘天自高》,却首先说起了他那串钥匙,完全是因为书里的描述激活了我的记忆。这本散文集中有一篇《防盗门》,说的是修家里防盗门的事情。写到最后,张暄说:“此门共两个锁孔,六套钥匙,每套钥匙两把。一把钥匙小些,专事开关镶嵌在门页上能伸缩两个锁舌的门锁;另一把大些的,能扭转安装在门页里并从不同方向伸缩并松贯门框的钢筋。”这里的描述一下子让我明白了他钥匙多的原因。你瞧瞧,光是他家的防盗门就与众不同,居然有一大一小两把钥匙。而另一篇《临时工陈钟》也写到了钥匙。陈钟丢三落四,常常把钥匙忘锁在打字室里。于是“我驱车过去,开门,数落他几句,教给他我带钥匙的方法:一条链子拴了系在裤子上,裤带上穿一个钥匙扣挂钥匙,开门时只需把钥匙从扣上取下来,而钥匙还被链子拴在裤子上。这种挂钥匙的好处就是,只要裤子在,钥匙就在,双保险,万无一失。”读到这里时我笑了,我又想到生活中的张暄一定是个精细人。估计他的办公桌拾掇得井井有条,书桌也整理得纹丝不乱。不像我,只要是桌子,那上面准是垛着几摞书,小山似的,结果是我常常找不到要找的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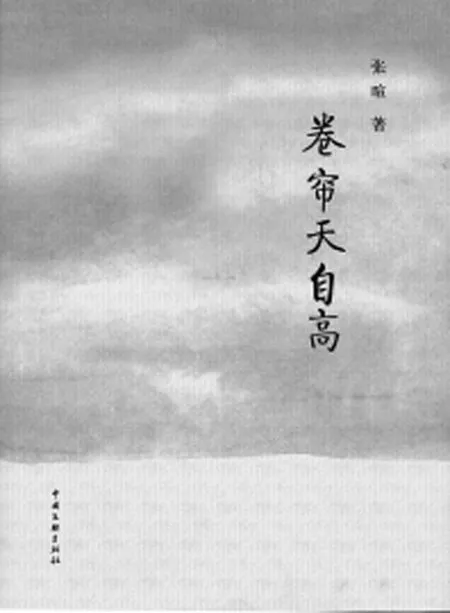
《卷帘天自高》,张暄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年版
或许正是生活中的这种精细成就了张暄观察的仔细,也让他笔下呈现出一种描述的细腻。他写10岁左右的男孩坐自行车,“正坐”需要更高的技巧:“在跃身起跳的时候,得让一条腿抬高跨过后座并骑乘之上,像是在从侧面跳一个跑动着的鞍马。”(《自行车》)这种写法一下子会击中许多中年男子,让他们的记忆蠢蠢欲动起来。他写狼,小狼被淘气的孩子敲打着叫唤,母狼身体轻微地震颤。“然后,我真切地看到,一滴眼泪缓缓地从它眼睛里流了出来。它的眼睛外围有一块发白的毛发,那滴眼泪淌过那块白色区域,渗入它通体的毛发之中”。(《最后的狼》)这种描写,一下子让人意识到狼也是有感情的动物,它在疼痛、无奈和绝望时的表现或许与人并无太大区别。他写书签,居然能生发出如此思考:“书签是善意的休止符,是对读书活动的一种间断,或者说是对两次读书活动的承续,这种承续貌似无意,却有着颇具内涵的积极力量。所以在这本书里,它很少有机会发挥自己本质的用处。它的身体,呈裁纸刀模样。更多的时候,我让刀尖伴随目光划过那一行行文字,或者在沉思的时候,绕于指间,掠过皮肤、嘴唇,感受想象中的刀锋。”(《书签》)这枚有着特殊造型的不锈钢书签是张暄的爱物,他拎着派不上用场的书签读完了年轻时读不进去的《复活》,书签也仿佛经受了一次名著的洗礼。像这些描述与思考,我就觉得十分妥帖,让人过目不忘。这里显然有细描的功劳。
散文虽然有种种写法,但我觉得大体而言,可分为内向型和外向型两种:前者是对内心宇宙的逼视,故所叙所描,多与自我的生活与思想有关;后者则是对外部世界的摹写,故用笔常常在自身之外。这本散文集,张暄虽然也写到了自己,但更多的时候却是在写别人,写外界。有时他写的是一处场景,有时写的又是一种物象,而更多的情况下,他写的则是一些陌生和熟悉的人。比如,那位卖袜子的老妪,推销演出票的“漂泊者”,怒气冲冲的“怨妇”。这些人只是偶然与作者发生了某种联系,却被张暄逮了个正着。而几笔下去,她们又能活脱脱地站在你面前。我暗自琢磨,散文若去写陌生人,难度其实是很大的。因为你对那些人并不了解,全看你有无瞬间捕捉的能力,就像摄影记者那样。张暄敢去写陌生人,说明他有一种自信。
那么,熟悉的人就好写吗?我觉得也不好写。有时候因为太熟悉,你甚至不知从何处下笔。像陈钟、老王(《排队》)、老莫(《老莫开车记》)、卓然(《卓然的幽默》)、老樊(《与老樊闲坐》)等,这些人与张暄或者交道多多,或者交情很深,他们往往从一个侧面,一个片断进入了张暄的散文,或者说张暄只是截取了这些人最有神采的一个或几个瞬间。比如,他笔下的那个老莫我也认识,老莫开车出事的那个地点我甚至更熟悉一些,因为我那位村里的朋友就是在那个水泥隔离墩上出的事故,离开了人世。散文中,作曲家老莫开着一辆破车在我家乡的道路上走神违章掉轱辘,本来可恨可笑,但张暄一写,极度喜欢开车、且把开车看作人生最大享受的老莫却变得可爱起来了。读他这篇散文,我的脑海里总会浮现出一个吉普赛人的形象。这说明通过张暄,老莫可能已充分文学化了,他变成了一个文学形象。
其实,不光是老莫,进入张暄散文中的好些人总会让我想到小说里的“刻画人物形象”之说,这大概与他的散文写法有关。张暄既写散文又写小说,有时散文就带上了小说的笔法。对这一点他并不避讳。他在自序中说:“最初的《临时工陈钟》,就有编辑说像小说。到了《母子》、《小心眼儿》、《最后的狼》等篇,几乎完全称得上小说了。回头来看,不过是顺从兴致,加了虚构,浓化了情节,就成了这副模样。”我虽然对散文的看法比较保守,觉得散文不应该虚构,但张暄以小说笔法去写散文,确实又写出了许多新意。像《临时工陈钟》,就显得舒展大气,收放自如。这么说,莫非跨文体写作有一些道理?
张暄是我晋城老家的一名警察,起初做刑警,后来当交警。2009年春节我初次认识张暄时,只是觉得他有一种警察才有的干练和精气神,而这一次读他的散文,又让我意识到他还有一种侦探心理,这是不是也与他的职业训练有关?这本集子中有篇散文写到了我本人,张暄从读我的散文集《书里书外的流年碎影》说起,然后纠结于我究竟有没有本事。经过一番铺陈和考证,他终于在书中的一幅图片里找到了答案。那张图是一封信,放到书里后,图片上的字已小得不好辨认,但张暄还是从那里摘出了一段话。由于我当年的中学老师在信的末尾说过:“当一个教授多好啊!我们所追求的就是当教授,不当书记和官僚。”张暄便说:“原来赵勇的‘没本事’,是被这帮人害的!”(《从〈碎影〉里扯出来的闲话》)记得当时为书找图时,偶然发现我还保存着30年前中学老师的这封信,很是惊奇。而由于写到了这位老师,我就把他的信放在那里,图与文之间的内容并无必然联系,但张暄却从这封信里抠出了他所需要的东西,就像警察发现了一个人的犯罪证据。他的这个发现甚至也让我吃了一惊,于是我想到,虽然这封信早已被我遗忘殆尽,但30年前的那番教诲是不是已经进入我的潜意识,以至于我在“没本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成了一名潜藏多年的逃犯?我藏着掖着装着,却还是被目光如炬的警察看出了破绽。这样,在遥远的“教唆犯”和今天的“罪犯”之间,他便成功地建立起一种严密的逻辑关系。那一刻,张暄俨然就是福尔摩斯,你不服都不行。
说张暄有一种侦探心理,我当然不是在骂他。因为我觉得,好作家其实都有一种侦探心理。唯其如此,他才能不放过生活中的蛛丝马迹,也才能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由此我便想到,张暄那种细致的观察、细腻的描摹、对笔下人物的准确定位,还有那种冷静从容的叙述方式,或许都与他的职业习惯与侦探心理有关。凭着这种习惯和心理,那些很容易被人忽略的场景、物象、片断、人物的瞬间等,才能进入他的散文。而如此一来,他的散文也就变得与众不同了。
《卷帘天自高》是张暄的第二本散文集。据他说,他最近几年主要是在写小说,散文并没怎么去刻意经营。他不光写小说,而且也不断通过读小说来提高自己的写作技巧。我们一见面,他总会给我推荐一些小说。听着那些陌生的书名和同样陌生的作者姓名,我就愧从心头起,就觉得自己研究大众文化多年,果然把自己鼓捣得没了文化。比如,这本集子里写到的舍伍德·安德森的《暗笑》,他最近推荐给我的《逃离》(艾丽丝·门罗著)和《大眼睛的女人》(安赫莱斯·玛斯特尔塔著),我就没听说过。后两本小说我已买回来置于床头,正准备补课。记得我的一位大学同学读过张暄的一篇博文后说:“向张警官表达敬意!一个读麦克尤恩的警官,值得我们敬佩。”我现在也想说,一个懂得不断用文学阅读丰富自己、武装自己的作家确实是值得敬佩的,因为他还知道自己的不足,还在偷偷丈量自己与这些优秀作家的距离。而这种阅读、揣摩、丈量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他进步的过程。我想,等张暄再读了一些好小说也再写了一些好小说之后又生产出一批散文,它们一定会有一种新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