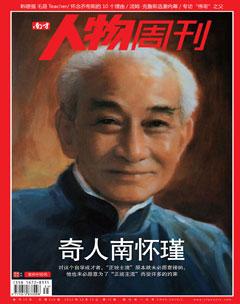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离去
骆平
父亲喜爱甜食,晚年更甚,像蛋糕、糖果这样甜到发腻之物,他是来者不拒,大口饕餮,如稚童一般。据说嗜甜的人性情温和、乐观、缺乏攻击性,父亲便是如此。今年中秋的月饼,父亲却是没能品尝,农历八月十二,他因心肌梗塞遽然离世,享年76岁。
父亲是长子,少时家贫,夜半祖母常拥他落泪。那时父亲就读于一所教会小学,学校有规定,凡考试获得第一名者,免学费。年幼的父亲为祖母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到第一。从念书第一天起,直到大学毕业,父亲在历场考试中,始终都是第一名。
最小的叔叔诞生时,父亲已经19岁。祖母哭泣着,欲将这第六个孩子送予别人,父亲拦下了。当时父亲已经考进大学,他不顾素昔的要强,到学校说明情况,申请补助,每个月徒步一个多小时,将钱送到家,养活弟弟妹妹们。
纵然家贫,父亲的仁善却与生俱来。祖母一度以卖饭为生,前来就餐的都是贩夫走卒之流。祖母一早去米店赊米,卖完结算,而利润微不足道,不过是剩下的饭菜勉强够一家人果腹,这利润显然还是隐藏在精细微妙的切与分之间。每遇父亲操刀,面对那些下苦力的顾客,黄瘦的脸与汗水总是让他不忍,下手总有失偏颇,卖到末尾,不仅没有剩余,反致本钱不保。
分数的一流与内心的悲悯,或许并不适宜管理者,在其后漫长的行政管理生涯中,父亲为他的优秀以及善良所困,行进得千辛万苦、步履维艰。缘于勤奋,他像一名秘书那样熬更守夜地撰写公文,加班是常态的工作方式。他的手下无比信任与依赖他。家庭问题找他,经济困难找他,子女读书找他,父亲是有求必应。
说不上来像父亲这样的领导是成功抑或失败,他的工作业绩是显著的,然而他的每一次提拔和晋升都是艰难的,领导层态度暧昧,并不常常赞赏他,因为他不是阿谀之人,他的性格黑白分明,没有那个圆润的灰色地带。
父亲做官做得辛苦,连累了母亲,母亲在家事与工作间忙得焦头烂额。父亲不是细腻体贴的丈夫,但他有一颗柔软博大的为父之心,出差时,会到商场为我买一套新衣裳。上了高中,我倍感学习压力巨大,情绪低落,父亲无论多忙,每晚必定抽空陪我散步,路过学生食堂,为我买一串糖油果子抑或香酥的锅盔。我挽着他的胳膊,吃着零嘴,海阔天空地乱侃一气,心里觉得考分差强人意也不要紧,我依然可以是一个幸福的女孩子。
父亲担任了三十几年的高等教育管理者,在退休的时候依然渴望继续工作,这却是规则以外的愿望,是不被允许的,他的继任者限他速速清空办公室,父亲不得不落寞离开。
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花甲之年的父亲决定创业。他进入一家大型民营企业,老板宣称,要组建一所高质量的民办大学,以社会公益为惟一目的,不谈赢利,这与父亲的梦想不谋而合。父亲与几位大学教授在企业中热血沸腾地干了一年多,这几个在体制内形而上地拼搏了几十年的老知识分子见识了体制外形而下的名利场,黯然退出。那所海市蜃楼的大学宣告解体。
接着,父亲说服了母亲,与另一个朋友一起投资办一所中专,最终学校经费不足,草草结束,父亲去办注销手续,发现学校的注册人是那个朋友,而非朋友当初信誓旦旦的承诺注册父亲的名字。用寡言的母亲的话来形容,父亲在退休以后,遭遇了前半生从未遇到过的各种形形色色的骗子。
创业失意,父亲打算认真规划他的老年生活,老当益壮,锻炼、健身。他选择了骑自行车,骑着车,到公园里溜溜,到书城去逛逛。可是,拥挤的交通、冒失的马路杀手,能有一条让七旬老者安全骑行的道路吗?全家人捏着一把汗,反复告诫他当心当心再当心。终究,还是出事了。父亲被一个飞车青年撞倒,对方哭诉,说自己是在校大学生,身上没钱,父亲心软,放了他,自己忍着剧痛,叫了一辆三轮车,颠簸十余公里,回到家中。我们连夜送他到骨科医院,拍片出来,大腿髌骨骨折。为这一摔,父亲一动不动地足足躺了半年。
卧床折磨,诱发了父亲的老年痴呆癥。他在世的最后4年,在一家收治痴呆病人的医院里度过。病情发展迅速,他不再认得老伴和女儿,直到弥留,我轻轻唤他:“爸爸,你要坚持,过了今天,就会好起来的。”闻言,他似安心,双目微合。这一次,他被最宠爱的小女儿欺骗了。父亲的明天,不复再来。
父亲这一生,从来没有世故过,从来没有精明过,甚至,他从来没有真真正正地衰老过,他一直都在理想主义的光影中飞翔,也因此在现实的坚壁间伤痕累累。幸而,不论成败,不问是非,在人类的终极命运面前,众生平等,绝无例外。我想,父亲清洁与光明的灵魂,脱离了现世的污浊,在天堂的细草与繁花中,终将安息,终得不朽。
——给祖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