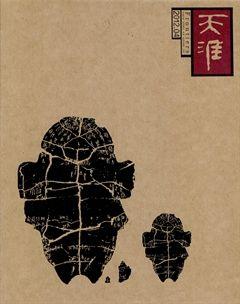走进安详:找回中国人的生存意义
若干年前,我得了一种怪病,遍寻良医均不得治。就在我心灰意冷的时候,上苍让我碰到了一位高人。那是一次想来有点传奇色彩的邂逅。故事的过程不在此赘述,单表结果,那就是折磨我多年的顽症居然被他治好了。
许多亲戚朋友问我,那人到底用了什么灵丹妙药,竟有如此神效?我说,说来你们也许不会相信,他开给我的全部药只是一个词:安详。
他说,所有的疾病都来自非安详,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单位,一个国家,要想康泰就要长养安详之气。
我问如何才能安详?
他说,安详有许多层次,获得安详是一生的事情。
我请教他,就我而言,当下应该怎么做?
他说,读安详的书,做安详的事。
病急乱投医,带着试试看的态度,依教奉行,不想身体果然渐渐好起来;两个月后,折磨人的病痛基本消失;半年后,我成了一个让大家羡慕的健康人,生活和事业也顺起来。
安详是一种不需要条件作保障的快乐,换句话说,它是一种根本快乐、永恒快乐、深度快乐,它区别于那种由对象物带来的短暂快乐、泡沫快乐、浅快乐。
那么,人如何才能走进安详呢?以我近年来实践安详的心得体会,有以下几个途径。
通过“给”走进安详
“给”就是把我们能拿出来的那份物力、体力、智力奉献社会,并且不求回报。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融化“自我”这块坚冰,清除这一通往安详道路的最大障碍。
一个人要想走进安详,首先要和天地精神相应。
而“给”,就是天地精神。
阳光、空气、时间、空间都是免费为我们提供的。有人收取土地出让金,但是大地本身没有收取;有人收取水费,但是水本身没有收取。
为此,天才长,地才久。
当年鲁哀公问孔子他的弟子里谁的境界最高,孔子的回答是颜回。因为他“不迁怒、不贰过”。孔子为什么要首先強调不生气呢?当年搞不清楚,后来突然明白了。人为什么会生气?生气是因为自我被冲撞啊;人在什么情况下不生气?无我啊。那么,如何才能无我?利他是一条最重要的途径。
我们且不要说像颜回那样完全消灭自我,就是尽可能地弱化自我,快乐也会成倍增长,因为烦恼和焦虑来自患得患失,而要消除患得患失,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掉得失心。
而要去掉得失心,就要向天地学习。
日月无言,昼夜放光;大地无语,万物生长。
放光,又无言;生长,又无语。
当我们尝试着把能拿出来的那份财物给更需要的人,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对财物的占有欲就降低了。渐渐地,我们就能体会到钱财的得失不再对我们造成很大的焦虑了。同时发现把财物给急需的人更有增值感,这种增值感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这样,附着在财物上的那个“我”融化了,另一个“我”诞生了,它就是本我。
这时,我们就会明白,所有的痛苦都是因为“小”造成的,宇宙、苍生、人类、国家、家族、家、小家、本我、大我、小我,层层隔离,逐次成“小”。为了捍卫这个“小”,焦虑产生了,痛苦产生了。
可见痛苦是因为我们心的“小”。这是我的,那是我的,得到喜,失去苦。一个宝物,到了我家,我高兴,到了别人家,我沮丧。但在“整体者”看来,放在谁家都一样啊。
可见,分别越小痛苦越小,分别越大痛苦越大。
反之,当这个“小”按照小我、大我、本我,小家、家、家族、国家,人类、苍生、宇宙这样的次第扩展,来自小我的焦虑便逐次削弱,直至于无。
可见,这个“小”是被“分别”出来的。
现在,我们反其道而行之,通过把自我认同的财富、力气、智慧给予他人,我们的心量就打开了、扩大了,结果是,焦虑消失,安详到来。
对于一个村落级心量的人,家的得失已经不会对他造成焦虑了;对于一个世界级心量的人,村落的得失已经不会对他造成焦虑了。而对于一个以“大整体”为家的人,已经不需要作“回家”想了,终极归属的焦虑自然消失了。
实践上一段时间,我们会发现,“给”的方式更加润物无声,比如一个公益倡导,比如一个公益访谈,比如给世人做一个好榜样,比如用“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引动更多的人去给予,等等。
再实践上一段时间,我们还会发现,在“给”别人的过程中,我们有了力量感,还有包容感、温暖感、自愿感。这时,我们就懂得了什么叫“量大福大”。事实上,量大也会力大。我们才知道,真正的力量是与我们的心量对应匹配的,这大概就是古人讲的“大则势至”吧。
无疑,最究竟的“给”是点亮他人的心灯,帮助他人找到本有的光明。在长篇小说《农历》中,我写到这么一个故事:盲尼夜行,观音菩萨让她掌灯避人,不料还是被一个和尚撞了个满怀,盲尼说,难道你就没有看到我手里的灯吗?和尚说你手里的灯早已灭了。盲尼当下开悟,原来任何外面的光明都是不长久的,靠不住的,一个人得有自己的光明。
通过“守”走进安详
“守”是让心归到本位,让行归到伦常。
要让行归到伦常,就要首先搞清楚什么是缘分和本分,这我在《<弟子规>到底说什么》一书中有过专门阐述。
而要让心归到本位,就要回到现场。
更多的时候,人的心不在现场,所谓“神不守舍”。许多错误和灾难都是在神不守舍时发生的,比如司机走神,比如口舌之战。在我看来,疾病也是在神不守舍时发生的。当我们长期心不在位,与之一一对应的“身”就会出问题,因为只有身心匹配才会阴阳两全,只有阴阳两全,才不会造成生理的短路和故障,这也就是古人讲的病由心造的道理。而焦虑和抑郁就更是不在现场的结果。
只有回到现场,我们才能“躲开”时间。只有“躲开”时间,我们才能免于焦虑,一切焦虑,究其根源,都是因为时间。人们之所以患得患失,是因为有时间在;人们之所以恐惧,是因为有时间在;人们之所以悲观,是因为有时间在。
只有回到现场,我们才能进入整体。一定意义上,整体也是安详之体。因为整体,我们释然;因为整体,我们安然;因为整体,我们放心;因为整体,我们放松;因为整体,我们自信;因为整体,我们满足。就像一个孩子,当他回到家里,回到父母身边,就再不需要提心吊胆一样。同样,因为整体,我们能够听;因为整体,我们能够看;因为整体,我们能够呼吸。以呼吸为例,它的无条件关联性、生生不息性告诉我们,所有生命都是整体的一部分,所谓同呼吸、共命运。因为同呼吸,所以共命运。相反,因为共命运,所以同呼吸。既然整体如此优越,那么我们只需要把自己交给整体即可,因为整体什么都不缺,什么都不坏,它的特性是生生不息,圆满自足。因为这种整体性,人的念头一起,会在瞬间充满宇宙。那么,一个人念一句善,意味着全宇宙都知道,念一句恶,同样全宇宙都知道,而且每个念头动处、落处,都有一个反应、一个结果,它不会无功而逝。这时,我们就会明白古人“一切唯心造”的道理,也就能够明白“报应”一词的意思,如此,真正的敬畏心就生起了。
只有回到现场,我们才能把生命变成和谐。曾经很重地关门,心想门无知,轻重何妨?后来悟到,轻重和门无关,而是轻时,自己收获了一份爱心。当我们能够轻轻地把门关上,轻到听不到门和门框的触碰声,我们会觉得门不再是门,而是一个生命。这时,我们的心里会有爱发生。一个人总是对物件轻拿轻放,时间久了,也会对感情轻拿轻放,小心翼翼,伤感情的话就会少说,伤感情的事就会少做,家庭冲撞就会减少,和谐就会增多。到单位也同样,到社会也同样。一个人总是对物件轻拿轻放,时间久了,也会对责任轻拿轻放,小心翼翼,错误就会减少,遗憾就会减少。同理,他也会慎重对待欲望、诱惑。因此,“缓揭帘”、“宽转弯”,看上去是一个动作,却关系到人的成功和幸福。
只有回到现场,我们才能把生活变成诗意。当我们回到现场,再看到一个水果,会有一种感觉,它是一个十分自足的世界,那么美妙,那么不可思议。面对它们,有时会有种非常强烈的感觉,仿佛能进入它们的内部,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完美的世界,都有些不忍心吃它们,一个人的慈悲心就生起了。真是“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只有回到现场,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智慧。现场是智慧的源泉。智慧和知识不同,智慧是一个人的慧力,它是由能量、妥善、圆满、速度、成功构成的,或者说,它是由能量、妥善、圆满、速度、成功体现的。有些人可能学富五车,但他处理问题却是一塌糊涂,有些人只字不识,却可度人于岸,六祖慧能就是典型。来自现场感的智慧是由源头提供的,它有些类似于写作中的“灵感”。它显然是一个赏赐。既然是一个赏赐,就对接收者的清净度要求很高,一个人的清净心就生起了。
当我们随时随地都能回到现场,并且明明白白地感受着这个现场,安详才能到来。
那么,如何才能回到现场?
有以下几种方式可以采用:
一是找到现场感。
所谓现场感,就是不要离开本体,或者说和本体保持同步。这个“感”,近似于“感觉”,又不同于“感觉”,它是感觉的总部,比感觉更自觉、更主动、更永恒。
就像一棵树上的花朵虽然有别,根却只有一个,这个“根”,就是现场感。热是感,冷是感,饥是感,寒是感,疼是感,痛是感,都是感。热、冷、饥、寒、疼、痛有别,但“感”无分别。这个无分别的“感”,就是本质所在,就是整体所在,就是永恒生命力所在。由此可知,只有进入这个“感”,才能进入平等。
这时,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当徒弟问师父,父母未生我之前如何?师父答,转头就是。把头转向哪里?在我看来,答案就是这个“感”。
为此,古人为我们设计了许多方便,《弟子规》讲,“执虚器,如执盈”,端着一个空杯,就像端着一个满杯;“缓揭帘”,“宽转弯”,只有“缓”,只有“宽”,我们才能“感到”自己。
具体来说,吃饭时要明明白白地尝到每一口饭菜的味道;喝茶时要明明白白地让口唇、舌头、喉咙、食道感觉到,明明白白地跟踪它,一直到胃里;走路时要明明白白地觉到每一步提、移、落、触的过程;睡觉时要明明白白地听到自己的心跳;说话时要明明白白听到自己在说什么;起心动念时要明明白白知道如何“起”,如何“动”,如何“落”,等等。
之于生命来讲,这个“明明白白”太重要了。如果我们在品“这一口”茶时错过了茶,我们即使把《茶经》背个滚瓜烂熟,也找不到茶。如果我们在喝“这一口”水时错过了水,我们即使泡在大海里,也找不到水。
当我们体尝过一段时间“现场感”之后,就会发现“感觉”比“思想”离本体更近,离安详更近,离喜悦更近,也离能量更近。就是说,它更有价值。这从能量的补充上我们可以切实体会到,如果思想没有停止,或者说是意识没有关闭,能量是无法有效补充的。比如,非常疲累时,我们面光而立,通过光的屏蔽作用,让思维停止,不多时,会感到精神一些。
“感”是我们和大本体的通道,它通过眼、耳、鼻、舌、身、意发生,它本质上是我们的“神”,是一种来自整体性的能量。
当这种“感”稳定下来时,本体能够时时刻刻跟踪“我”。同时我们会明明白白地感觉到我们和大本体的同根性、同源性。随之,我们会有一种安全感、力量感,因为同根,因为同源。这时,焦虑自动消失,烦恼自动消失。这时,我们不由得不感恩。这,也许就是“感恩”一词的出处。由此可知,只有“感”到,才能“得”到。
一个人,只有他的这个“感”出来,才能和天、地、人“交流”,否则,他是一个闭塞的系统,一个“伪生命”系统,维持生命运转的就是惯性,不是本性。本性的枝叶是“感”,本性的触须是“感”。
当一个人的“感”打开,喜悦之泉就会打开,这时,幸福就不再是装在杯里的水,而是源源不断地流淌。现在有不少人在讲成功学,但大多在讲如何把水存在壶里,倒在杯里,而不是让他汩汩流淌,源源不断。就是说,他讲的还是流的原理,不是源的原理。有了源,就有了一切,因为源来自大本体。“泉水在山乃清,会心当下即是”,“是”什么?“是”真之所在,“是”美之所在,这个“是”,正是通过现场感获得的。如果我们舍近求远,舍本逐末,结果是一生都在追逐,到头来既见不到“山”,也见不到“水”,当然也见不到“心”。
一个人如果找不到现场感,要想做到“守”是不可能的。比如我们常常犯的错误,打开水龙头往桶里接水,心想还得等一会儿才能接满,就去干别的事了,可是这一干,就把接水的事给忘了,结果让水溢了一地。再比如上网,本来是要到网上搜索一句话的,但搜着搜着,就被别的信息勾引跑了,上网的初衷被忘得一干二净,有时一两个小时都浑然不觉。正是因为走得太远,我们常常忘了因何出发。而一个有过现场感训练的人,他会分配他的知觉的,“分知觉”的“目”在劳动,“总知觉”的“纲”永远把控着这个“目”,而不会让他因为“目”的精彩而忘了“纲”。由此可知,现场有大现场和小现场,知覺有总知觉和分知觉,人格有大人格和小人格。
据我的经验,一个人是否找到了“现场感”,有如下几个标志:
一是当下感。能够随时回到当下,随时清晰地“感”到呼吸,甚至感到“呼吸之根”。会对身体非常敏感,接着对环境非常敏感,身体对环境也非常敏感,冷热痛痒都有种放大之感,比如累了,会知道那个“累”是在什么地方发生的,如果能够成功跟踪这个“累”,它会渐渐化掉。后来还会有宏观和微观通感,虚空和微尘通感。可以随时“人流”,但不“忘所”。
二是喜悦感。觉得生命中时时都有一种喜悦感,也就是焦虑感消失。如果一个人的焦虑还在,说明还没有找到现场感,因为“现场”中无焦虑。比如,去交电话费,如果前面排着长队,找到现场感的人将不再着急,不再催促,如果他还着急,还埋怨工作人员怎么这么慢啊,说明还没有找到现场感。
三是享受感。觉得时时事事都在享受。这才发现,快乐就在“现场”,就是“现场”的一种“感”。因此,回到“现场”是一个境界,体会这个“感”又是一個境界。回到“现场”是寻证,而“感”既是寻证,又是享受寻证。由此,曾经让我们厌烦的工作转为我们喜悦的资源了,工作量变成了喜悦量。一个找到现场感的人,他对世界的感知力提高了,世界在他面前变得更丰富,更有层次感、维度感,更有诗情画意,更有生命力,他的幸福指数自然就大幅度提高了。这才明白,无用之用,才是大用。相对于世俗目标来说,现场感是无用的,但事实上,它是大用,是生命的全部,因为我们恰恰在这个“无用”中,尝到了生命的原味。
四是同味感。如果我们找到现场感,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不是甜却又在甜中、不是辣却又在辣中、不是苦却又在苦中的味,这个味,就是“无味之味”,它事实上是一种更重要的味。就像水,它不是咖啡,但没有它我们尝不到咖啡味,它不是茶,但没有它我们也尝不到茶味,等等,它是味的“底”。这样,我们会觉得生活中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由此,我们就能够全然享受生活,包括曾经厌恶的生活。
五是超然感。因为能看清世间的真相,所以能超然于生活之外,甚至生命之外,但又不排斥生活,不排斥生命。他会非常淡定,又非常积极。他在奔走、奉献,但心如止水。可谓“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可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六是整体感。能够用“一”思维看问题,它的特性是整体性、圆满性、平等性、智慧性、力量性。中华民族一直强调集体意识,强调利他,强调爱,强调“家和万事兴”,正是因为“和”是整体的表现,爱是生命力的表现。
二是“后退”。
比如,我们看到或者想到了一个目标,心里有了占有的念头,马上意识到进入了“想法”,立即从这个“想法”里“后退”,退到一个“没有想法的地带”,发现因占有欲而产生的焦虑消失了,我们重新回到喜悦中。同时还会有种荒唐感,觉得自己刚才怎么动了这么一个无聊的念头。这个“没有想法的地带”,应该就是本体地界,或者说是本体地界的通道了。
一切焦虑都产生在“想法层”。理论上来讲,当我们把“想法层”端掉,焦虑的根就被挖了。
但事实上,对于现代人来讲,要把“想法层”彻底端掉,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生产“想法”的时代,面对洪水一样的意识流,怎么会没有“想法”。因此,用闭关自守、逃脱生活、减少意识关联点、消灭“想法”诱因的办法,已经无法做到。
可以采用的办法是随起随退,就是“想法”才起,马上就退,让焦虑没有浮出水面的机会。当然,要马上退,首先要我们马上意识到“想法”已经起来。通常情况下,当我们意识到时,“想法”自动破灭(这个“意识到”,就是本觉。我们之所以会有不安全感,是因为我们把错觉当本觉。我们之所以会有终极焦虑,仍然是因为我们把错觉当本觉)。
这种“马上”的功夫,决定了一个人回到现场的功夫,也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一个人的幸福指数。
如果没有这种“马上”的功夫,生命常常被惯性掌控。
换句话说,更多的时候,生命都由惯性体操作,本体在沉睡。当我们能够随时发现惯性体,本体就会随时醒来。原来平时跟我们捣蛋惹我们烦恼的正是惯性体。比如,等我们发现,水已经倒在杯里了,你会惊讶,是谁指挥身体倒的?是惯性体。那个指挥者是如何发出的指令,我们不知道。可以肯定的是,那一刻,我们不在现场。许多错误都是在那时发生的,因为惯性体没有无条件准确性。
只有我们能够随时发现“想法”,认清“惯性”,才能真正回到现场,走进安详。人之所以烦恼,是因为“走丢了”的结果。而消除烦恼的唯一途径就是“回归”。
三是进入不允许分心环境。
不允许分心环境可以让我们“强行”体会“准现场感”。比如用极简方式洗茶:把开水倒进茶杯,倾斜杯子,用一根筷子把茶挡在茶杯口,把杯里的水倒尽,但又不让一叶茶出来。
可见,日常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们是在“准现场”的,却没有意识到。比如把刚开的水倒进暖瓶,比如走单杠,比如打球,只是我们没有把它自觉化、日常化,特别是“感”化。还有,书法家、画家在创作时是在“准现场”的。
当然,最终我们要从“不允许分心环境”到“现场感”。
由此可知,在现场是一种身心全然在场又被“感”的状态,特点是“这时”“这事”同时和“身”“心”“感”发生关联,更多的时候,我们身在心不在,或心在身不在,因为我们的身心没有一个调和者——“现场感”。
回到现场是瞬间发生的,就像一个动作突然停止一个思绪突然停顿,它是一个着陆的过程,只不过很快,不需要过渡。训练有素之后,我们会发现,烦恼是雪,现场感是阳光,阳光出来,雪自动化掉;烦恼是黑暗,现场感是阳光,阳光出来,黑暗自动消失。我们还会觉得,现场感是一个巨大的熔炉,无论多么顽固坚硬的烦恼之木、痛苦之铁,一旦进入它,都会顷刻熔化。
这种熔化力,来自安详,就是安详。
通过“勤”走进安详
金刚钻之所以无坚不摧,是因为它的密度,而生命的密度,正是由“勤”造成的。相同时间里,我们比他人完成了两倍的细节,我们的密度就是他人的两倍。
“勤”在本质上是对时间的致敬。通常情况下,人们认为时间是无生命的,这不对,在传统生命维度内,时间一定是生命体,一定是呼吸体,我们浪费时间,就是在欠大账。
在寻找安详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深切地感到时间是物质的,具体的,就像手上的粉笔,只要你写,它就会短下去;又像阳光下的雪,即使你不动它,它也会薄下去。对于一个人来说,它有一个总量,就像一缸米,只要你用,它总会完。
那么,拿这有限的时间用来做什么,就成了关键。对于一个要成为物质富翁的人来说,把一天时间耗在股市上是正确的,但对一个想做精神富翁的人来说,把一天时间用在股市上显然是错误的。精神富翁也许不反对财富,但财富应该是朝着精神高地行走产生的副产品。对有更高超越性追求的人,他就会把这一碗米用在终极目标上,哪怕进项不多。
由此看来,目标成为关键中的关键。谋事之前,行事之前,甚至动脑之前,先想想是否有益于终极目标,成为正确事业的生命线。到此方明白,我们的一切行动,都要以是否朝着终极目标为公式为标准答案进行换算,去找那个朝向终极目标的最大值,去选择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才是正确的取舍。
“勤”意味着行动力。一粒种子,只有落地才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否则,它永远是一粒种子;一个面包,只有我们食用它,才能变成我们的能量,否则它跟我们的生命没有任何关系。
有一些儒学专家、道学专家、佛学专家、心理学专家,虽然学术水平很高,但烦恼依旧,灾疾依旧,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知而无行。这就像许多“财富专家”恰恰没有财富一样,因为赚钱除了理论,更需要去播种,去耕耘。
还有一些人,要么去寺院、道场皈依,要么拿出一生的积蓄去朝圣,但仍然和吉祥如意无缘,原因何在?在我看来,问题就在“行”字上。
我们要收看某套电视节目,必须和它的频道相应才行,否则,即使你坐在电视台台长的家里,也无法看到这套节目。可见“同频”是关键中的关键。因此,真正的朝圣,在我理解,应该是和圣人的频道相应,应该是完全按圣人的教诲去做事。如果我们不依教奉行,那么即使我们每天把圣人的名号挂在嘴上,把圣人的经典背个滚瓜烂熟,也没有用。同样,我们要获得安详和喜悦,就要和安详、喜悦的频道一致。
一个密不透风的“勤”背面就是安详。许多人的安详之所以不能出来,就是因为“勤”是透风的,不究竟的,因为这个透风,这个不究竟,才有了心猿意马,就是说,我们给了意识开小差的机会。而在意识开小差时,感和觉就被干扰,来自本体的安详之光就无法流淌。我们一定有这样的体会。当我们专注于一件工作时,恰恰没有焦虑,闲下来时,焦虑到来。可见带给我们焦虑的是意识。为此,仅仅从消除焦虑的角度,“勤”也非常重要。这时,我们突然会发现,“勤”在本质上也是现场感的一个媒介。
强调“勤”,事实上是强调从细节做起,从改过做起,从衣食住行待人接物做起,不放过每一个因缘。
为什么不能放过每一个因缘?打个比方吧,我们要拨通一个人的电话,需要把对方的每个号码拨对才行,如果对方的号码是七位数,我们只拨对了六位,电话是通不了的,因为它不圆满。在日本,工人即使对老板非常有意见,也不会敷衍工作。他会在头上绑一根白布条,表示抗议,但对手中的工作,永远尽心尽力。因为他知道,工作是在完成自己,跟老板没有关系。
一个人因为对老板的不满生产了一个次品,他生命的账单上就永远留下了一个漏洞,对于生命本体来讲,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因为时空的特性是不可再来,不可复制。如果我们在一个特定的时空点把一个工序做错了,把一句话说错了,将不再有可能更正,因为那个特定的时空点已经永远像流水一样流走了。这正好反证了“在现场”的重要,因为一个人如果不在现场,事实上是不可能不犯错误的。
回头再说老板,其实,我们所有人都在给一个“大老板”打工,如果把我们的隶属关系定位在这个角度和高度上,那么我们就不会计较小老板对我们的厚薄了,“大老板”对我们的厚薄才是最值得我们在乎的。
所有工作事实上都是自己和“大老板”的一个约定,和小老板没有关系。一个个缘分,看起来是我们和世事的关系,究其本质,是“大老板”在我们生命中的展示。我们错误地处理了一个缘分,就等于我们向“大老板”犯下了一个错误。
因此,写下“不用扬鞭自奋蹄”这句话的人,肯定明白这一点。它是一个主动、一个自愿,真正的敬业正是从此而来,真正的心量正是由此而来。想想看,当一个人心怀与“大老板”的约定和心怀与小老板的约定,做事效果该是多么不同。
通过“静”走进安详
在十分热闹的聚会中,却听到一则安静的故事:一个农民为一家寺院送豆腐,看到和尚们整天在那里静静坐着,很享受的样子,很是好奇,就请求加入进去体会一下,不想刚一坐定,就想起有人若干年前欠他的一笔豆腐款还没收齐,当即起身告退,找人要账。
在我看来,这是关于一个时代的寓言。之于卖豆腐者,“静”太不重要了。
但事实真相是,静是最重要的。没有静,我们感受不到世界的富有和美丽;没有静,根本智慧无法起作用,诗意无法发生;没有静,心神无法安宁,而心神不宁的直接结果是灾疾。对于整个社会来讲,没有静,就意味着没有和谐,没有幸福。
古人之所以十分看重静,因为静是生命力,或者说是生命的体。累了一天,睡一觉,精神百倍,補给能量的,正是静。这个静,既是状态,又是能量。男女之爱之所以吸引人,正是因为借助于对方让我们暂时回归静。如果我们能够在自身找到这个静力,就再不需要借助对方回到静了。同时,它还告诉我们,生命是在静中孕育的,尽管它看上去是激情,但那个激情正好是另一种静,因为在那个时间段里,我们没有杂念产生。因此,这个静和速度无关,出色的舞蹈演员在舞蹈时,看上去在动,但她的心是静的,因此能够打动人,她自己也在享受中。
既然静能够孕育生命,那就意味着它能够孕育一切,包括智慧。现在我们就会明白,古人为什么半日读书半日静坐。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我们就会知道,读也是静,静也是读。
在今天,能够体会到静、享受到静的人,已经不多了。因为我们的环境已经没有了静地。古人对静地的要求是,九里之内听不到牛叫声,显然,现代社会无法找到这样的地方了。当年回老家,当我走进那个小山村的时候,从那个山头走过的时候,就觉得进人了一种节奏,那是一种巨大的、充沛的、富有磁性的静。每晚,我都要出去,一个人坐在山头上,抬头,明月就在当空,一伸手,星星就在掌心。那种寂静,真是有种融化人的力量。那一刻,我能够实实在在地体会到来自浩瀚宇宙的无尽滋养。这几年,已经没有当年的感觉了,因为村里已经有拖拉机和摩托车这些东西了,当年那种持久的浓烈的厚实的寂静,已经无缘享受了。
为此,“闹中取静”就成了一个课题。我尝试过通过一个对象物,致心一处取静。比如把一本经典读一千遍,把一首歌唱一千遍,觉得有效果。当下瑜伽之所以流行,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通过一定难度的动作,让如猿之心如马之意暂时粘在上面,给本体一个浮出水面的机会,回家的机会,喘息的机会。也就是通过一念,到达无念。
当我们能够成功地把握好“第一念”,就能体会到古人讲的“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从心而觅,感无不通”。
如果我们真正走进安详,就会发现安详和世俗成功并不矛盾,因为安详会感召大善缘。就是说,世俗成功是安详感召来的一个副产品。这就像一个人,职务是厅级国家自会配发厅级工资,是处级国家自会配发处级工资一样,关键是看我们拥有哪一级的安详。如此,我们就不会为一时之逆而沮丧,也不会为一时之顺而得意。天意就是这样,当时我们是看不出来的。但在我们内心,一定要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天意是存在的,而且是毫厘不爽的。
有一個晚辈向我倾诉工作变动的事,并言倒霉。我听完后问他,你是缺儿还是少女?是缺吃还是少穿?是在贫中还是病中?如果不是,那怎么能够轻言倒霉?或许我们谁都可以不相信,但一定要相信上苍,我们谁都可以怀疑,但一定不能怀疑上苍。如果我们连上苍都不相信,还能相信什么?而一个心中无信的人,又何言安详?一个心中没有安详的人,又何言幸福?一个心中没有幸福的人,又何言成功?同样,一个心中有上苍的人,怎么能轻言倒霉?他当时就申明收回所言。之后,坦然面对变动,乐观应对生活,不料一个个意想不到的好事不断到来。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如果善人被饿死,那就没有天理。但是,怎么会没有天理呢?一个城市都有一个城市的规划,一个单位都有一个单位的制度,怎么会没有天理呢?
在清华演讲时,有一个研究生对我说,他很赞同安详文化,但现在马上就要找工作,怎么能够安详,如果找不到工作该怎么办?我说,如果你真是一个获得了安详的人,就不会找不到工作。如果最后真没有单位接收你,你就去义务扫大街,时间一长,就会有负责扫大街的人赏识你,把你纳入他的团队,说不定还会让你负责这块清扫工作。如果你仍然按照安详原则用心工作,再过上一段时间,人们就会发现这一块的卫生尤其好,环保局一调查,说不定就会提拔你负责更重要的工作……渐次,说不定你最后还能成为环保局长呢。当然,对于一个追求安详的人来说,他肯定不会在乎是否能够当上环保局长,但环保局长自会成为安详生用的一个平台。
为了方便读者借鉴,我把自己当年“由信得定”的一个口诀分享如下:
“大有我无,思非当是,但行莫问。”
“大有我无”,是说一切都是由“大逻辑”决定的,自己想也是白想。再说,连“我”都是一个假象,还有一个谁在乎得和失呢?同时提醒自己,只有我们的言行合乎大道,“有”才会发生,才会到来J也即只有“公”,才有“益”。“公”是根本,“益”只不过是“公”这棵大树上结出的一个果而已。佐证这一原理的,有“求之不得”、“舍而得之”这些成语。另外,当“大我”在现场时,“小我”消失了,焦虑也消失了。
“思非当是”,是说一旦思想,已经错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从思想回到现场,因为真正的“现场”一切都不缺,并且是“真有”。
“但行莫问”,是说尽管去做好事,不要考虑结果,因为结果之想会把我们带出现场,产生焦虑。
通过“给”,我们把心路腾开,把心的空间放大,从“小我”转变到“大我”;通过“守”,我们回到现场,回到本质,回到根;通过“勤”,我们给自己不断“升级”,同时不给习气以空间和机会;通过“静”,我们的心湖能够映照明月,能够明察秋毫;通过“信”,我们的心得到大定。
最终,通过“给”“守”“勤”“静”“信”,我们走进安详。
郭文斌,作家,现居银川。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农历》、小说集《吉祥如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