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发轫期科技知识分子形象回眸
○曾镇南
一
伴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应运而生的新时期文学,是我国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个崭新的阶段。新时期文学的爆炸,差可与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爆炸比肩而论。现在回眸凝视,这一段被30多年时间定格的文学史,以它留下的一批如群星璀璨的杰出作家和争奇竞艳的优秀作品,雄辩地为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作证。在这30多年文学史行程中,曾经出现过许多贬抑我国新时期文学的议论,但喧哗消歇,尘埃落定,新时期文学的实绩、价值和影响,渐渐被具历史眼光和艺术良知的国内外观察者、研究者所认识、所高看。
想当年,巴金说,“我感到,我们现在的作家作品已超过30年代、40年代”;冯牧说,我国新时期文学所取得的成绩,“同世界文学所达到的水平并不存在很大的差距”;王蒙则断言,“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这些信心满怀、豪情洋溢的论断,现在看来,是可以征信于后世、取验于作品的。最近,因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引发的重新关注、重新阅读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读书潮,必将大大提高人们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历史定位和艺术魅力的认识。
现在,我仅从新时期文学发轫之初出现的一批科技知识分子形象的角度,来作一次回顾。
在我看来,一个称得上发达和成熟的现代社会,必须造就大批有真才实学和崇高担当意识的知识分子队伍。这些知识分子队伍大致可分为五种类型:人文知识分子、科技知识分子、治国理政知识分子、财经商贸知识分子和生态文明知识分子。其中,前两种是基本的、具有母基性的,后三种是从前两种派生、分蘖出来的。这五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从事的都是马克思所说的“一般劳动”(一般劳动是一切科学工作、一切发现、一切发明。这种劳动部分地以今人的协作为条件,部分地又以对前人劳动的利用为条件)。而与大多数普通劳动者所从事的“共同劳动”相区别(共同劳动以个人之间的直接协作为前提)(《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P120)。这些知识分子所从事的“一般劳动”,即把横向平展的知识的浸润性与纵向承继的知识的创新性相结合,从而形成科学发展的正能量,推动社会和历史的前进。
在新时期文学肇始之前,科技知识分子的形象很少出现在当代作家的视野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对要求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改造思想的偏狭的理解,对文艺工农兵方向的片面的强调,还有在国际封锁条件下对决定国家命运的高科技事业的保密要求等,使科技知识分子的形象难以出现在作家笔端。
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浪潮、思想解放运动,冲破了描写和反映科技知识分子生活和事业的禁区;科学春天的到来,呼唤着崭新的知识分子形象出现。早在1960年代就以塑造人文知识分子常书鸿形象的《祁连山下》而惊艳文坛的诗人徐迟,那时率先写出了一时洛阳纸贵、名重天下的报告文学名篇《哥德巴赫猜想》,把陈景润这匹在世界顶级数论高原上寂寞驰骋的天马,引入人间。这篇大时代的大文章所塑造的陈景润形象,不仅激发了驱动科技创新的力量,也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境界和品质,使它从一开始就攀上了与伟大的民族复兴事业相配称的精神高地。紧接着,徐迟又以惊人的速度写出了《地质之光》《在湍流的涡旋中》《生命之树常绿》等作品,分别刻画了地质科学家李四光、物理学家周培源、植物学家蔡希陶的感人形象,真可谓“诗人善画盖有神,必逢佳士亦写真”。徐迟以诗心诗笔写出的这一个个散发着感性的诗意光辉的科技知识分子形象,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国家形象的艺术写照。

《哥德巴赫猜想》,徐迟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
作家黄宗英的《大雁情》《桔》《小木屋》,以注入深情、感同身受的笔墨,最先描写了秦官属、曾勉、徐凤翔等尚处于郁郁不得申其志的境遇中的林业科技工作者、自然生态守护者的形象。他们的现实命运,即是蛰居在六平方米书库的昔日陈景润的不同形态的翻版。为他们科研工作条件的改善呼吁,也就是对妨碍科技知识分子成才遂志的习惯势力和僵化体制的有力冲击。在这个意义上,黄宗英的这些报告文学作品是更具现实的战斗性的。
作家陈祖芬的《祖国高于一切》,是报告文学中剪裁有致、笔调清畅、语言明快而富有诗感的短篇,活脱脱地写出了内燃机专家王运丰高尚的仁人志士的形象。她的笔尖似有一束艺术的追光,不仅照亮了王运丰以专业报国的辗转而艰难的命运中的几个节点,而且照透了他如水晶般莹洁、坚强的爱国之心。老作家黄钢的《亚洲大陆的新崛起》,与徐迟的《地质之光》同题异趣,把李四光的事业放到中国新崛起的历史大背景中,以真确的事实、洗练的细节和深沉的思想,刻画了这个科学泰斗在行进时具有的宏大的气魄和时代的节奏。这是在一个科技知识分子身上探索性地开掘出来的推动中国新崛起的巨大正能量。这种正能量现在已从地下热海的诸多泉眼里喷流出来,和盘托出了中国崛起之谜中最有现代意味诸多谜底的一个。不管怎样,作家的笔已触及时代本质的一个侧面,他是尽了时代的报告的天职的。
如果说报告文学是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重镇,那么,中篇小说的兴起和极一时之盛,则是显示新时期文学的实绩、声势及深度的另一个重镇。当时勃然兴起的中篇小说中,有不少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如张贤亮的《绿化树》中的章永璘,温小钰、汪浙成的《土壤》中的辛启明,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中的罗群,王蒙的《杂色》中的曹千里与《蝴蝶》中的张思远,宗璞的《弦上的梦》中的慕容乐珺和《三生石》中的梅菩提等。这些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都是放在一个较长的历史跨度中去刻画的,他们都怀着一颗忠诚的报国之心,却在极左路线的阴影下饱受磨难,最终又在忍耐和坚持中等来了命运的转折。这些知识分子形象的时代典型意义是深刻而又鲜明的,但其中却鲜有科技知识分子形象,只有作家谌容的《人到中年》刻画了一个人到中年、遭际坎坷、忠于职守、矢志不移的眼科医生陆文婷的形象,以纤笔触及她担荷人类苦难、救世济民的仁心和灵魂,差可归入科技知识分子一类。这个陆文婷的文学形象,是当时大量中篇小说里知识分子群像中最具有典型意义的。由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人到中年》风靡一时,催人泪下,使生活中成千上万的中年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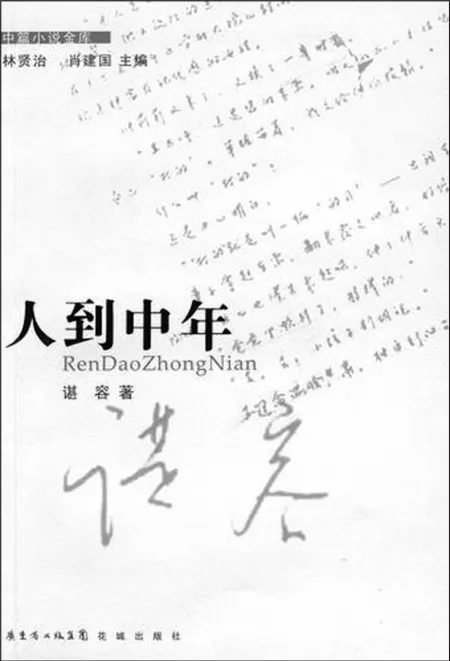
《人到中年》,谌容著,林贤治、肖建国主编,花城出版社2009年8月版,12.00元。
(最近我读莫言的早期作品《爆炸》,其中有个细节写到那个快人快语、在村卫生所当妇产科医生的姑姑,一见“我”就说:“你把我写进电影里没有?我比陆文婷不差,接了一千多个孩子,人到中年,你姑父还在宁夏,调不回来。……”我看到此不禁哑然失笑。这也算是陆文婷形象典型意义之大、社会波动幅度之广的一个小小注脚吧。)
二
在当时的中篇小说之林里,还有没有写得比较丰满、生动、有典型意义的科技知识分子形象呢?当然是有的。这次应约谈谈新时期文学之初出现的科技知识分子形象,我找出了当年写的一些读作品的笔记片段,其中有对两部中篇小说——朱春雨的《沙海的绿荫》和中杰英的《在地震的废墟上》的简评,不妨续接在这篇回眸之作的最后,算是拾遗吧。重读这些写于30多年前的文字,字里行间还能感觉到自己刚开始写文艺评论时的热情、较真和华丽的文风,因而不免有些脸红。不过,热情也好,较真也好,绮丽也罢,都是拜当时时代潮流之所赐,笔墨是难脱时代的印痕的。
朱春雨的《沙海的绿荫》,是一部较早出现的描写科技工作者生活的中篇小说。作品反映的是一个很特殊、甚至很富神秘感的领域:核导弹基地的生活和斗争;但是它展开的故事和人物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充满着人间情味的。在18号甲的“三枝花儿”——沈巧、欧阳美怡和黄金桃的不同命运中,在唐天虚和顾雨时的对峙中,在事业和爱情的冲突中,作者以瑰丽宏阔的笔墨,织入了时代的风雨、社会的变迁和人生的哲理。而那幽深的峡谷、冷落的驼铃、凄寂的孤烟、浩瀚的沙海及壮丽的日出,映衬着战士的豪情,使小说流动着一种浪漫主义的神采。处于这一切中心的,是沈巧的动人形象。这个穿着军装的中年女科学家,形貌平常,作者没有用任何华彩来打扮她,却成功地展示了她生命的太阳的全部光芒。尽管她在内心深处爱着唐天虚,但在学术见解上坚定地、坦率地护卫着自己的独立性。在学问贬值、空话膨胀的日子里,她的学术成果竟被顾雨时之流利用来作为打击唐天虚的借口,这使她深感痛苦。但是,对科学真理的无私的态度,终于使她顶住顾雨时的压力,保护了唐天虚进行的研究试验。当她发现自己苦苦追求的系数的准确值的底数,恰恰就在唐天虚发现了但无法从理论上说明的那一条闪现在巨幅荧光屏幕上的直线里时,便无私地献出了自己的计算公式,让自己的研究成果,像一滴水汇入江河一样,汇入唐天虚的研究试验中。沈巧对待科学真理的这种无私精神,像沙漠上的旭日一样,荡涤着顾雨时之流搅起的鄙俗的迷雾,吐射着辉煌的光华。在沈巧这个人物身上,作家概括了我国现代科技工作者探求科学真理的无私无畏的精神。正是这种对科学真理的坦诚追求和尊重,引导他们穿越那动乱的年月里弥漫的迷雾,在难以想象的复杂、困难条件下,为中华民族的富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足以和《沙海的绿荫》中的沈巧相媲美的,是中杰英《在地震的废墟上》所精心塑造的韦凡——一个抗震工程学家,又一个科学真理的热烈追求者。中杰英以他特有的雄劲、简练而犀利的语言,把韦凡的形象勾勒得异常鲜明。这个形象有如刀劈斧削出来的奇峰,拔地而起,给人的灵魂以一种强烈的冲击力量。这种力量和匀细严整的工笔画的人物的魅力是不同的。韦凡这个形象,是普罗米修斯型的人类命运的探索者,是拥抱人类利益的献身者。这个形象的强大生命力,正在于他海涵地负的思想力量。韦凡从小是在贫穷和劳苦的磨砺下成长的,对工程抗震的数学模型这一科学真理的追求,渗透着他对人类命运的伟大的悲悯心。韦凡是在和科学研究中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积习斗争中,表现出他丰富的内心世界的。在他粗犷的性格中,跳动着纯厚正直的科技工作者的良心。
通过对上述两部中篇小说的简短巡礼,我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要充分地估量创造我国现代科技工作者的艺术形象的社会现实意义和文学意义。具体的艺术形象的价值,当然不是由它反映的生活领域和描写的人物职业决定的,但是,不能因此完全否认题材的选择对文学整体格局的重要意义。现代科技工作者的形象在文学中一出现,就引起读者和评论界的强烈反响,这正说明此类形象的创造适当其时。马克思认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但在十年动乱中,科学被贬斥,这造成了我们民族的空前灾难。某一个生活领域、某一类人在文学中得到反映的深度和广度,往往反映着生活发展和文学发展的动向。现在,科技工作者在整个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中的地位日益提高,他们应该在现实主义文学中占有自己的席位。高尔基十分强调“科学和文学之间的某种联合,某种内在联系的必要性”,而且“特别强调同40岁以下的科学家们的联系”,认为这种科学家是“现实所创造出来的一种新型的人”,号召文学去表现他们。他的这些意见,对于我们的现实生活和文学现状,仍葆有新鲜的意义。我国的科技工作者,特别是中年科技工作者,的确是饱受生活磨练的一代才俊。20世纪50年代高昂的时代精神和健康的社会发展,十年动乱中的挫折和屈辱,新时期开始后改革开放的复兴局面,都在他们的心灵中留下投影,刻下印痕。他们对社会、人生巨大变迁的感受是丰富而深刻的,对事业的潜心追求也到了收获期。这些人的曲折的历程、艰难的奋斗和卓越的贡献,正是文学的极好素材。沈巧、韦凡及其同事们的形象,恰恰是一组中年科技工作者的群像,这并不是偶然的。这是现实生活通过作家发出的不容忽视的信息。这些文学形象算是做了一个先行,其继起者将是郁郁乎盛哉,是可以期待的。
第二,认真地研究现代科技工作者形象的创造,必须解决的一些特殊的艺术问题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首先,应把科技工作者当作社会人,在社会冲突中揭示其内心世界。高尔基认为:“不要把科学和技术写成储藏着现成的发现和发明的仓库,而应当把它们写成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克服物质和传统的抵抗的斗争场所。”能否做到这一点,往往决定着这类作品艺术上成就的高低。我国的社会生活为现代科技工作者的形象提供了广阔的活动舞台,他们所经历的斗争的丰富、生动、深刻,都是罕见的。这就为作家们进行高度的艺术概括提供了素材基础和潜在的可能性。《沙海的绿荫》在描写社会斗争的广度和深度上,应该说是提供了某些成功的经验的。而《在地震的废墟上》则在展示科技工作者的时代风貌和崇高思想方面更具优长之处。其次,还有一个怎样写出科技工作者的特殊但又丰满的个性问题。科技工作者由于长期工作的训练,思维都是条理化的,极富理性;又由于专注于事业,一般都比较内向、孤僻,甚至表现出不合群和冷漠。这就需要作家仔细分析这类人性格的外观与内层复杂的对立统一,掌握好描写的分寸。爱因斯坦强调一个人对人类利益的责任感和个人对于社会的依赖性时,曾指出:“要是没有能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有创造能力的个人,社会的向上发展就不可想象,正像要是没有供给养料的社会土壤,人的个性的发展也是不可想象的一样。”(《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P39)更有意思的是,爱因斯坦还剖析了自己的性格。他说:“我对社会正义和社会责任的强烈感觉,同我显然的对别人和社会直接接触的淡漠,两者总是形成古怪的对照。我实在是一个‘孤独的旅客’,……我总是感觉到和社会有一定距离并且需要保持孤独。”(《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第43页。)这样一种对人类整体的亲近感与身处人群中的孤独感的矛盾,在改革开放时代的科技工作者身上,也许不会像爱因斯坦所尖锐感觉到的那样“与年俱增”,但不可能完全消失却是可以断言的。而这种矛盾表现在每一个具体的“这一个”文学形象上,又是千殊万异的。这也充分显示出写出科技工作者的可以被理解、被接受的独特个性的困难。
马克思指出:“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干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而文学,诚如鲁迅所说,是交流人类思想感情的最平正的工具。让我们的文学和科学更紧密地携起手来前进吧,为了祖国的未来,为了人类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