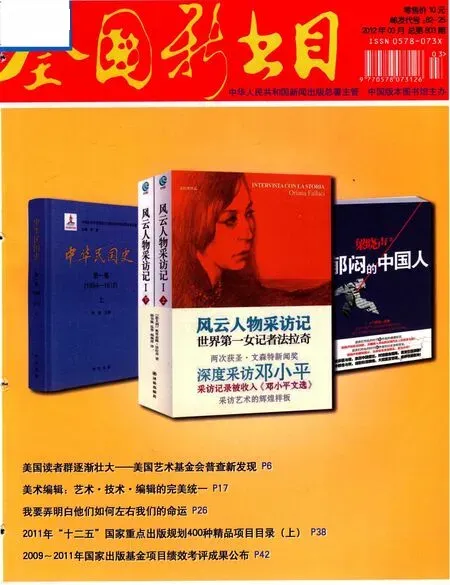厨房密语
◎文/金柏莉·史诺
金柏莉·史诺厌倦了冰冷枯燥的学术世界,毅然投入厨师生涯,几经波折后当上了俱乐部主厨,成为众人眼中颐指气使的“上帝”。但是在一个禅修中心的厨房里,她发现自己不但不能呼风唤雨,还必须时刻返照自己,修习一项陌生的功课---慈悲心。历经几番身心的煎、煮、烤、炸后,她渐渐明白:炽热高压的厨房工作,正是体验“活在当下”的最佳战场。
厨房里聊天的味道
我喜欢在厨房里,选择在厨房里工作的原因之一,就是喜欢人们在厨房里聊天。厨房里的聊天好像有其独有的味道。小时候,我的社区感就来自满满一厨房忙忙碌碌的女人在一起干活。度假的时候,在姑婆南加州那幢巨大的老房子里,那些又老又没劲的亲戚们会在正式的客厅里聚集一堂。在那里,我得坐得板直板直的,又不自在又得小心翼翼不能失了礼数。只要一有机会,我就跑到大厨房去。厨房里铺着地砖,有个壁炉。以前厨房是一幢独立的房子,后来用落地窗式的通道跟主房连起来了。哈媞姑妈门廊外的厨房,是一片独立的领地,里面满是丰富、湿润的味道,行动和温暖,啊,还有大家融入一起的联结感。表姐妹们,姑姑婶婶们和姑婆们用一种巨大温暖的女性肢体和声音把我围裹起来:交谈、八卦、建议、咨询,好像每个声音都能填满半亩地。
我母亲总是跟一个瘦女人一起待在客厅里。那女人跟别人拥抱的时候,总是冲着人家的脸颊摆个姿势,虚张声势一下,不会真的吻人家。但厨房里的女人们送上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响吻,啧啧有声。她们把我一下搂进怀里,给我一个超级巨大的拥抱,还会用力地挤一挤、拍一拍,有时候还会亲密地掐我几把。在这群闹闹哄哄的亲戚中间,我的姑姑婶婶们和表姐妹们总会告诉我该去考虑什么,听什么,怎么做。建议、暗示和人生规划,都在不知不觉间渗进了一盘盘胡麻籽华夫饼和天使曲奇里,塞进了砂锅鸡、柠檬派和木莓果冻里。
那些厨房里讲的秘密
我爱死了在假模假样的家族场景背后,在热气腾腾的假日厨房里讲那些秘密了---玛格丽塔姑姑的癌症、亨利酗酒、菲利希亚的闪婚---无论客厅里有什么没提到或不能提的,在厨房里都能说,都能分析,都能笑论,而我就站在他们脚边,我的鼻子勉强能够到桌面。我母亲总是使用加密的语言,每次到最后我都能拼出意思来,把她用维多利亚时期女人使用的秘密语言来形容的那些人和事联系在一起,琢磨出些端倪。但在厨房里,女人们的丝质印花裙外面围着腰带、围裙,即使是她们在谈论镇上最棒的八卦时,也让我装饰沙拉,在一个水晶托盘上码放柠檬曲奇和奶油糖果布朗尼,或给果仁杯里放果仁。她们快手快脚地掀开这个盖子,弄开那个盒子,打开烤箱门看看里面的香焗甜薯和酵母卷烤得怎么样了,给跑来跑去的小孩子紧一下头上的蝴蝶结或发带。但没人会错过任何一个炉子旁边或饭桌周围同时进行的几个谈话中的任何一个细节。
家里的女人都假装服从家里的男人,但其实她们从来都不听话。事实上,男人们只是被简单地推到前台,耐心地坐在一起,就像一场飓风后的幸存者一样。我的姑姑婶婶和表姐妹听到妇女解放运动时,她们会问:“图什么啊?我就是不太明白。”
在餐厅里,很少有什么对话是能结束的,至少在员工之间是这种情况。在拉法叶的时候,我学会了在谈话进行一半的时候,去做其他的事,在一两个小时之后再把话说完或回答之前的问题。餐厅的厨房里,或者至少是拉法叶的厨房里,总有些东西,让人们来来往往,将胸中的郁结对完全陌生的人一吐为快,说说自己的女儿做了流产,她们的丈夫有多无能。我目睹着这种事情一次次地发生:“这儿,女士,这是您点的土豆。有个女人,叫邦妮,在昨天晚上的约会中,嗯,邦妮和我……”
这才刚刚上午10点。
与朱尔斯论厨
下午的情况是,主厨朱尔斯和我会在准备晚饭的时候无休无止地谈论食物。有一次,我们站在料理台的两边,好像是在准备洋葱汤、罗勒酱、第戎鸡肉、皮拉夫肉饭、扇贝、朝鲜蓟菜心、菲力牛排用的贝亚恩鸡蛋黄油酱汁、酿汁意大利式蔬菜、胡萝卜维西、奥地利式沙哈蛋糕、巴伐利亚奶油和法式巧克力蛋糕。
那天晚上,所有的东西都分好了份,烹饪妥当,装饰精美,放到餐桌上,被客人吃光了。
第二天,是同样的料理预备,我们为了做一道汤把蘑菇切开,为了做另一道汤把姜和冬葱剁成末。我们给鳟鱼搅好了馅料,把小牛肉片拍得薄薄的,把一块猪肉烤得红得发亮,给黑椒牛肉调好味,做了一份巧克力慕斯,卷好了塔皮,把柠檬剥好了皮,准备填料。
每天的菜谱都不一样,花样层出不穷,完全是根据朱尔斯的奇思妙想而定。朱尔斯不像洛奇做饭那么乱七八糟,他做的菜非常美味,而且他喜欢做实验。
在拉法叶最让我感兴趣的就是准备食物时,要把所有东西一遍一遍地品尝。我整天都得用手指头蘸些荷兰蛋黄奶油酸辣酱尝尝,或舔舔用来调金万利香橙甜酱的勺子,或刮一刮盛放奶油用的碗,或在装盘的时候掰下来一块蛋奶酥……总而言之,整天这咬一块,那尝一口。
朱尔斯和我之间的谈话一般都是围绕着食物展开的。“你听说了吗?”他一边说一边把一块肉冻放在鸡肉上,做出个造型,这样就可以把用胡萝卜和韭黄茎叶做的花插在上面,“去年那个赢了法国厨艺展示大赛的人,嗯?我不确定他赢了,但没听说过其他说法。他做了一条鲨鱼,一整条7英尺长的鲨鱼。他挖了个坑来做这条鱼,大概烧了4天吧,然后他把一条小鲭鱼和一堆海草碎裹在鲨鱼上。把其他人都给比没了。他们不过是弄了些小鳗鱼冻,装饰漂亮的鸡肉。可这个人弄了个庞然大物的鲨鱼!”
或者我们会争论不同技巧或原料的各种优点。如果我们把奶油混着威士忌来做荷兰蛋黄奶油酸辣酱,味道是不是要比直接用搅拌机搅出来的好呢?人们真能的分辨出来我们用的是罐装鸡汤还是我们自己煲的高汤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能)我们能分辨其中的差别吗?通常不能,特别是在奶油浓汤里,因为底汤中添加了太多原料。为了味道上那么一丁点的差别,值得我们付出这么多额外的麻烦和成本吗?美食家和白痴的界限在哪里呢?
好好地吃饭 好好地爱
酱汁对我而言是项新发现。作为南方人,我从小到大只吃过白汁和肉汁,但我对这两种酱汁都不怎么感冒。后来在大学里一点点积累,我逐渐知道了荷兰蛋黄奶油酸辣酱和贝亚恩鸡蛋黄油酱,而以半釉汁打底的酱汁家族,从法式波尔多酱到魔鬼酱,再到罗伯特酱,为我开启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视野,并且让我开始学会分辨各种的微妙味道。调制酱汁是朱尔斯的拿手好戏,我喜欢看着他专心致志地调制酱汁,和自己手中的酱汁发生联系时,那张英俊的面孔严肃,甚至有点严峻的样子。即使是不好的日子里(这样的日子也不多),制作一道复杂的酱汁,他就会恢复心情的。
我们经常阅读餐厅普遍选择的烹调书,从中寻找菜谱。有时候我们从中寻找晚餐的灵感,其他时候只是找找乐子而已。“听听这个,”我说,“彼得大帝浓汤,法文叫Potage Pierre-le-Grand’,这道汤是把蘑菇和榛子松鸡肉泥混合在一起,’榛子松鸡肉泥?我们还有用剩下的榛子松鸡肉泥呢,对吧?哎,这有个好玩的:鹧鸪橘子盏。你觉得吃午饭的人愿意放弃火腿三明治,选这个当午饭吗?”这样的对话多了去了。
有时候朱尔斯和我会谈起弗吉尼亚·伍尔夫,因为我们都是她的铁杆粉丝。我们从《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中节选了一段,抄下来挂在水槽上:“人类的形体是由心、身体和头脑混合而成的,即使历经沧海桑田也不可能分开来存在于不同的个体中。一顿美好的晚餐对于良好的沟通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一个人如果不能好好地吃饭,就不能好好思考,好好地爱,好好休息。”
敬美好的食物 敬美好的晚餐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每天下午在厨房待的时间越来越长。几个月之后,我一周开始有三四天给朱尔斯做助厨。晚餐比午餐隆重很多。菜品都精致地装盘,服务更好,菜单也更注重食物间的平衡感与和谐感,这是午餐中所缺乏的。拉法叶提供包括汤、沙拉、主菜和甜品的套餐,价格都一样。这里除了周日和周一之外,每天晚上都提供晚餐服务。每天晚上他们会有两道汤、三道沙拉、三或四道主菜和三道甜点。如果客户愿意的话,他们也可以单点,但大多数客户都会点全套。因为我们大概6点钟开餐,而且通常超过9点半后就不再接受点单了,所以人数上比中午接待的客户要少,但每个人吃得都比午餐多。晚上的时候,拉法叶的老主顾们来这里不仅仅是吃东西,他们是正儿八经地来就餐的,而且是大手笔地就餐。
在厨房里,我们全神贯注、兢兢业业,把专业技术倾注在每一道菜、每一道作品中。我们有时候会看着人们吃东西,等着他们尝了以后,睁大眼睛,坐直身子,倾向食物,然后又咂摸一下嘴。我的上帝啊,他们的身体会说,我不知道食物尝起来竟然还可以是这个味道!
然后朱尔斯和我会开一瓶福乐里(Fleurie)葡萄酒,举杯庆祝一下。
“敬美好的食物,”我们会这样说,因为我们知道整个下午的辛勤劳动都物有所值,“敬美好的晚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