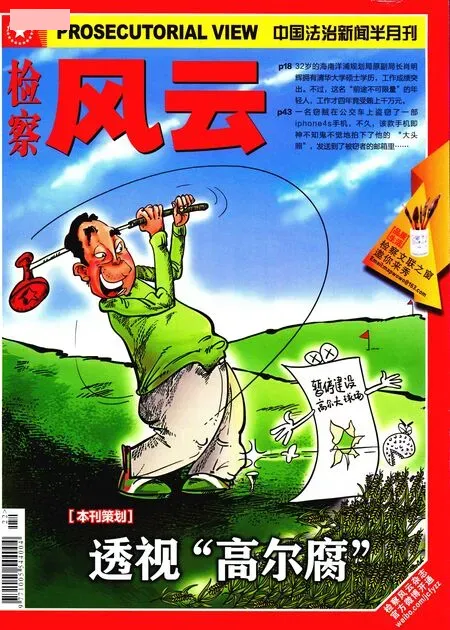上海劳工幸存者口述实录
文·图/王正瀚
上海劳工幸存者口述实录
文·图/王正瀚
上海劳工袁学仁:
王正瀚(以下简称王):袁伯伯,作为上海劳工,您是哪一年怎么去的日本?
袁学仁(以下简称袁):我老家其实在杭州,我父亲是开店的。我在杭州上学的时候,正好上海电信学院到我们学校来招生,我就考了电信学院到上海读书。我记得那年是1944年,我18岁,正好从学校出来,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看到马路上贴了广告招募去台湾的码头工人。广告上写的薪水不低,我当时正好没事干,就想去台湾挣一年钱再回家,这样子就报了名。
王:您当时用的是另一个名字?
袁:是的。我现在的名字叫袁学仁,以前最早叫袁武林,武松的“武”,双木“林”,这是我在学校时的名字。报名到台湾当码头工人的时候我用了祖父给我起的号“伯湖”,所以用的是“袁伯湖”这个名。
王:您说说报名之后的情况。
袁:我记得我们是在提篮桥附近的一个茶楼上报的名。可是,去了以后也不知道具体去的地方,而后就被安排在一个大仓库里住着,住进去以后就觉得不对劲了,但知道也已经不能出来了。
王:就是说,在报名之后,你们是被囚禁起来了。
袁:是的,被关起来了。过了几天后,一个晚上,日本人让我们上了卡车,到了黄浦江边坐了摆渡船,出了黄浦江口,上了一艘日本船叫“仁洋丸”。我记得在海上走了两个星期吧,当时天上不时有美国飞机轰炸,就这样我们一下船就到了日本。
王:当时与您同船的人都是与您类似的方式被抓去日本的吗?
袁:对,大概有一千多人。上了岸以后,就脱掉身上的衣服消毒,然后上了火车一直到北海道室兰住下,第二天我们就被送到日铁七厂当苦工了。
王:那您还记得您看到的这个广告上面有没有写是以什么公司的名义招工的呢?
袁:没有写,就说是到台湾做码头工人。
王:出面招你们的是什么人?
袁:都是中国人,他们(指日本人)都是通过地痞、流氓出面组织招人。
王:从这时起您就与家里没有联系了?
袁:是的。我父亲当时在杭州,母亲还在老家海门。我原来就是想挣一年钱后去看母亲,哪晓得就被骗去了。
王:被骗到日本后,你们的劳动状况是怎样的呢?
袁:我们到了室兰以后,在一个叫轮西的小村庄住下,大概有二百多人吧。住在日本农村像大祠堂一样聚会的地方,我记得那里前面有个戏台子,地上就铺点草给我们当睡铺。我们刚去的时候是八月份,去的时候天气还暖和,等到以后天开始冷了,你想想北海道冬季气温常常到零下二三十摄氏度,这样的环境就可想而知了。
我记得,我们第二天走路去日铁七厂上工,路上将近要走一个小时。他们(指日本人)就给了我们一套外衣,里面穿的衬衫两件,一条被子,一条毯子,就睡在地上,地上铺草,人跟人挤在一块。在那里吃饭吃不饱,都吃野菜、杂粮饿着肚子,路上走路一走就要一个多小时,然后干活。每天干的活就是搬砖、卸煤啊什么的。干活只是一个方面,受罪的一个是吃不饱,第二个是天气冷了,路上要走一个多小时,路面结了一尺多厚的雪,衣服穿得又不多,所以印象最深的就是又饿又冷。
在上班的路上,我们看到什么东西就捡了吃,吃得我拉肚子了,一开始一个钟头一次,后来十几分钟一次。拉肚子拉得厉害

上海劳工幸存者袁学仁近照

上海劳工幸存者唐绵昭近照
访谈背景:
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出现了国内劳动力严重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战事的扩大,日本劳动力奇缺,从那时起,日本侵略者就通过抓捕、欺骗等手段,在中国各地掳掠劳工,将他们输往日本,上海的普通百姓也蒙受了这一劫难。在恶劣的环境和极其残酷的强制奴役之下,许多中国劳工客死他乡,而留给侥幸生还者的则是身心的双重创伤。为了让后人更为直接地了解历史,笔者走访了两位当年上海劳工的幸存者,记录下了他们诉说的那段辛酸往事……了就不能上班了,也没有药吃,他们(指日本人)给病号吃的饭要减少一半,但是我连这一半的饭也吃不下了,因为拉肚子拉得太厉害了,全靠我们的难友给我打打开水,照顾我。在我拉得最厉害的时候,他们把我送到大房子旁边搭的一个小房子里,这里面有三个重病人,我是一个,还有两个比我年纪大的,在大房子里有炉子,小房子里没有炉子烤,挺冷的,其实基本上就当我们死人一样看待。那两个年纪大的病号照顾我,把我放在中间,因为我当时只有18岁,还是小孩子,他们俩在两边。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觉得身上很痒,虱子很多,天亮了后才看到旁边那两个人都死了,所以虱子都爬到我身上来了……

图为上海劳工唐绵昭亲笔撰写的控诉书
当年中国劳工个人的不幸遭遇,同样也是我们国家和民族那段屈辱岁月的见证,它对后人有着特殊的警世作用。因为牢记战争所造成的苦难,是真正理解并珍视和平的前提。
后来我的难友发现了我,就跟日本人进行交涉,才把我搬到里边有个病人待的大屋里,大屋比较暖和,但是我拉肚子,饭也吃不下,难友就跟我说你这是肚子里有寒气,拔火罐可能会治好,拔火罐我知道,我父亲在我小的时候经常拔火罐,我呢,当时没有这个条件,就找了一个罐头盒,里面一烧就扣上去了,但是也没扣准(给采访人看伤疤),我眼睛一闭就扣上去了,结果扣歪了,由于火直接接触肉,烧在肉上就起泡了。那时也没有药,就这样自己自生自灭地活着……
王:也就是说在您生病的整个过程中,没有得到任何治疗?
袁:没有,就是拉肚子拉得实在太厉害时,不让你上班。还好,我后来慢慢地好了,能够吃饭了。
王:您还记得您生病这段时间有多久?
袁:大概半年左右,从天冷的时候一直到天气快暖和的时候才好了。我也不清楚是不是自己拔火罐医好的。我没生病的时候,不是有条毯子嘛,我就把一条毯子一剪二,用根草绳绑住裹在身上,外面再穿上衣服。就这样子,每天总有一两个人饿死的或者冻死的。虽然我因祸得福生病的时候没有上工,但每天晚上都(看到)有抬死人回来的。我们202个人,一共死了六十多个人,基本上三个人里面死一个,有被冻死的、饿死的还有被打死的。
王:你们干活的时候他们还打你们?
袁:是啊。因为干活干不动啊,吃不饱能干得快吗?他们就用皮鞭、棍子打我们。松江有一个劳工在推火车的时候受了日本工头的打,他一下子滑了下去,手指头被压在火车轨道上,把半个手掌都压掉了……
王:抗战胜利后,你们怎么回来的?
袁:我们是在国际红十字会的帮助下回来的。
王:那原来广告上写着会给你们的报酬,都兑现了吗?
袁:没有。到最后放我们回来的时候,他们给了我们每个人很少的钱。
王:这还是在他们投降以后?
袁:对。
王:这段经历,对您此后的人生有些什么样的影响?
袁:当劳工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之所以有这样的遭遇就是当时国家太弱了,如果我能活着出去,我一定要从军保卫家园。所以,回国后我没有去父母那儿,而是加入了浦东游击队。刚被放回来,就直接从回来时住的招待所入伍了……
上海劳工唐绵昭:
王正瀚(以下简称王):唐老先生,您当年被掳去日本做劳工是什么样的情况?
唐绵昭(以下简称唐):我原来是怡和船厂的船员,经常在上海和香港之间来回跑。战争爆发后,香港被日本占领,我就失了业。1944年夏天,当时日本人已经进租界了,有一天我在杨浦区和虹口区的外白渡桥附近,看到墙角上有一个广告招贴,这个时候日本人还不是明目张胆来抓人,而是通过广告用招工的办法来骗。
王:具体您还记得这个广告上是怎么写的?
唐:它上面写着任何工种都要的,工资多少多少,就这样子说。
王:它上面有没有写招工到哪里去?
唐:没写到什么地方去,就讲招工,因为当时上海招工很多的。招工后我们就登记去了,登记时他们让我们到杨树浦公平路码头的一个仓库里面去报到,一进去就不好出来了,那里四面都有铁丝网,日本人已经站好岗了,没办法出来了。我们等于是被欺骗去的,这时候家里一点也不知道。这恐怕都是叫汉奸干的,一共被骗去了三百多个人,连大学生也有。因为日本人来了后,失业的人很多,许多店家、厂家都关门了,我就想去找份工作,谁知道是骗人的。一进去等人到齐了,他们就用卡车把我们押送到杨树浦的一个码头上,日本人当时用枪押着我们先到小船上,小船到了吴淞口外面,日本人的大船已经等好了,再用大船把我们运到日本北海道。
王:您当时几岁?
唐:22岁。
王:从这时起您与家里就没联系了?
唐:对的。这个时候母亲听人说我被关进去后,还曾经来找我,但是已经没办法(救我出来)了,后来就一直哭哭啼啼,把眼睛也哭瞎了,我当时还有一个弟弟。
王:那你们到了日本后又是什么情况呢?
唐:哦,我们到了北海道夕张址(给采访人看材料)一个叫角田煤矿的矿上。去了后先叫我们跑步,因为以后要下矿劳动的,不锻炼的话,下矿后身体会不行的,所以先让我们培养体力,每天让我们兜圈子跑,跑了大概个把月吧,就下矿井了。
王:那你们当时做的都是什么活呢?
唐:有各种工种,有的是铲煤,有的是操作马达。我主要是铲煤,一天最起码干12个小时。早上出去到夜里回来,就给带一个饭盒,一个饭盒子里面可以说80%是杂粮、野菜、黄豆,少量的、最多只有20%的米,这一盒子东西吃完就算数了,就没了,回来也吃一盒子饭,一天就两顿。那么零下几十摄氏度怎么办呢,只发了一套衣服,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是夏天,没什么衣服,到那边天冷了,我们要开矿干活,他们才发了一套粗布的工作服,一条毯子,一双日本的跑鞋。
王:你们到北海道时是1944年的几月份?
唐:七八月份。这个时候天还热,都穿着汗衫、短袖衣,到了十一二月份就冷起来,零下三四十摄氏度,但我们要照样工作,没办法了只好用毯子裹在身上,再穿上衣裳去上工,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几十个人挤在一起,把毯子合起来盖,用身体相互取暖。
王:那你们平时睡在什么地方?
唐:就榻榻米。
王:你们住的地方离做工的地方有多远?
唐:走过去大概一个多小时。
王:住的地方怎样?
唐:很差的,就是板房,我们自己想出的办法大家挤在一起,否则要冷死的。在那里可以讲是吃不饱,又冻又冷,工作更不用谈了,这种煤矿开采都是强劳动力,你吃力了想坐一坐,日本人皮条就啪、啪抽上来了,他们专门派工头监督我们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些人做了几个月吃不消了,有的人选择自杀上吊之类的,有的人选择自残,甚至(自己把)手指头斩掉,因为他们实在没办法了,斩掉手指头就不能做工了。我那个时候二十几岁,年纪轻,身体还可以,但做了大概半年工夫,也实在吃不消了,就打算逃跑。我们逃跑的连发起者一共有六个人,一个被抓住了,五个逃走了,逃出去后就跑到深山里面去了,结果第二天也被他们抓住,因为逃的时候是盲目的,只晓得吃不消了就逃,从板房出来就是荒山野林,路我们又不熟悉。抓回去后,他们要杀一儆百了,把我们五个人衣服全部脱光,一丝不挂,让三百多人围起来,就拿皮条当众抽打我们,杀鸡儆猴——你们以后还逃吗?逃就这样子。
这个时候不谈了,讲起来眼泪都要流出来了。打好后再把我们关起来,他们那里也有牢房的,我们就睡在水门汀的地上,五个人被捆在一起,一天只给吃一顿饭,连水也不给喝,渴死了我们只好趁放风的时候把小便倒掉,用盛小便的桶盛点自来水拿回来喝,就这样过日子。关了大概一两个礼拜,我记不清了,再放出来继续工作。这个时候还让我去挑猪食,在冰天雪地里,一双跑鞋穿了一年,已经破得一塌糊涂了,我自己用针线补上补下,没办法再补了,又没袜子,就一双破跑鞋,零下几十摄氏度冰雪积得很厚,我的这个脚就发炎了(给采访人看伤脚),肿得很高,路也没办法走了,就帮你剪掉。
王:他们没有给你任何医治?
唐:对,就把脚上烂掉的肉剪掉,痛得不得了。
王:当时也没有上任何麻药?
唐:没的。他们就不把你们当人,你死了,再来一批,无所谓的。因为日本人到处侵略,他们国内没有人了。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后,他们才对我们稍微客气一点,这个时候美国人进来了,他们看到我们就把我们送回上海,就这样回来了。日本人投降后,我们解放了,就要跟他们算账了,来的时候他们说好给多少工资,我们在这里受了多少苦,他们也是企业,有办公室的,我们就到办公室跟他们算账。
王:你们在日本干活时他们没给过你们任何报酬?
唐:没的,没的。所以我们去问他算,他们说手里没有钱,就拿出一点点零用钱,一两天就用完了。我们就提出:一个工资要给我们算清,另一个要赔偿我们的精神损失,七十多个人死了,他们的骨灰等后事要抚恤好,我们两百多个人当时也斗争过的。
王:您刚才说你们去的时候是三百多个人,有七十多个人死在那了?
唐:对,七十几个。
王:那这些条件都是你们回来前向他们提出的?
唐:对,回来前提出的。结果就答应一条让我们回去,这个时候我们想能回去就算了,就没再斗争下去。当时回来后国民党也没管我们,我们也没提什么。后来解放了,中日友好,我们的这种问题要服从大局了,那么,我们斗争的想法一点一点淡薄了,一直到后来,有一个人从日本回来了,他在日本的山里面待了七年,做野人七年,后来被日本人发觉了遣送回来。他的儿子跟日本人打官司,报纸上说日本法院已经判定胜诉了,但日本政府不同意,他们说当年中日友好条约中我们已经放弃掉一切赔偿了,但我们说我们是为企业开矿的,跟国家无关,我们官司打了六七年,结果都败诉了。我们的要求,第一是我们这样做苦工,最起码的工资应该给我们;第二,我们精神上受的折磨,又怎么说呢?当时全国各省各地都有被抓去做劳工的,但现在打官司的门被关上了……
后记:
如今身居上海的两位老人,过着与其他普通老人一样再平凡不过的生活,但他们都称比起那些永远也不能回到家乡的难友,自己已十分幸运了。在采访的过程中笔者能感受到当年的痛苦经历对他们的烙印之深,以及他们所流露出的对至今仍不愿承担罪责的日本政府的不满。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赔偿,还有一种公道一种正视历史真相的态度。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