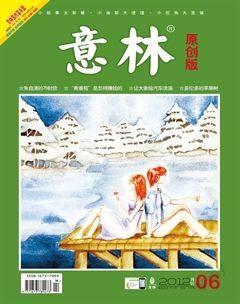时光又老又旧
2012-07-06 14:37云泥
意林原创版 2012年6期
云泥

午后的阳光如果穿堂而过,落在那些陈旧的家具上会是怎样的一种况味?我们都知道,这种昏黄压低了岁月的终点。
我妈妈收拾好最后一个包裹,跟着哥哥搬进新的住处的时候,她花白的头发一定会有几根散落,不!是遗落在老屋的门扉后面,我们在那里嗅着她的味道成长,长大了又想着办法在新的家里剔除老的痕迹。我们宁愿收藏一本老的书籍,甚至更喜欢翻阅它发霉的腐味,也不愿意看见时光刻在镜子里的那个还以为年轻的自己。
常常对着镜子问你是谁,然后又回过头来,在母亲的脸上搜寻我将来的样子。我分明在她的眼里看见了黄昏垂暮的场景,目光那么执拗,言语又那般不清。
想念那些午后的阳光,穿越老屋的葡萄架,射进屋里的日子。那时的父母都还年轻,母亲因为我贪玩逃避劳动,挥舞着手中的扫帚四处追赶。我像长了鸡的翅膀,山羊的腿脚,跳得又高,跑得又快。
父亲是用沉默表达他的爱护的,我常在我们俩约好的地方发现那个时代少见的水果。那个时光眼神就是代码,只是一转身的工夫,父亲就只剩下墓碑前的瓷片,不变的笑容永远停留在四十年前。
得了帕金森的母亲每天用双手抖落剩余的时光,我真想把我儿时长出来的鸡头凤脚还给父母。现在,母亲剩下的时光都是从阳台的这头,到阳台的那头。
我问,此时的阳光如何?我以为她会回答甚好!
她趴在窗臺踮起脚尖看看窗外,眼神空茫着说,时光同我一样又老又旧。
我相信,婴儿的眼睛与身边的老人比起来真是清澈。人看得越来越多,眼神就越来越混浊,不管清晨还是黄昏,这两代人的眼里绝非同色。
儿子躺在黄昏的沙发上,吃着点心看借来的笑话,笑声穿越客厅塞进我们的卧房,打碎了我和母亲又老又旧的时光。母亲抖着双手爬回她的床上,而我,坐在电脑前,只请进来一半的夕阳。
那些又老又旧的时光一半晒在深色的地板上,一半留在了开着小花儿的桌沿儿上。
猜你喜欢
趣味(作文与阅读)(2022年3期)2022-06-10
江苏科技报·E教中国(2022年5期)2022-05-11
摄影与摄像(2021年3期)2021-10-31
青年文学家(2020年10期)2020-04-27
时代邮刊(2019年24期)2020-01-02
华人时刊(2019年19期)2019-11-18
文苑(2018年19期)2018-11-09
意林·全彩Color(2018年5期)2018-05-31
东坡赤壁诗词(2017年3期)2017-07-05
小天使·四年级语数英综合(2017年4期)2017-0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