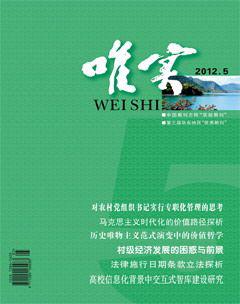儒家思想视域下我国传统社会弱势群体救助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1YJCZH093);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资助项目(B-a/2011/01/018);南京大学国家社科基金预研项目;江苏省博士后科研基金(1102030C)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梁德友(1971- ),男,安徽宿州人,法学博士,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流动站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社会学、社会保障理论。摘要:我国传统社会存在大量的弱势群体,从类型上可以划分为人伦缺失型、经济匮乏型以及社会排斥型三种类型。在儒家“人本”、“仁治”理念影响下,我国传统社会救助弱势群体实践采取“教”、“养”结合的方式,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伦理关怀。但由于时代和历史的局限,传统视阈尚存在诸多狭隘与不足。梳理与反思我国传统社会弱势群体救助的思想与实践,对当下我国社会救助制度建构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弱势群体;救助;儒家思想
中图分类号:C91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12)05-0029-05
在我国漫长的传统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动荡及天灾频繁等原因,弱势群体一直是我国历史境遇中的主要问题,从官方到民间、从理论到实践,都对其给予充分的关注,积累了丰硕的救助弱势群体的宝贵经验。总结我国传统社会弱势群体救助的理论与实践,对当下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关怀社会弱者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我国传统社会弱势群体类型
“弱势群体”(Vulnerable groups)又叫失能群体、脆弱群体、困难群体等,主要是根据他们在社会中较差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境遇来定义的。根据弱势群体产生的原因与特点,我国传统社会弱势群体大致可以分为人伦缺失型、经济匮乏型、社会排斥型三种形态。
1.人伦缺失型。人伦缺失型弱势群体主要是指鳏、寡、孤、独、废、疾等群体。人伦关系是我国传统社会维系家庭关系和人际关系的主要纽带,是作为社会的人得以生存发展的主要社会资源和外部支持。但是,鳏、寡、孤、独、废、疾等却面临人伦断裂,他们因得不到血缘亲情的帮助与关怀而沦为弱势群体。“少而无父者谓之孤,老而无子者谓之独,老而无妻者谓之鳏,老而无夫者谓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穷而无告者也,皆有常饩,喑、聋、跛、躄、断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礼记·王制》)这是我国古代典籍中较早对社会弱势(不幸)群体的概括。有的学者把此类弱势群体又称为人伦缺失的“穷民”,认为从唐虞三代直至魏晋南北朝,社会弱势群体主要是鳏、寡、孤、独、废、疾者。[1]为什么中国传统社会存在大量的人伦缺失型弱势群体?笔者认为,除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不发达(如营养、医疗、社会保障等)等原因外,主要是由于战争、疾病等造成了大量的家庭成员残缺、身体残疾,从而造成人伦缺失型弱势群体大量出现。据史料记载,春秋242年间,发生战争达480次;战国248年中,大规模战争共达222次。就连中国封建社会相对稳定繁荣的唐朝,也发生过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造成无数家庭破碎、骨肉分离、夫妻难聚。[2]人伦缺失型弱势群体不但经济上比其他人短缺,而且缺少来自家庭、亲情的支持,是中国传统社会弱势群体的主体。
2.经济匮乏型。经济匮乏型弱势群体主要是指在社会资源占有上处于不利地位,经济极度贫困,几乎无法维系基本生存状态的“穷民”。这部分弱势群体抵御各种社会风险的能力极弱,特别是在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社会灾难时无法继续维持基本生存,只能沦为赤贫者。经济匮乏型弱势群体的主体是灾民、贫民,等等。
灾民指受自然灾害影响而无法生存或生存艰难的人。历史上,作为“灾荒大国”的中国,历来是“三岁一饥,六岁一衰,十二岁一荒”[3]。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英国学者李约瑟教授曾统计:“中国每6年有一次农业歉收,每12年有一次大饥荒。在过去的2100多年间,中国共计有1600多次大水灾,1300多次大旱灾,很多时候旱灾和水灾会在不同地区同时出现。”[4]频繁的自然灾害使得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史书上“人相食”、“白骨蔽野”的记载时有发生。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中统计,仅清朝因饥荒而死的人数:嘉庆十五年为99万人,十六年为2000万人;道光二十九年饿死1500万人;咸丰七年为500万人;光绪二至四年,死亡1000万人。即使在丰年盛世的汉唐,也时常出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惨景象。[3]另外,经济匮乏型弱势群体还包括大量的贫民。贫民主要是指经济贫瘠,生活难以为继的人群。他们在身份上属于自由民,在职业上主要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等,但经济地位低下,受到社会歧视。例如,商鞅变法时曾规定:“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奴。”把“怠而贫者”与“事末利”的工商业者相提并论,一同治罪。[5]42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手工业失业者也是贫民的主要组成部分。[2]由于大部分小手工业者都是家庭手工作业,规模小、技术落后,抗风险能力较差,加之统治者的剥削与敲诈,我国封建社会小手工业者经常面临失业与破产的风险。特别是近代以来,由于资本主义的入侵,大批手工业者纷纷破产,成为贫民弱势群体。
3.社会排斥型。该群体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社会排斥,其弱势的形成主要来自外部,属于社会性弱势群体。社会排斥型弱势群体主要包括贱民、难民等。贱民是指对强势群体有一定的人身依附、自己没有社会地位和人身自由的社会群体。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贱民主要包括:奴隶(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属于奴隶主的私人财产)、杂户(政府直属奴隶,由地方政府管辖,战时调拨入伍)、声音人(地位与杂户一样,归太常寺管辖,世代担任乐工)、官户(犯罪之家,由司农寺管辖,男子为农奴,女子多发配洗衣局)、工户(少府寺管辖,世代担任工匠)、乐户(包括妓女、戏剧演员和其他游艺从业人员)、部曲(贵族私人所属的农奴,其后裔永远是农奴)、客女(贵族所属的女奴)、妓女、奴婢(是最下贱、最卑鄙、最哭诉无门的奴隶,身体生命全掌握在主人之手),等等。[5]43以妓女为例,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春秋以后,妓业已很发达。[6]到唐代,唐玄宗立“教坊”,官妓达到鼎盛。宋代根据侍奉对象把妓女分为官妓、家妓、营妓、军妓、僧妓等;按技艺分,则有舞妓、乐妓、歌妓等。明清妓业仍在发展。妓业的兴盛说明妇女求生艰难。在男权社会里,妓女是男人的玩物和泄欲的工具,她们的人格被剥夺,没有地位,没有生命保障,被奴役、被蹂躏、被侮辱,同婢女、宫女、奴仆一样,处于社会底层,是典型的社会弱者。[2]
二、我国传统社会弱势群体救助理念:
以儒家思想为例
早在2000多年前的两周时期,富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就提出了“保息六政”(《周礼·地官司徒》)的社会福利政策。其后,儒家倡导的“仁政”和古代许多思想家提倡的“兼爱”、“博爱”和“饥者得食,寒者得衣”的观念,都蕴涵着丰富的救助弱势群体思想。其中,儒家的“人本”、“仁治”理念是我国传统社会弱势群体救助的重要精神资源和价值基础。
1.贵人、爱人。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强调人的重要性,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早在2000多年前孔子就说“天地之性人为贵”,指出天地之间、万物之中,人是最高贵、最有价值的。另外,儒家还提出“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苟志于仁矣,无恶也”[7]35等人本主义思想,体现了对人的价值的高度重视。孔子的“仁者,爱人”是儒家向家庭、家族、国家以致整个社会提出的关爱他人的一种伦理诉求。这种爱人观从政治伦理的角度体现了人的价值和尊严,反映了儒学对“人”的伦理关怀。孟子虽然重“天命”,但其思想的主流却是强调人性与义理相通,把人本质的信仰转换到人是自己的最高本质的认识上来,从而将世界真正视为“人的世界”。孟子说“仁义理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正是对普遍人性的揭示。在儒家传统思想里,人的这一普遍人性具有内在的超越性,从而使人具有绝对的尊严和平等性。儒学维护人的价值和尊严是以尊重、关爱、理解他人为前提条件的,这主要表现在孔子的“爱人”上,其内含了对他人的尊严的肯认。更难能可贵的是,儒学谈论人的价值和尊严虽然立足于人的道德性、社会性等方面,但它并不拒斥人之自然性,只不过,更强调人之自然性应以社会性为引领。《论语》就多处强调人的自然属性,如“欲富”、“欲贵”、“好色”等语,以致荀子认为“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不事而自然谓之性”[8]274。
2.重民、利民。所谓重民,就是重视“民”,把“民”放在重要位置。特别是统治阶级在处理与被统治阶级的关系时强调以“民”为主,把“民”作为统治的重要因素来考量,孟子就强调“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9]51。《尚书·五子之歌》已有“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10]之语。但真正把“民”纳入“仁学”范畴,并从人文关怀的视野对其作出审视的则是孔子。《论语·先进》所说明的“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等,都表明其回避、怀疑天命鬼神的用意在于致力社会人事的思考和处理。他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7]36朱熹注曰:“民,亦人也。”孔子在这里把“民”纳入了“人”的“大共名”。孔子还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7]61不仅把“民”视作道德理性的个体,还认为“民”的价值取向也是追求“仁”。此后,孟子在继承孔子“仁学”民本观的基础上提出了“政在得民”说,荀子则提出“尊君爱民”说,指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
另外,中国传统儒家的民本观还强调“利民”。丁原明教授认为,利民是儒家强调统治阶级执政伦理的价值取向,即不做不利于广大人民的事情,要求统治者必须坚持“德治”、行“仁政”。其具体内容包括“制民之产”与“取于民有制”等,就是要给人民维持其生存的基本物质生活资料,并把对他们的榨取限制在规定的范围内[11]。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孔子主张“惠民、养民”,他说:“养民也惠”[7]78、“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7]4,把“民”与“人”放在同一天平上来称量,并主张给人、民以物质实惠。
3.平等、无类。儒家思想认为,人与人之间不存在高低贵贱的类别,众人皆平等,对于社会弱者也应一视同仁。《诗经》中说:“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强御。”(《诗经·大雅》)孔子一贯认为“仁”作为人之为人的最高美德,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在求“仁”的道路上,人们都是平等的。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具有成就仁德的能力,只要加强自我修养、慎独克己、不断追求,就一定能成“仁”。正如孔子所说的:“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7]74孟子则认为在道德价值面前人是平等的,不存在高低贵贱。为此,他直接喊出“尧舜与人同耳”,并赞同“人皆可以为尧舜”[9]573。孟子之所以认为圣、凡可以同类、平等,是因为在他看来,在“人之所贵”之外还有“良贵”,公卿大夫在其“人爵”之外还有“天爵”。所谓“良贵、天爵”即是人的内在价值,也就是人人具有的先天道德意识。故而,所谓圣、凡平等即是人的道德价值和人格尊严平等,亦即人只要尽自己的主观努力,则“涂之人可以为禹则然”[8]274。另外,在男女的社会地位上,儒学虽然主张男尊女卑,但在处理家庭伦理关系中,有时也给妇女以某种程度的尊重,主张男女平等[11]。这一切都说明,追求圣、凡平等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和价值诉求。当然,客观地讲,在中国传统封建社会中,人的等级、贵贱一直是社会存在的客观事实,儒家文化中的平等主要是从道德的角度论述的。
三、养之、教之:我国传统社会弱势群体救助实践
“养之”就是把人的生存权放在首位,从物质上对其进行帮助;“教之”是指在“养”的基础上,对弱势群体进行教育,不断提高其自身素质和道德水平,使他们在“养”的基础上实现“助者自助”,最终融入主流社会。通过历史考察,笔者发现,先秦至隋唐的救助制度都是重养轻教,直至南宋末年,才开始注重教化。由此,施善与教化就成了中国传统社会救助社会弱者的重要实践旨趣。
与西方主要是宗教慈善机构承担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不同,在我国传统社会,政府一直是救助弱势群体的主导力量,是第一责任主体。据史籍记载,西周时期中央政府即已设立专门管理救灾食物的官职——“地官司徒”,并已开始建立了对后世有着重要影响的仓储后备制度。汉代以后,从存问制度的设立到对年老、鳏寡、废疾及贫困之人定期或不定期的物质赏赐,使得国家对弱势群体的救助更加系统化。到南北朝时,国家设立了六疾馆、孤独院等专门的收养机构,对鳏寡孤独、贫病无依者以集中救助。唐宋时期不仅救助措施比较完备,而且救助政策渐成惯例。在赈济、蠲免、调粟、仓储、安辑、养恤以及捕蝗、袪疫、薄关税等方面,大凡能救助弱势群体的各种救助措施,基本上都出现了。例如,南宋著名的养济院有临安府养济院、建康府养济院和绍兴府养济院。《咸淳临安志》记载:绍兴二年,诏临安府置养济院,将街市冻馁乞丐之人尽行依法收养。除收养乞丐外,对那些鳏寡孤独废疾者也进行救助,救助标准为“大人日米一升,钱十文省,小儿减半”(《宋会要辑稿·食货》)。元明清时期,救济事务在继承了前代成果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社会救济内容和方式愈加丰富,统治者对社会弱者的救助工作也越来越重视。例如,《明史·成祖本纪》记载,明成祖“闻河南饥,有司匿而不报,逮之并榜示天下,今后有水旱灾伤不报者,罪不赦”。
进入晚清社会,西学东渐。西方国家救济灾荒以及对贫困群体救助的做法、政策和思想理念得到广泛介绍和阐释。当时,在华的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曾多次撰文呼吁中国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的所谓“养民新法”,通过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大幅增加全社会产品总量解决所谓的“养民”问题。受西方思想影响,中国开始借鉴、学习西方先进的社会救助经验,并结合中国传统社会救助方式、方法,尝试探索适合于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弱势群体救助方法。例如,清人赵元益在其《备荒说》一文中提出了树艺、绘图、农学、铁路、保商、治河、蚕桑、制造等思想。其中,农学、铁路、保商、制造则直接借鉴于西学思想。积极主张变法图强的文廷式也向朝廷建言:学习西法,发展生产,“可养无数贫民”。
中国传统社会对弱势群体的救助不仅重“养”,而且强调教育在人生中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意义。在儒家看来,除了物质上的满足和自然生命的保障外,重要的在于“教”,即文化知识、道德品质、生活技能等方面的培养和教育。孔子说:“既富矣,教之。”(《论语·子路》)孟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荀子说:“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立大学,设庠序,修六礼,明七教,所以道之也。”(《荀子·大略》)董仲舒也说:“古之王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法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汉书·董仲舒传》)由此可见,我国传统社会普遍认识到了“教”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和重要作用。因此,在对弱势群体救助的过程中,执政者非常重视“教”的意义,强调“养”、“教”结合。例如,史料记载,蔡京当政后,实施“孤贫小儿可教者,令入小学听读,其衣襕于常平头于钱内给造,仍免入斋之用”(《宋史·食货志》)。
不过,我们也不难发现,这些“教”主要是伦理方面的教育,是统治者维护和强化其统治的一种手段,也是我国传统社会重“价值理性”而轻“工具理性”的突出表现。到了明末清初,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外国势力的入侵,西方救助弱势群体理念的传入,“教”的内容开始向“工具理性”倾斜。以经元善、张謇为代表的一些实业家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将西方的社会救济思想与自身的社会实践相结合,大力提倡“教养并重”的救助理念,宣传介绍西方社会救助活动中“教”的功能。思想观念的变化导致救助方式的转变。光绪27年(1901年)10月,革职侍读学士黄思永提出在京城之外城“收养游民,创立工艺局”的建议,得到光绪皇帝允准。由此,在中央政府的倡导下,各地纷纷建立起“工艺局、工艺厂”等新式救助机构,注重被救助者生存生活能力的培养,改变以往单纯救济的救助模式。[12]通过成立专门机构“授之以渔”,进行职业技能的培训,需要帮助的人群就能够掌握某种专门技术,从而实现“助人自助”。
四、我国传统社会弱势群体救助的反思
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我国古代弱势群体之“弱势”不是经济弱势、生理弱势,更不是政治弱势,而是人伦缺失。[1]所以,我国传统社会十分重视对弱势群体的伦理救助,强调从道德角度出发救助弱势群体,注重发挥家庭、家族、血亲关系的特有功能,从人的亲情关系入手去救助。“这种救助的路径既调节了基层社会,即宗族内部的关系,又增强了民众对政府的认同与归依;既有宏观的大同理想与德政管理,又有微观的个体修为与人伦救助。这些都曾经有效地发挥了它的社会保障与稳定功能,在整体社会风气的关注与改善上也颇有成效。”[13]我国传统社会救助社会弱者的这种路径偏好,笔者认为,一方面,是由我国血缘、地缘的农耕文明决定的。我国长期以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每个人生活在相对固定的地域,形成了伦理本位的人伦社会,这决定了我国传统社会更重视人与人之间地缘、血缘的相互依存和扶助,而非现代商品经济下人格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契约关系;另一方面,是由我国传统文化本身的特质决定的。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吸收各学派所长和外来异质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和以互助、均富为主要内容的道教思想。自汉代始,以慈悲观念、因果报应为代表的佛教思想传入中国,更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浓厚的伦理意蕴和伦理价值取向。故此,我国传统社会对弱势群体的认知自然具有浓厚的道德色彩。
在儒家思想指导下,我国传统社会对弱势群体的救助活动得以延续,但由于时代和历史的局限,传统视阈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不足之处。首先,这种思想的贯彻不是靠规范的制度来实施,而是依靠所谓的“明主仁君”个人的道德感召和良心发现,随意性较大。故这种救助方式的存续往往是“其人亡则其政息”(《礼记·中庸》)。既会因人而设,也会因人而废。救助制度缺失,难以形成对弱势群体救助的长效机制。其次,具有浓厚的道德色彩,救助被冠以当政者体恤民众、广施仁政的名号,被看作救助者的恩赐。因此,救助行为总是由当政者或地方官僚自上而下地单方面发起和推行,弱势群体在救助实践中往往只有被动地等待和接受,享受不到作为社会平等一员所应有的尊重,是典型的“暴力关怀”。这种“嗟来之食”迫使弱势群体常常为了“五斗米”而折腰,不可避免地在人格、尊严、自由和自主方面受到伤害,使本来温情脉脉的救助活动失去本真的价值和意义。再次,作为政府的一种职能,传统社会救助弱势群体的理论和实践都缺乏目的性、计划性和整体性,是国家主义建构的一种形式,存在着政府公权挤压、侵犯受助者个人私权的行为。最后,中国传统的救助方式比较重视从物质方面入手,强调“济贫”,突出所谓“养”的内容,忽略对弱势群体精神的关顾和支持;而“教”的部分大多限于对社会弱者进行伦理规范方面的教育,“忽视了对被救济者摆脱贫困、择业谋生能力的培养,忽视了对他们综合素质的提高。这样一种救助方式,没有发挥被救主体的作用,其救助效率及效果,均由此而受到局限。这也是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下,社会救助形式的一个重要特点”[12]。另外,在救助实践中,由于封建等级的偏见,救助手段和救助方式的伦理含量不高;把救助仅仅看成一种慈善活动,没有给予受助者充分的尊重与理解,恩赐色彩浓厚。这都说明了我国传统社会救助弱势群体的历史局限性和不足。□
参考文献:
[1]仇婷婷.我国传统社会弱势群体救助思想与制度的历史变迁[J].政法论丛,2008(3).
[2]蔡勤禹.国家、社会与弱势群体——民国时期的社会救济(1927-1949)[D].
[3]许宝键.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评述中国成功解决12亿人口的吃饭问题[N].经济日报,1999-02-28.
[4]岑大利、高永建.中国古代的乞丐[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5.
[5]张敏杰.中国弱势群体研究[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3.
[6]王书奴.中国娼妓史[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8:37.
[7]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4.
[8]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6:330.
[9]焦循.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0]孔颖达.尚书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6:156.
[11]丁原明.儒学的人文关怀与现代制度文明[J].齐鲁学刊,2005(3):7-8.
[12]陈桦.中国社会救助活动的近代转型[J].学术月刊,2007(12).
[13]刘华丽,李正南.中国古代社会福利思想综述[J].南昌高专学报,2003(1).
责任编辑:戴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