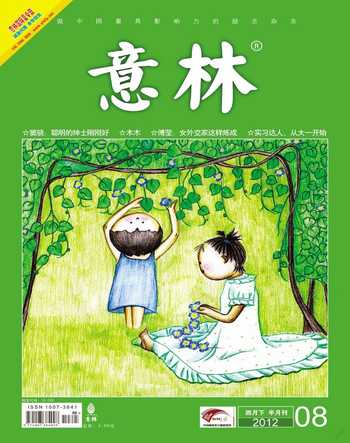薄雨清明
2012-05-31 01:24:00简媜
意林 2012年8期
简媜
清明之后的薄雨天气,水乡居民得了很好的理由不出门。
屋瓦上,炊烟如一条游龙,惊动竹林内避雨的谷雀,以为起了雾,走了雨。
我从街道走过,湿滑的石板拉着我的瘦影。影子浮在石上,有种人在江湖之感。
瓦檐下的民家正在烹煮什么呢?祭祖的牲礼还在,此刻或有巧妇站在灶前,料理今晚的丰宴。清明之后,邀亲族聚坐,说说生的年岁或逝者的逸事。
雨季不适合出游,雨丝湿了衣袖,步履也因吃水益加沉重。是谁家的窗口飘来一阵药香?闻来像刚起炉的参汤。是窖喜的新妇吗?还是久病短了元气的老妪?
雨阵收山了,屋檐滴下水珠。闷慌的孩童纷纷夺门而出,街坊间一阵脆亮的童谣。
未出门的人忙些什么?为一场宴席愉快地躲在厨内?为一件远行的袄子,不能停止针线?还是卧褥上响起亲人的咳嗽声,扶起她正在拍背?
风雨无私,漂洗众家屋瓦,可又让人担忧,一寸寸洗下去,总有瓦薄的时候。届时,我若回到这里,这些人会在哪里继续他们的故事?
人世不斷衍生悲欢故事;欢乐的末节带了悲伤的首章;而悲伤又成为另一篇欢乐故事的楔子。有了这些,使大雨中的人们懂得安分守己,与所系念的人更接近,共同品尝一桌佳肴,举杯祈求今岁平安;也借着一碗参汤,把无怨无悔的细心和盘托出,人的有情必须放在无情的沧桑之中,才看出晶亮。
时间,从来不善于人情,万年之后,我与这些人都要消逝。那时,也还会有清明的乡宴;会有突然的骤雨打在民家屋顶上,只不过熬药的人换了面孔,雨中游吟的人换了布履。相同的是,仍有无家可归的心,无法根治的宿疾。
就连白鹭也还用旧日姿势飞翔,只不过停栖的沙洲已垦为良田,而今日街坊化为茫茫沧海。
我仿佛看见未来的一只白鹭,正好栖息在打帘子、挨着窗台做针线的新妇旁边。
(姬月摘自《哲思》2012年第4期)
猜你喜欢
散文诗世界(2021年5期)2021-09-10 07:22:44
少年文艺(2020年10期)2020-10-12 02:41:04
西湖(2019年6期)2019-06-11 03:03:08
食品与发酵工业(2017年12期)2018-01-03 05:43:49
文学港(2016年11期)2016-12-20 18:57:03
食品研究与开发(2015年8期)2015-10-27 02:00:18
小猕猴学习画刊·下半月(2015年10期)2015-04-29 21:19:50
诗歌月刊(2014年11期)2015-04-20 00:11:25
大众考古(2014年11期)2014-06-21 07:18:44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2013年10期)2013-03-06 08:2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