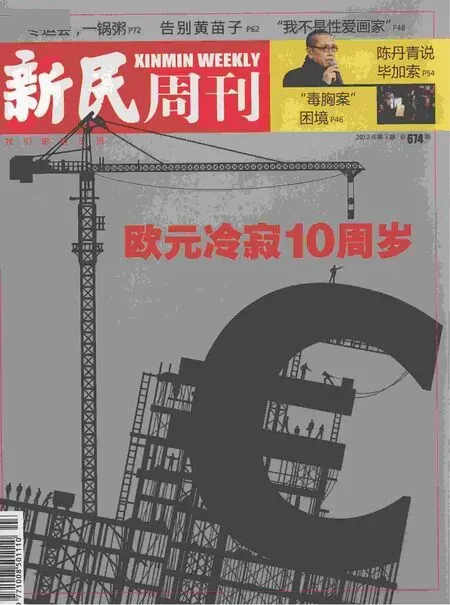汪峰:在摇滚的存在中怒放
何映宇


老无所依,生无所求。
这个世界,是让你充满挫折感的世界,如同多年前,那迷惘的青年,站在北京建国门的立交桥上,俯视着芸芸众生,内心悲凉:
“我将在今夜的雨中睡去,伴着国产压路机的声响,伴着伤口迸裂的巨响,在今夜的雨中睡去。”——《晚安,北京》。
如果,睡去,就可以不理会这世上的纷纷扰扰,就可以坦然面对我们内心的荒凉与恐惧,那么,这是一种让你存在的方式。
可是,如果你必须醒来,疼痛着清醒地活在当下。你就要忍受各种荒谬各种悲催,忍受一次次尊严受到侮辱、心灵受到欺骗的愤怒,这,也是一种真实的存在:
“多少人走着却困在原地,多少人活着却如同死去;多少次幸福却心如刀绞,多少次灿烂却失魂落魄。”
这是汪峰最新推出的专辑的主打歌《存在》中的歌词,这首歌在网上一经推出就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依旧是汪峰发自肺腑的呐喊,是不是也触动了我们活在当下的无奈感?
摇滚,是不是一种拯救心灵的力量?去听一听汪峰最新的双CD的唱片《生无所求》,也许会有新的感悟。
汪峰,在摇滚的存在中怒放!新唱片刚刚发行,全国巡回演唱会又接踵而至,1月2日,他在上海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举办了新年里的第一场个人演唱会。对于现在的汪峰来说,那些艰苦的岁月,都已成往事。
但,没有忘记。
正是在往事的废墟中,开出了摇滚的枪花;美丽,但长着尖锐的玫瑰的刺。
他的音乐,不是简单庸俗的励志或愤怒,他有灿烂阳光的一面,向着太阳展翅翱翔的自由与洒脱,也知道,如何面对这世界的冷漠与疼痛,即使,仿佛飞鸟一般坠落的刹那,也是生命残酷的怒放。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新民周刊》:你从小就学小提琴,学的是西洋古典音乐,在青春期的时候,听到罗大佑、崔健、Beatles、Bob Dylan等人的音乐,是不是对你原来的音乐理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汪峰:我觉得这真是好的音乐!甚至可以说已经超越了“音乐”这两个字!我觉得如果仅仅只是音乐的话,永远没有音乐可以超越古典音乐,那绝对可以称之为伟大和深刻的艺术!但是如果有了文字之后,文字和音乐组成一首歌曲,那就不一样了,它会产生巨大的力量,去影响一个人对音乐、对世界的看法。摇滚乐能以简单的方式直接冲击你的心灵,对于一个人的影响不需要前提,而古典音乐需要前提,至少是欣赏的基础,否则根本不可能,所以我觉得摇滚乐更容易打动一个人的心。
《新民周刊》:进入大学以后開始接触摇滚改变了你的人生轨迹,师兄小伟是你的第一个贵人,和他是怎么认识的?
汪峰:小伟是我们音乐学院老师的子弟,这样我们就在音乐学院认识了。他后来担任了我们“鲍家街43号”乐队的经纪人,他不会创作或演唱,但是很喜欢摇滚乐。在音乐方面,他有很强的前瞻性,这一点真是很厉害。事实上,当时,他很早就预判到中国摇滚乐后来一些会发生的事情。他对“鲍家街43号”时期的我们的帮助,包括如何去做摇滚乐、如何去做事,他都有自己非常具有前瞻性的看法,这些看法我都受益匪浅。
《新民周刊》:大学毕业以后也没有直接靠乐队生活。当时你进入中央芭蕾舞团担任副首席小提琴手,当时的工资五六千,在1990年代,那可以算是相当不错的收入了,可是你就是特受不了那种分裂的状态,觉得特别纠结,所以一定要辞职?觉得自己是个为了理想可以不顾一切的人吗?
汪峰:当时大学毕业,月工资是1300元,加上各种排练和演出一个月差不多有五六千元的收入。我没有不喜欢小提琴,但是我当时更喜欢摇滚,我更愿意写歌去创作,这两点也许有人能处理得很好,但对我来说却是完全对立的。我当时没有一边创作一边练小提琴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冲突,其实乐团跟国家机关没有任何区别,需要人浮于事,需要很圆滑,随时改变自己的立场来适应生存的环境,但是创作歌曲完全和这些没有关系,必须要完全真诚地面对自己,面对外部世界!如果你每天同时遇到这两种状态的事,那就会极为分裂!让我去应付?我做不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时候,你只能选择一样。
《新民周刊》:在“鲍家街43号”乐队时期,写了你的第一首代表作《晚安,北京》,据说当时你站在北京建国门立交桥,突然内心心潮起伏,当时是怎么样的回想与触动,成就了这首著名的《晚安,北京》?
汪峰:就是觉得很多年过去了,依然站在这里看周围, 还是那些建筑物,好像什么都没变,,实际上生活却发生了巨变,那种感触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特别特别大的一种震动。如果在那个时间节点之前,还是个十六七岁的孩子的时候,生活又不同,没有那么多烦恼,物质对人的影响不会那么大,感情生活也不是真正的感情生活,十年之后就不一样了,所以当时的感触特别大就写了一首歌。
《新民周刊》:“鲍家街43号”时期,在京文唱片出了两张专辑,可是生活却极为穷困,最穷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汪峰:吃饭还行,我不认为我有多困苦,如果是北漂,家不在北京的,那会更困难。我是北京人,实在不行了还可以回父母家吃饭。我最困难的时候大概就是连房租都付不起的时候,但是我觉得这也很正常,如果不吃苦,就成功了,那怎么可能?
《新民周刊》:穷到付不起房租的时候,问家里借钱,还给家里人打欠条,那时候有没有怀疑过自己的选择?
汪峰:从来没有犹豫过,我没有想我能成功,我想的是我应该不会失败,起点和原则我是有的!至少我应该不会没人搭理,我觉得不可能!我做了这么多年音乐,不可能出现那种情况。做事如果没有自信的话就别做了,但是不要盲目自信。
加盟华纳,商业与摇滚的坚持
《新民周刊》:在“鲍家街43号”到你加盟华纳的过渡阶段,你做了一些电影音乐,不可不提的就是2001年给王小帅的《17岁的单车》谱写电影音乐,那一次是王小帅找的你吗?你觉得做电影音乐和做专辑有什么不同?
汪峰:做《17岁的单车》是王小帅找的我。我和王小帅其实之前早就已经认识,大概在某个场合碰到后来大家都熟了,都是朋友,他说,他喜欢我的歌。
如果不是朋友,一般我是不会接电影音乐的,我觉得我不是很合适。做电影音乐和做自己的专辑有区别,你得要考虑电影的氛围和感觉,和表达自己的感受还有些不同。
但是要做好任何事都是一样的,要尽心尽力。方法不太一样,实际上花的精力也差不太多。后来也有人找我,我就没有再接,我更想做我自己的音乐,所以也就没有什么电影方面的歌曲出来。
《新民周刊》:在华纳出的《花火》那张专辑市场和口碑都双赢,据说是因为你特别喜欢北野武的电影《花火》所以写了那首歌并做了那张专辑,是这样的吗?
汪峰:也有点致敬的意思,其实还是因为自己有很多想法。
《新民周刊》:像《在雨中》、《幸福的子弹》这样的歌,唱片公司是不是也特别有意地考虑,在保持你个性的同时,更增加一些流行的元素?
汪峰:没有啊,那就是我那段时间写歌,里面正好有这一类的作品。我从来不会因为有人告诉我说你应该写什么去写什么,或者因为现在大家都有可能听什么然后我去写什么,在作品这一方面没有任何人可以决定或者是影响我。
《新民周刊》:就像《春天里》,还是有这样的感触,所以才写的?而不是像某些乐评人说的,写《飞得更高》、《勇敢的心》、《我爱你中国》这样旋律朗朗上口的励志歌曲,是为了迎合市场。
汪峰:为什么要考虑?这样说的人可能不明白当你有意识地考虑写首你认为老百姓喜欢听、可能会火的歌,这种想法真是极其愚蠢!从创作角度来讲,你真以为你有一个目标就能写出来好歌吗?这真的太可笑了!好的作品都是发自内心的,没有杂念、很单纯的情况下才会写出来。
我对我写歌的要求就是旋律一定要出色,这一点已经决定了它有流行性了,别的就不用考虑了,首先我就很喜欢好听的旋律的,这点是不冲突的。
《新民周刊》:我也知道你喜欢诗歌,比如说惠特曼的诗歌,或者是食指,写歌词的时候会不会向诗歌靠拢?
汪峰:创作方面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不同的歌不同。有一些歌我就希望有韵脚,但是有一些歌我就完全不应该有韵脚,去自由地表达,因为最重要的是音乐和歌词的表达。
《新民周刊》:加盟华纳之后,个人事业马上突飞猛进,很多内地歌手加盟海外的唱片公司都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你觉得问题在什么地方?
汪峰:这就说明,唱片公司跟一个国家、一个企业是一样的,你的体制决定了你的命运!如果一直是在一个错误的体制里,你就可以知道你最终的命运了,如果在一个对的体制里,现在吃点苦没事,你一定能熬出头,体制決定了你的音乐、你的付出有没有收获。
《新民周刊》:“鲍家街43号”签约的是内地的京文唱片,你觉得内地的唱片公司和海外的相比,差距在什么地方?
汪峰:规范化!海外唱片公司有版税,至少一个歌唱者有一定的经济收入,生活应该不愁。但是国内的公司没有版税,没有词曲费,而是给你一笔钱,这笔钱包括了制作专辑的所有费用,所以我在“鲍家街43号”的时候,基本上每张专辑我们乐队每人平均才分到三四千元。那个时候我们制作一张专辑费用比较高,大概要15万,录音需要花费10万出头,也许是十二三万,那剩下两三万7个人分,再加上公司还要抽掉一点钱,所以这是一个错误的体制!
华纳就有专门的词曲费,一首歌词多少钱曲多少钱,都要算清楚,版税就是我们先预估你这张专辑能卖多少,我提前给你钱,不用等到专辑发售以后,这至少也是一笔收入。包装宣传则是另外投钱,所以这是一个正确的体制。
《新民周刊》:这些年有没有看到特别优秀的年轻乐队,你对更年轻的中国摇滚音乐人怎么评价?
汪峰:有好的,但是少。都是基础问题有待解决,不是想法上的,而是方法啊技术上的问题很多,还有做音乐的底线有好多还没搞清楚。
《新民周刊》:这次你的巡回演唱会,为什么把第一站放到鄂尔多斯呢?这个时间那个地方应该也比较冷,也不是一线的城市。效果怎么样?
汪峰:效果很好,因为整个的巡演是由一家演出公司策划的。鄂尔多斯经济实力不成问题,这家公司的老总正好是鄂尔多斯人,希望以他家乡作为第一站,那我想也没问题,大城市小城市都要演,结果也是很好的,有1万多人来看。
之后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巡演,曲目方面,新歌老歌都会有结合,到了最后两场新歌的比例会增多的,因为我的新专辑刚刚发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