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北贫困带:生态保护背后的生存难题
南关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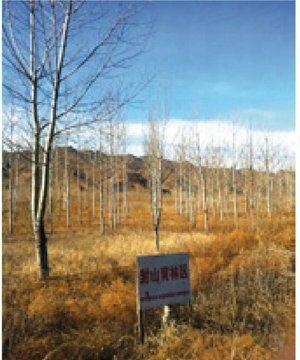
特约记者 山绿了,水清了,树多了,原住民们却变得更穷了,这是发生在河北接坝地带的怪现象。在北京以北100多公里外的大片贫困乡村,生态与生存成了一对悖论,其背后则是依靠行政命令强行推进的环境保护运动。
退稻变穷
太阳暖暖地照在黑黢黢的山峦间,残雪在阳光下格外晃眼。莽山之间,一条玉带印入眼帘,清亮亮的河水泛着鱼鳞的细光,这条河叫潮河,一路向北汇入北京的密云水库。
潮河在群山间蜿蜒奔突,河两岸的平地时大时小,把一座座村庄串珠一样连起来。长阁村是潮河边上一座较大的村庄,位于河北省丰宁县南关乡。正午时分,间或能见到一些人聚在村口晒太阳。很快你就会发现,坐在那里的绝大多数都是老人、妇女、孩子,男人们都走出山谷打工去了。
“我们这一带都是空心村。”一位村民说。天伦之乐、其乐融融的景象定格在5年前。先前,村里的青壮劳力大都留在家种水稻。这一带虽有水稻种植传统,但产量不高。上个世纪80年代初,当地通过兴修水利灌溉设施和推广插秧新技术,亩产逐年提高到1200斤左右,水稻种植面积占全村耕种面积的70%以上,“能上水的地方都种上稻子了”。
长阁一带的水稻远近闻名,蒸出的新米白中泛绿,糯香滑软,深受附近居民喜爱。农民足不出户,刚上田的新米就被外地客商抢购一空。当空气中弥漫着悠长的稻香时,长阁村一年中最喜庆的时候就到了,有了这些金灿灿的谷子,农民家中一年的吃穿用度全有了。
稻香转眼已成追忆。
2006年10月,奥运在望,京冀两地政府在北京签署了一份重要文件—《北京市人民政府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经济与社会发展合作备忘录》。备忘录提出,两地共同实施“稻改旱”工程。双方分两期合作实施密云、官厅水库上游承德、张家口地区18.3万亩水稻改种玉米等低耗水作物。
第二年,这项工作在长阁村也如火如荼地推进开来。“村民们不太乐意,但上面抓得很紧,到处都在讲为首都保水节水的重大意义。有人说自家地势低,地里有淤泥,能不能明年再改?上面不允许。”村民孟宪堂说,他是村里“稻改旱”最大的受害者。1983年,他花3万多元从天津买回来一台碾米机,后来慢慢发展成了一个小型大米加工厂,并藉此很快富了起来。
当年,很多媒体曾以赞美的口吻描述“稻改旱”是一项民心工程,它实现了双赢:农民退稻改旱后,每亩地可从下游获得450元补偿,收入较以前基本持平,种旱地的劳力投入大减。
但是,缓过神来的农民很快就发现自己“吃亏了”:最近几年,稻米价格节节看涨,稻改旱时每市斤仅1.2元左右,如今最便宜的大米也卖2.7元一斤,而玉米价格涨势不明显。从2008年开始,“稻改旱”的补助提高到550元,农民算来算去还是不合算。
孟宪堂拨拉着手指算了一笔账:如果稻米以亩产千斤计算,一亩地的收入在2700元左右,换成玉米,亩产千斤,收入不过是800元,再加上补助,农民“稻改旱”后每亩地净亏1350元。
如今,老孟只能在炕头上回忆往昔光景,以前,他家有10亩稻田;大米加工厂的收入每年有5万元,已经干涸的鱼塘改旱前每年也有几千元收入—这个昔日村里的“大户”现在光景一年不如一年。
村党支部书记李长国那里有一组数据,“稻改旱”之前,长阁村村民多年人均收入1200多元,现在只有700多元,再次从小康村掉落到贫困线以下。外出打工几乎成为村民摆脱贫困的唯一途径。
孟宪堂年纪大了,不能和青壮年一起外出打工。“稻改旱”后,他一直琢磨着做点什么好,他尝试着种过菜、养过猪,但这些“大路货”农副产品价格起起伏伏,销路存在问题。
“要脱困,得有好的项目。”孟宪堂心里也明白,但好项目投资大,邻村有搞油桃种植的,投资额近千万元,这些还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农民,哪里去寻这巨额投资?
各个政府部门也搞了一些项目,但僧多粥少。见到记者时,苏武庙村的高立新脸上有按捺不住的喜悦,他那饱受资金困扰、盖盖停停的鸡棚快要完工了,投入使用后,这个鸡棚每年会带给他2万元左右的收益。
这个项目对高立新来说,可谓来之不易。由于项目能够获得部分信贷支持,申请的人特别多。“我们村一共建3个鸡棚,有20多户人家报名竞争。”高立新说。符合要求的毕竟是极少数—选址要求距潮河500米以上,报名者要交纳3万元押金。
距孟宪堂家不远处,潮河水哗哗流淌着,这是这几年才出现的新现象。“稻改旱”之前,潮河水经常断流,每到插秧季节,上下游难免因争水发生矛盾。在别人眼里,孟宪堂一直是能人,但他有些想不明白:为什么生态环境改善了,日子却越过越难了?
丰宁县水务局工作人员介绍说,该县“稻改旱”涉及9个乡镇67个行政村的3.6万亩耕地,按水稻亩均消耗淡水1200立方米、玉米亩均消耗淡水400立方米测算,“稻改旱”下来,每年为下游节水2500万立方米。“稻改旱”生态效益明显,当地百姓也付出了代价,除水稻和玉米之间差价造成的收入减少外,当地的稻米种植加工农机具和过去为水稻生产建设的水利设施大量荒置,这些地方的农民出现了政策性返贫现象。
总理的嘱托
因发展受限而返贫的还不止“稻改旱”地区。
作为京、津的上风上水之地,潮河、滦河均发源于丰宁,这里是首都重要的生态屏障,被认为是内蒙古风沙南侵北京的重要通道。
2000年,北京媒体发表了一组图片—《被黄沙围困的村庄》,震惊了高层。时隔不久,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赴丰宁县小坝子乡榔头沟村考察。他在一片沙地上发表了“治沙止漠刻不容缓,建设绿色屏障势在必行”的指示。当年朱镕基现场发表讲话的地方已被建为教育基地,这有可能是榔头沟村如今唯一一片裸露的沙地。
时值深冬,凛冽的寒风从漠北吹来,在山谷间发出阵阵呜咽,但风是清洌的,空气中几乎没有混杂尘土,目力所及,山上长满了灌木,河滩、村庄均被林木所包裹。
榔头沟村人说,过去这里被称之为“沙窝子”,到处是沙地和乱石滩,山上的草和灌木也被随处放养的山羊啃食殆尽,这个季节正是黄沙肆虐的时候,狂风挟沙尘包裹了村庄,能见度仅有数米,家家户户闭门不出。
朱镕基视察过后,丰宁县开始大规模地退耕还林、封山禁牧。缺水,立地条件恶劣,栽种的树木不易存活,村民们栽了拔拔了栽,“哪一根存活下来的树不是种了五六遍?”10年下来,农民们艰辛的劳动换来了丰宁全县森林覆盖率从27.4%提高到2010年的43.7%,但也失去了35.5万亩耕地。
当地还以雷霆手段推进封山禁牧,县里往各处派出了巡查组,规定3次被检查发现有山羊进山的,乡镇长就地免职。一时间,地方官们压力很大,一些人常年蹲守在野外。在封山禁牧以前,小坝子乡有7万多只山羊,现在山羊、绵羊合计不足1万只。
眼瞅着环境一天天好起来,这里的农民却越来越为生计犯愁。榔头沟村的周庆荣当年曾和朱镕基合影,11年前的光景还历历在目。说起往事和家事,周庆荣的泪噗噗掉下来。
“当年,总理见了我,拉家常一样问我,‘你家种了多少地?养了多少只羊?我告诉他10亩地、30只羊,总理又问,‘能不能不种了,国家给你粮食补?我说能,总理脸上有了笑容……”这些陈年往事,周庆荣不知对人说过几百遍,再次谈及时已没了当初的兴奋,她眼光暗淡,像在背台词。
这和她的经历不无关系。当年她听从总理的话,卖掉了30只山羊,家里的10亩地退掉了6亩,而国家给的补贴却从当初的每年每亩160元降到90元,仅够买1袋面粉,她那些林地树木长不大,也不能砍伐。“那时候多留点地种棒子多好。”
10年下来,周庆荣的家境一日不如一日,如今,仍住在10多年前低矮破旧的房子里,大儿子33岁了,因为家贫,还没讨着媳妇。日子越过越难,每次路过村委会,瞥见墙上挂着总理和她的合影,想起总理保护好生态的嘱托,她就心头无比沉重。
“这不是哪一家的问题。”一些村民自我安慰。小坝子乡这个昔日的穷窝子贫穷依旧,2000年全乡年人均收入900元,2010年则仅有680元。乡里的一位干部说,过去实施的一些项目主要是生态公益专项,与当地群众的生活联系不紧密,要脱贫还需要一些好项目带动,但本地财力有限,无力支持更多项目。
期望越高,失望越深。对于各路而来的记者,村民们毫不掩饰他们的厌倦:“说有啥用啊?报纸上不知道说过多少回了,啥变化也没有。” 只记得领导要求把这里建成北京的后花园。
接二连三的报道也让基层官员们神经紧张,“我有一个请求,你能不能多写写领导对我们很重视?不要老是说我们的百姓过得有多苦。”另一位乡干部对前去采访的记者说。
来自小坝子乡的最新消息是,这个乡最近已被河北省纳入重点扶贫开发计划。
那些虎头蛇尾的治理
环境向好,生活变差,一个现实的悖论正困扰着京北那些农牧交错带的原住民。
“把清水和氧气输送给北京,把沙子留给自己。”这是在河北张、承地区流传已久的口号。多年来,河北省以北京护城河角色出现,一直在“两环”、“基地”、“腹地”、“后花园”等概念之间徘徊。植树造林、关停工厂,当地人主动牺牲了诸多自我发展的机会。
以丰宁县为例,为了给北京保水治污,该县相继关闭了明胶厂、化工厂、电渡厂等一大批厂矿企业。“丰宁是个国家级贫困县,财政本来就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在京津风沙源治理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你总不能让我们像计划年代那样发动农民投工投劳来做生态保护吧? 如果老百姓活得没有尊严,他不会去考虑环境。”当地一位干部说。
靠行政命令推行的生态保护措施能坚持多久?这一问号在今天正在演变成惊叹号。事实上,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反弹迹象。最近几年,山羊又开始出现在很多当地人的羊圈里,封山禁牧与偷牧者一直在玩猫鼠游戏。在坝上和接坝深山区的农民多年来一直沿袭放养牲畜的生活方式,禁牧又不增加其它经济收入渠道,这样做的效果可想而知。
“这中间其实是没有一种生态补偿的长效机制问题。像稻改旱后农民重新返贫,中间缺乏相应的价格变动机制。”环保部环境规划院生态环境部主任张惠远说。
张惠远介绍,北京和上游地区的生态补偿话题由来已久,但近年来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基本上是北京一家独大,遇有重大活动或感受到本地环境受到危害时,才会与上游坐谈补偿的问题。
缺乏政策的连续性,使得上游一些群众治理水土的积极性正在耗尽。因为没有连续性,这些治理往往异化成一场场运动。丰宁县水务局水保股股长孙志勇随口便列举出这些年来一场场半途而废的治理:
从1989年开始的滦、潮河上游水土保持重点防治项目,只实施了3~5年便中断投资;全国生态示范县建设项目规划长期50年、中期20年、近期10年,只实施了两年便中途夭折;《21世纪首都水资源规划》有17个水保项目,设计治理水土面积1400多平方公里,规划实施期为2001~2005年,仅实施了4个项目就已搁浅……
“当时,这个项目搞了两年,就请一家咨询公司来评估,评估结果是‘没有效果,就中止了。这也太儿戏了吧?都说10年树木,两年你就能看出多大效果?”孙志勇说,这些虎头蛇尾的项目已经影响到基层群众治理水土流失的信心。
张惠远认为,建立生态补偿的长效机制,使上下游之间从生态依存向互利共赢转变,使生态脆弱区农民脱贫才是根本性的办法。
“一个行政区划内可能好解决,跨省补偿太难,需要国家层面来协调制定相关政策,有了政策执行也很难。”这位《生态补偿条例》专家组成员用一连串“难”来形容目前的胶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