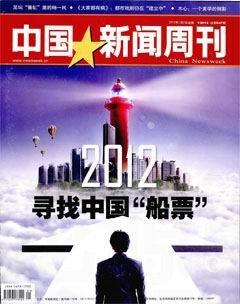大家都努力来打扫
2012年,不会是世界末日,但是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俄罗斯和美国的大选,朝鲜面临关键的一年,叙利亚局势的动荡,伊朗和西方的冲突……经济上,欧元区债务危机还将持续,中国有可能出现地方债务违约……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备感压力的时代。
今天这个时代的压力,回过头看,有点像上世纪80年代,那时没有网络,没有现在的信息量,那时如果哪家杂志发表了一篇尖锐的文章,就会很受人尊重。不过,那时讨论的许多问题,当时觉得很勇敢,今天看起来也不算什么。
与80年代相比,如今对一个公共事件的讨论,已不再是少数人的事情。是全民话题,只是知识分子发出自己的声音,影响力稍微大一些而已。但也并不绝对。比如最近的“乌坎事件”,如果有一个记者能够进去,会比所有人都要强大。
然而1980年代是思想解放的十年,中国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也基本团结一致,虽然在理念上有些分歧,中间也出现一些波折,有一些中青年知识分子为了自己的利益卖身投靠,但都只是少数。
80年代,也是艰难的时代。“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翻来覆去,每当终于有篇小说要在重要的文学杂志上发表,杂志会突然因为“清污”或者“反资”撤稿,这种打击对于一个还没有名气的作者是致命的。
压力不只来自政治,还有艺术观念。当时的先锋文学出现之前,经历了文革,中国的文学形式都退化得过于简单,很多作家像写作文一样在写小说,我们这一代希望追求更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当这种需求表现出来时,一些中老年作家和批评家,还有一些掌握文学权力的人,都持拒绝态度。王蒙是我们的支持者,但他是少数。这不只出现在文学领域。崔健的摇滚,刚出来的时候也不允许,只能地下演出;也出现了很多非主流的电影,比如张艺谋有三部电影都被禁,包括《活着》。
但这种压力的后果是,80年代产生了一批文学艺术新人,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活也丰富多彩。压力之下,会爆发出一群新人。
90年代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平稳的时期,经济飞速发展,但也带来了负作用,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社会矛盾等等,只不过这些在当时都没有充分体现。平稳的表面使90年代的人会突然发现没有政治了,一切都“经济”了。,
经过整个90年代经济发展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好像分化成了两类,一类是受到重用的,比如有些成了官员;一类则被排除在利益之外。前一类大多是精英的表情和语气,自我感觉很好;后一类脾气不好,牢骚比较多。当然,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始终保持了独立性和批判性。
回到今天,现在的名人基本还成名于上个世纪。新出现的文学先锋则很难判断。郭敬明,完全走商业路线,而韩寒的杂文则完全是写给中国人读的,应对压力的晦涩,外国人可能完全看不懂。但这样的压力如果持续下去,我相信,十年之后,中国的文学会出现另一拨重要的作家——他们应该都是90后。
当然,这也涉及到中国的文化体制。
中国的文化体制是三十多年来中国变化最少的领域,这种文化体制是畸形的。中国的经济体制也是这样。金融危机之后,房价都在跌,只有中国在涨,最后要靠政府出台限购令这种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强制手段来控制。我们国家的整个发展,仍然缺少一种自我调节、自我修复的功能。
举个简单的例子,今年我去美国,问我的编辑,美国一年出多少种书,他说两万种。我吓了一跳。以前中国每年出12万种书的时候,他们大概出10万种。中国现在每年要出30多万种书,但他们只有2万。由于金融危机,大量书店倒闭,出版社也以缩小规模来渡过危机,但中国不管是不是处于危机时期,都会大规模出版。
但另一方面,一种书只要在中国卖到两万册就算畅销书,可是哈金告诉我,他在兰登书屋出版的一本书,卖了7万多册,仍然不算畅销。全美一年只出两万种书,其中30%是文学类的,卖到两万册非常容易。而中国出版的书太多,最后就相互抵消了。
一个成熟而能自我修复的社会机制,最终还要建立在全社会的公信力上。
我个人对中国的文学奖项完全不关心。因为中国的评选从机制上就不能够保证公正。比如,美国的普利策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终审评委只有三个人,但他们一辈子只能当一次这个奖项的评委,每年都要换人,就是为了保证评选的公正性。而作家也只要关心作品就好了,不必关心出版后是否受欢迎,也不用关心是否能获奖。
这样的公信反映在方方面面。
2003年去美国出版《活着》时,我的出版编辑特地嘱咐我,不要接受《纽约时报》国际部的采访。事后我才知道,因为这位编辑的先生就在这个部门任职,她担心如果我接受了采访,反腐败部门会怀疑她利用丈夫的职位来推广这本书。
那年美国新闻出版界还发生了一件大事,是《纽约时报》的记者抄袭事件。这件事后来导致主编副主编全部辞职——如果失信,这就是代价。
前些天我到纽约,《纽约时报》评论版的编辑一我常给他写稿——告诉我,我的新书《十个词汇里的中国》英文版出版后,美国的Ⅸ新共和》杂志曾想约他写书评,但得知他和我本人很熟悉后,就放弃了。理由是,他们需要独立的书评。
这样做的结果是,双方之间建立了长期的信任。《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这些全国性大报,一篇书评可以带动几千册的销售量,媒体为了对得起读者的信任,就必须做负责任的推介,而读者反过来也信任媒体的推荐。但在中国,书评不可能对书的销售起到实质影响。报纸上的书评大多不是和友谊有关,就是和金钱有关,很多销售排行榜也是假的,是可以花钱买的。
我们应该努力建立一个公信的社会,但信誉是需要长期培养的。所以,不应该单一地责备中国的文学界,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在一个肮脏的环境里,无法做干净的事情,或者说大家都在弄脏这个环境,只有几个人试图打扫干净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惟一能做的,是大家都努力来打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