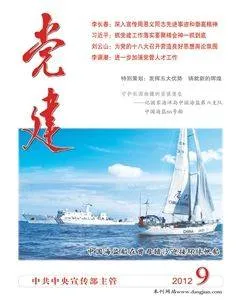美国中东战略:一厢情愿的选择
“9•11事件”后,美国中东战略日趋转向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霸权战略,最典型的体现就是发动两场反恐战争和进行“中东民主改造”。
美国本想更牢固地掌握中东地区主导权,却使该地区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并导致了美国最大死敌——伊朗作为地区霸权国的崛起。
事实表明,美国策动的民主改革仅仅是搅动起中东地区长久积郁的内部矛盾,使中东未来走向更加不确定。
奥巴马政府纵然有心全力收缩,缓解与伊斯兰世界关系,但其“中东新政”调整有限。这种因路线错误导致的“外交后遗症”,不是奥巴马短期的“灵巧外交”所能挽救的。
目前,叙利亚政府军和反对派武装战事处于胶着状态,美国正在主导制订“禁飞区”行动方案,以期待实现大中东战略。其实,过去相当长时期,美国在中东一直奉行现实主义政策。“9•11事件”后,美国中东战略日趋转向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霸权战略,最典型的体现就是发动两场反恐战争和进行“中东民主改造”。但十年过后,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和控制力非但未持续上升,反而日渐衰减,最终不得不重新进行战略调整。这种战略调整能否达到预期目的仍很难料定。
战略嬗变:从维持现状到颠覆秩序
以“9•11”事件为分水岭,美国中东战略可分为清晰可辨的两大发展阶段:自二战结束到“9•11”事件发生前的近60年内,美国基本奉行的是维持现状的均势战略;“9•11”事件后,美国转而奉行全面改造的霸权战略,这实际也是从经典现实主义向进攻性理想主义的转型。
1.维持现状的均势战略:“9•11”之前的美国中东战略。在中东,美国长期奉行的是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实用政策。石油供应和防范苏联是两大核心内容,而石油利益又是美国在该地区最具体的利益。美国在中东的总体战略就是促进和维护该地区稳定:
首先,在国家层面,采取“代理人政策”,避免干涉中东内部事务。1945年2月,沙特国王与罗斯福达成“石油换安全”的历史性交易。从此,沙特提供石油,美国提供安全就成为美国与沙特,乃至美国与海湾国家合作的基本模式。因此,尽管这些国家在人权、民主方面不尽如人意,但美国基本都是睁一眼闭一眼。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因深陷越战泥潭,因此在中东更加依赖扶植“代理人”来确保美国对中东的控制。总体来说,美国对中东事务的介入相当有限,所用手段也谨慎而节制(尤其是忌讳使用武力),这就使美国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战略自主性。其次,在地区层面,推行相互制衡的均势政策,防止出现威胁美国霸权的地区性大国。美国的中东政策主要由阿以政策和海湾政策两大部分构成。在阿以乃至大中东范围内,美国通过扶植以色列、土耳其等非阿拉伯国家来抑制阿拉伯民族主义;在海湾地区,美国通过支持沙特、科威特等温和阿拉伯国家来平衡伊拉克等激进阿拉伯国家,同时又通过伊拉克来制衡伊朗。
在阿以关系问题上,美国不遗余力地支持以色列,正是因为以色列能够成为美国平衡阿拉伯力量的战略筹码。美国的海湾政策同样如此。海湾地区作为世界上石油贮量最丰富的地区,伊朗和伊拉克均有可能称霸海湾,因此美国基于利益考虑,在海湾地区的基本政策就是防止任何一方过于强大,避免海湾油田被任何一国控制。因此,当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爆发后,美国在伊拉克节节胜利时,美国就暗中支持伊朗,而当伊朗转守为攻后,美国又开始偏袒伊拉克。总体看,美国的目的就是要使两伊两败俱伤。1990年,当萨达姆入侵科威特,并可能称霸海湾时,美国对伊拉克的态度骤然转变。美国在1991年发动海湾战争的基本目的就是恢复地区均势,防止中东石油为少数国家控制,这就决定了它是一场点到为止的有限战争。
总的来看,这种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中东战略,较为有效地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并保持了战略灵活性,应该说得大于失。
2.颠覆秩序的霸权战略:“9•11”后的美国中东新战略。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国家实力的膨胀使美国再次滋生出全面称霸的帝国野心。在很长时期内,美国对怎样塑造世界和中东一直举棋不定。而“9•11事件”的爆发使美国最终将恐怖主义锁定为最大威胁,将中东作为反恐主战场。在美国看来,要想根除恐怖主义,就必须对中东进行全面改造。
首先,通过发动战争建立亲美政权,进而实现地区霸权。苏联解体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极大地刺激了美国控制中亚、南亚和西南亚的地缘政治兴趣。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五角大楼就开始准备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也就是“9•11事件”发生多半年前,就表示要改变巴格达政权。伊拉克战争就是美国在实力膨胀后武力称霸世界的战例。
其次,推行民主改造,将影响范围从外交延伸到内政领域。小布什政府的外交哲学深受新保守主义熏陶。在他看来,其他国家所能做的就是效仿美国模式,而美国也负有某种“天定命运”去救助和推动落后国家向这一方向前进,在必要时甚至可以采取干涉和高压的方式输出民主理想。“9•11事件”发生后,小布什提出“新十字军东征”口号,要用美国价值观来“改造”伊斯兰世界,因此,美国必须采取“一种新政策,一个推动中东自由的战略”。他这种“新政策”的最明显体现就是美国在2004年2月推出全面改造中东的“大中东计划”。
陷入困境:美国中东战略的转型
美国中东战略转型并未给其带来相应战略收益,反而日趋被中东问题所困,这与美国新时期霸权战略本身存在的缺陷直接相关。
1.黩武主义本身存在缺陷。二战结束后,美国先后在朝鲜和越南发动两场局部战争,结果都是被战争所困。因此里根时期的国防部长温伯格与其助手鲍威尔主张如果不是与美国的重大利益有关,美国不应该随便动用武力。但小布什政府对前辈的这些告诫不屑一顾,而决意通过“反恐战争”来实现霸权目的,并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先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了两场战争。阿富汗战争使美国的霸权触角首次延伸到中亚这一权力真空地带,并在俄罗斯、中国与伊朗三个潜在或现实对手之间打入楔子;伊拉克战争则使美国首次在阿拉伯世界心脏地带获得战略立足点,并使美国有可能通过控制伊拉克和中东石油,达到控制其他大国的目的。
但这种战略收益极其有限,离美国的政策目标相距太远。首先,发动战争使美国深陷战争泥潭。美国本想通过发动伊拉克战争根除恐怖,在伊拉克建立民主政权,但反恐战争使伊拉克陷入前所未有的动荡,美国在伊拉克陷入了“输不起、打不赢、走不了”的战略窘境。同时,美国推动的“民主化”使伊拉克各派分离意识不断增强,这使美国塑造的“中东民主样板”面临全面失范危险。其次,战争破坏了中东脆弱的力量平衡,导致了美国最大死敌——伊朗作为地区霸权国的崛起。
长期以来,伊拉克一直是制约伊朗崛起的最主要因素。对美国来说,两伊关系的长期敌对,使美国长期坐收渔翁之利,以低廉成本维护着海湾利益。但小布什的反恐战争就像公牛闯进瓷器店,把中东本就脆弱的地区平衡完全搞砸了:一方面,两场反恐战争为伊朗崛起提供了重要机遇。阿富汗战争帮助伊朗铲除了塔利班政权,伊拉克战争又帮伊朗剪除了萨达姆政权。在不存在地区力量制衡的条件下,伊朗自动成为影响中东地区命运的决定性力量。另一方面,美国“先发制人”的军事战略,使伊朗生存危机感陡增,并由此激发了伊朗尽早崛起的危机意识。伊朗决策者认为,伊朗作为美国眼中的“邪恶轴心”和“暴政前哨”,随时可能成为下一个打击对象,对美国服软不会有什么好处,这也是伊朗近些年在核政策上日益强硬的根本原因。目前,伊朗通过推行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正迅速填补因缺乏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地区核心国家留下的空白,并由此直接威胁美国在中东的霸权地位。这与美国一再强调的“防止地区霸权国家崛起”的中东政策目标背道而驰。“对伊朗怎么办”已成困扰美国的头号难题。
2.“民主改造战略”存在重大缺陷。美国要对深受伊斯兰传统思想熏陶的中东进行全面改造,某种程度确有“改造伊斯兰文明”的嫌疑,这种外交思路不仅缺乏“政治正确性”,而且完全不切实际。
中东地区矛盾错综复杂,其社会发展程度与美国所期待的自由民主标准相去甚远。以伊拉克为例,它是1920年由英国把奥斯曼帝国中的巴格达、巴士拉、摩苏尔三省合并而成,这三部分始终没有完整地整合到一起。萨达姆之所以能在该国长期统治,是因为“他们具有在地区所有三个政治传统(部族政治、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中来回活动的出色能力。他们一直在和这个世界下三维象棋,而美国人似乎只知道如何走跳棋——每次只有缓慢的一步。”
事实表明,美国策动的民主改革仅仅是搅动起该地区长久积郁的内部矛盾,使中东未来走向更加不确定。近两年来,美国尽管为推行“大中东计划”不惜巨额投入,但“民主改造”结果,一方面是损害了与中东传统盟友沙特、埃及等国的关系,使这些国家离心倾向增加;另一方面是使伊斯兰极端势力借机崛起(巴勒斯坦、伊拉克、埃及、伊朗等均出现类似问题),尤其是2006年1月激进组织哈马斯的上台,令美国极为被动。而且,哈马斯还与伊朗、叙利亚等反美势力出现了相互联手的迹象,从而对美国的中东利益构成直接威胁。
从长远看,由于伊斯兰势力是中东唯一有影响力的反对派,而且中东地区反美主义情绪高涨,因此,政治改革要么可能出现“伊斯兰民主化”,要么使酝酿于“草根阶层”的反美情绪上升为现实政治力量,出现“反美的民主化”,无论哪种结果都有悖美国的国家利益。播下龙种,却收获跳蚤。由此使美国“民主改造”陷入欲罢不能但又难以维系的困境。
战略收缩:美国中东战略的再调整
美国霸权周期历来是“强大—扩张—衰落—收缩”。自二战以来,美国对外政策共经历了两次大的收缩:一次在20世纪70年代的尼克松时期。冷战结束后,美国凭借一超地位,在中东全面扩张,结果无疑导致国力透支,深陷战争泥潭,加之国内金融危机加剧,既定政策难以为继,被迫开始新一轮战略收缩。这种收缩从布什后期就已开始。
而2009年上台的奥巴马进一步加快了这种战略收缩步伐。奥巴马继承的中东外交遗产,与当初克林顿从老布什继承下来的完全不同,中东现实要求其对地区秩序进行重组。在美国实力不济、四面受困的背景下,奥巴马明确放弃小布什时期“文明冲突”的话语体系,尽可能缓解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依靠“巧实力”维护自身利益。奥巴马上任后,大幅推行“中东新政”:与反美国家接触,如对伊朗发出和谈信号、对叙利亚选派新大使等;加大扶植亲美国家,用地区盟友和相互制衡来取代美国直接统治;降低反恐调门,关闭关塔那摩监狱,尽快从伊拉克撤军,将反恐战场转移到巴阿地区。其“中东新政”的核心目标就是缓解伊斯兰世界反美情绪和“东向”倾向。
奥巴马意图通过战略收缩化被动为主动,重新掌握中东主导权。但奥巴马很难超越中东已有的现实:从传统安全看,中东的战略重要性决定了美国不会真正退出。美国不可能承受“失去中东”代价,尤其不可能容忍敌对的伊朗填补权力空白。从非传统安全看,中东活跃的恐怖活动决定了美国无法轻易离开。目前,伊拉克已成为恐怖主义的策源地;阿富汗塔利班也已卷土重来;2011年中东剧变更使“基地”等极端恐怖组织得以恢复、壮大力量。恐怖主义不绝,美国就不可能从中东从容脱身。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政府纵然有心全力收缩,缓解与伊斯兰世界关系,但其“中东新政”调整有限。有学者认为,奥巴马中东政策与布什并无本质不同,而只是前者的副本,这种政策必然失败。这种因路线错误导致的“外交后遗症”,不是奥巴马短期的“灵巧外交”所能挽救的。(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冯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