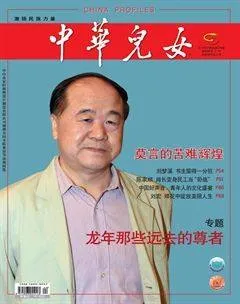张松林 动画事业是他活着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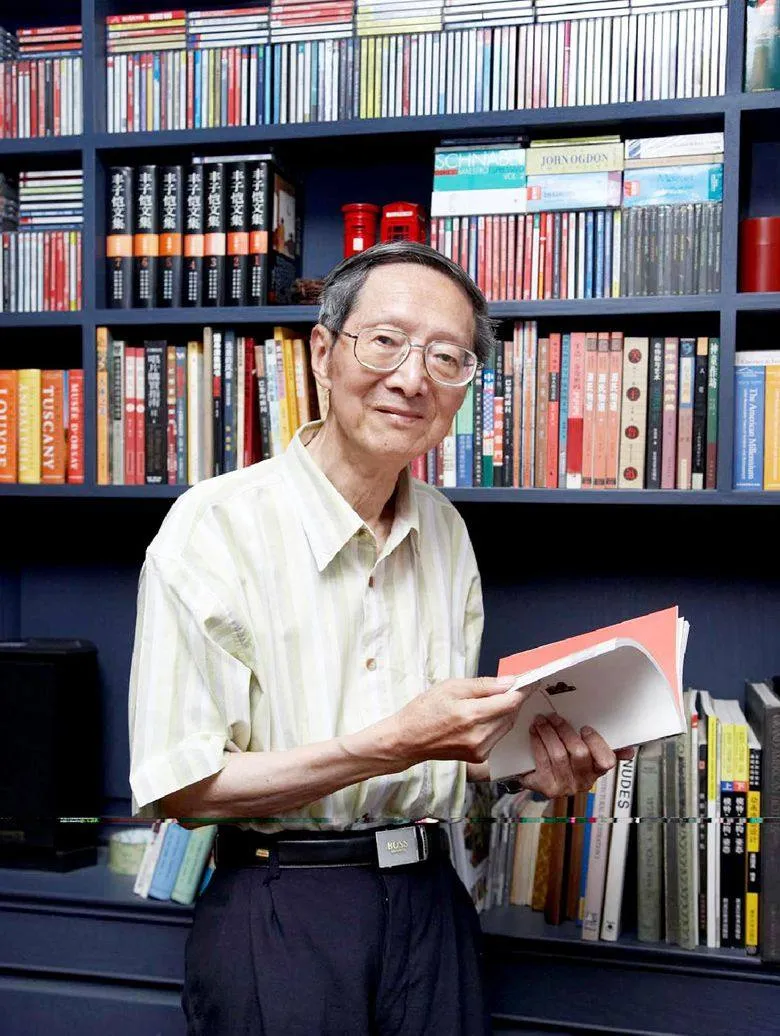
动画是人类进入现代文明以来共同的童年记忆。
2012年5月8日,80岁的张松林先生与世长辞。一时间,《没头脑和不高兴》这部50年前的老动画又在网络上流传起来,有网友回顾说,张松林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动画导演的杰出代表,大师走了,如今中国的动画市场上充斥着大量“没头脑”的作品,观众的确高兴不起来。
面对中国动画的曾经辉煌,面对21世纪日本、欧美动画铺天盖地的涌入之势,老人有更多想说想做的事儿。
寄望中国动画的新生
张松林大女儿张红告诉记者,父亲去世前一直在忙工作,病发突然,连遗愿都未能留下,“逝世前的周五,他改一个档案库的稿子,是一个把一些老艺术家生平经历整理归档的‘抢救老艺术家’活动。忙完稿子后,他可能真的太累了,周六晚上身体出现突发状况,住进了医院。病重期间,父亲时而清醒时而昏迷,清醒的时候,他和我嘴型对话,我问他是不是说‘很多事没做完’,他说‘是’。他一直都惦记着他的动画事业,我们特别伤心,没有让他如愿完成想做的事”。张红介绍,张松林想做的事情特别多,“从中国动画的低谷,到现在逐渐兴旺,他很希望能看到成果。平时,他特别关注中国动画方面的信息,不管是杂志还是报纸上出现什么相关信息,他都特别留意,还会经常上网,寻求行业新动态”。
张红回忆,晚年的张松林肺部有问题,走路都特别辛苦,生命最后的一两个月基本只能走上十来二十步的路程,体力明显不济,内心却很不甘心,就是想做事情,“退休后经常会有一些晚辈来找他,他都特别认真指导,从来不会拒绝。只有我们这些家人知道,他体质比较弱,这样操心对他来说是挺困难的。我们也常劝他不要做那么多事,他就说:‘什么都不让我做,不等于死了吗?’我们也能理解他,中国动画是他真爱的事业,是他活着的意义”。
尽管中国现在的动画公司已经遍地开花,老人对中国动画的现状仍有两大担忧,一是人才,二是质量。
2006年,张松林在谈到中国动画的现状时,曾经语重心长地说过:“我们动画片的剧本数量和质量都存在问题,一集20分钟的动画片都要1万多字的剧本,但稿酬就三四千元,比写电视剧剧本的收入差太多了,所以很多儿童作家都去接电视剧剧本了。可以说,我们就没有一支专业的做原创动画片的队伍。以前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还有几个,但是新人上不来,业余编剧也没有形成队伍。”
2007年,他又流露出对“国外动画冲击”的担忧,他说:“如今很多国内动画界人士已经认识到,动画片不仅仅是拍给孩子看的,成人也应该成为目标群体。只不过要成为一种普遍共识还需要一个过程。成人动画的要求更高,电影界当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前几年,北京电影学院也专门为动画开过编导班,只不过,办班也未必能马上培养出好编剧来。”
这两点,也是他自己毕生的追求。
中国第一代动画精英
张松林1932年生于上海金山县。他自幼喜欢美术,尤其痴迷动画。18岁时他毅然从“苏州美专”辍学,开始从事动画电影工作,从此踏入了美术电影的大门,开始了新的艺术旅程。此后十多年的努力让他终于有了导演的能力。他导演的《蜜蜂与蚯蚓》在主题上的探索和《小燕子》在中国彩墨花鸟画与动画片结合的探索都不曾让他止步,他始终在思考主题与形式更加完美的结合方式。
60年代初,我国的美术电影正处于繁荣发展的时期,需要培养更多的动画人才,在特伟先生的点将下,张松林调至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担任动画系副主任兼专业教师,这是一所新办的电影学校,一切都需要从头开始。他负责动画教研组工作,从编写教材,安排课程,以及毕业设计等各项教学工作中,他和其他同志一起,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三年里,手把手地培养了四十多名动画专业人员。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张松林用创作练兵的大胆构想。《宝莲灯》的导演常光希先生说:“张老最令学生佩服的就是从不墨守成规的理念。《没头脑和不高兴》是1962年上海电影专科学校动画专业班的毕业之作,全班同学每人分画5至10个镜头,形象设计由阿达等人完成,邱岳峰的旁白配音、张栋的京味配乐等也都可圈可点。“可以说,这部幽默夸张的20分钟动画集合了当时圈内最顶尖的编剧、导演、美术设计、配音、配乐等,集中体现了动画创作的团队精神。”常光希说。“我当时是学校的动画系学生,张老师是系副主任。我们两年大专的最后一个学期,整个团队就像宫崎骏的吉卜力工作室一样形成了合力,那样的氛围让每个人都能与导演沟通,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的流水线方式。就这样经过几十部作品的磨炼,我们这批人逐渐成为动画导演,《没头脑和不高兴》就是我们共同的起点”。
在中国一代动画人的努力下,山水画进入动画片成为了现实,以齐白石先生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英们纷纷投入动画片的制作,《大闹天宫》、《山水情》这样别致的作品开始为中国赢得国际声誉……
峰回路转所忧仍是人才
十年浩劫期间,正直有为的艺术家无一幸免地遭受打击,张松林也不例外。但他的内心十分平和,利用业余时间自制放大机在家里放大照片。几年间他白天学文件,晚上让孩子们轮流给他当助手,在家里为孩子们放大量优美的照片。他还为孩子们设计了很多图形,把孩子们的头像放在花朵中、球拍里,给孩子们枯燥的生活中增添一番情趣。
文革的经历也引起了张松林的深思。光有好的团队还不足以成就百年事业,中国动画必须有一个开放的社会和思想环境。他振奋精神,参加了美术片的恢复和整顿工作,1978年开始,担任副厂长兼编辑室主任,又对各种社会职务来者不拒。他历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上海分会的常务理事、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客座教授、北京广播学院名誉教授、北京电视台艺术总监、中央电视台火炬动画公司顾问、中国动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上海木偶艺术学会副会长。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还以浓厚的兴趣钻研美术电影的理论问题。1978年以来,他先后发表了《美术电影要走民族化道路》《美术电影创作初探》《漫谈美术电影剧本的特点》《美术电影艺术规律的探索》等论文十余篇。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影卷》《当代中国·电影卷》《电影艺术词典》《中国电影大辞典》的撰稿和编辑工作。在改革开放后,很多同行被外国高薪聘走之际,他投入了对中国动画发展更深入的思考当中。
文革刚一结束,他要求新入行的同事定期把全国各地的出版社、杂志上发表的可供拍摄美术片的选题报上去,并深入各地与业余作者广泛联系,还要求每个稿件必有回复,并要写上意见。在他的倡导组织下,上美厂文学组召集过多期业余作者学习班,让作者带着自己的作品集中学习,进行修改。在这样忘我的付出下和直接指导下,上世纪80年代,《哪吒闹海》《三个和尚》、《黑猫警长》、《鹬蚌相争》、《阿凡提》等一批佳作出现了。
就在这中国动画承上启下发展的关键时刻,电影领域直面市场的体制改革开始影响到动画制作。对于投资大、风险高又几乎没有任何市场运营经验的中国动画产业而言,一个长达10年的阵痛期出现了。原有人才的流失,后备人才的不足使整个行业都出现了危机。
为从源头增加人才储备,2000年,张松林力推中国第一所专业动画高校的成立并任校长。
在低迷时成立学会
为寻求突破,90年代初期,正是我国动画发展的低迷时期,张松林又和上美厂里的一批老艺术家发起成立了“中国动画学会”,为中国动画的再创辉煌而上下奔波,四处呐喊。在他的亲自组织和起草下,中国动画学会多次给政府有关部门呈送了关于中国动画事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并收集了大量日韩及欧美各国发展动漫的相关扶持政策,给政府部门决策时参考借鉴。
在当年国家广电总局为举办首届中国国际动漫节的申办活动前后,张松林更是做了不少工作。之前他曾代表学会给总局领导打报告提出申办中国动画博览会的设想。当得到领导关于由总局牵头举办国际动漫节的批复后,张松林顾全大局地又投入该活动中。作为申办城市的标书评委,他考虑到杭州的天时地利人和等有利条件,果断地投下了手中的一票。之后又力促动漫节的成功举办,不仅亲自过问筹备方案,力邀国际动画组织及各国动画艺术家的关注和出席,还大胆提出把学会曾和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联手举办的优秀动画展播“美猴奖”的评选和颁奖活动与中国国际动漫节携手共办,这一设想最终得以实现,并达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在国家对动画发展的政策支持下,各地动画风起云涌。张松林深知要创作优秀动画作品的艰辛,古稀之年的他为了我国的动画产业和教育的发展,也为了诸多中小动画公司、动画院系的成长竭尽全力,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每每见到他,总是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脸上洋溢着孩童般的笑容。谈起一些地方的动画发展,时而神采飞扬,时而沉着忧虑......
现任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厂长钱建平对张松林最突出的一个印象,就是张松林在肺部长期有病的晚年,仍对中国动画片的现实状况有清楚的了解和思路。
对新生事物永不疲倦的追逐者
在日常生活中,张松林对新事物特别敏感,观念前卫。他常常说,作为搞动画的人,一定不能让自己的思维停滞不前。他一生从事的是传统动画创作,然而他却对新生事物倍加关注。早在上世纪90年代,当多数动画人还不知电脑动画为何物时,张松林却抱着积极的姿态打开学会大门,让这一技术在1996年的年会上有了一席之地,堂而皇之地做了介绍和推广,以自己的行动对新技术给予了支持。
早在iPad风行之前,张松林就已经在娴熟地使用某品牌国产电子书学习,并不断地向周边的同事好友推荐。将近古稀之年,为了方便工作,他自学电脑操作技能,由于打字不熟练,他就用手写板写作,手写板只要有更新换代产品,他总是第一时间就更新。张松林把常用的键盘应用整理成册,成为应用电脑的独特教材。每次在操作中遇到问题时,他从来不会问第二遍。在日常工作中,他都是用电子邮件与全国各地的朋友、媒体联系,在他同辈人眼中,张松林总是时尚的引领者。
正是他的这种敢为人先、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性格,使他一直保持着敏捷的思维和旺盛的精神。当人们对日本动画在中国的漫延而忧心时,张松林倒是对《灌篮高手》等作品欣赏有佳,他说日本动画的两大要素是故事和数量,中国动画或者需要用十年的时间来追赶。他又说,美国人对中国文化的改编,在《花木兰》《功夫熊猫》这样的电影里也是成功的,而对内容的追求与创新,也是中国动画明天的出路所在。
一代大师,真知灼见。
责任编辑 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