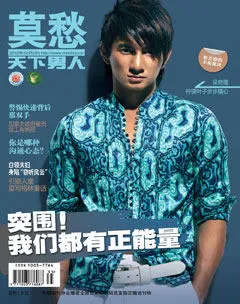加拿大政府雇员怠工有绝招
“满地可”成了“满地坑”
出国前,我从各方面了解到的信息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部门工作效率很高。移居加拿大后,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加拿大东部的蒙特利尔市,是该国第二大城市,曾经成功举办过奥运会。早年第一批广东华工到蒙特利尔时,给它起了个很好听的中国名字“满地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满地可演变成另一个绰号“满地坑”。如果你开车在蒙特利尔市内转上两天,就会感叹,这个新绰号名副其实:柏油马路上到处是裂缝,时间长了,就变成了一个个不深不浅的坑,稍不留神,一路颠簸下来,就得去修车行修平衡杆。
你也许要问,为什么不把马路修一下呢?可实际情况是,这里一年四季都在修路,马路上随处可见醒目的橙色修路禁行指示牌和路障,有些路障密密麻麻地排到距修路现场几百米之外。工程不可谓不大,修路工人不可谓不多,市政拨款年年创下新高,可路面仍然是坑坑洼洼。
对于外国游客来说,这是个谜,可常年生活在蒙特利尔的人就知道其中的奥妙了:因为修路工人基本不干活。他们每天高兴时会干一两个小时活,不高兴时,只干十几分钟活,却拿着每小时高达25加元的薪水。当地一家报纸经过长期暗访后做了如下报道:如果你想知道市政税为什么这么高,那你最好看看修路工人每天都在干什么。他们每天吃午餐用掉两个小时,他们看到坑洞而不去修补,工作时间却在睡觉、逛商店,甚至在街上悠闲地游荡,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把时间打发掉,然后搭乘工程车辆下班回家……
该报摄影记者专门冒着严寒跟踪市政养护队的三名撒盐工人,报道了他们一天的工作:三人一早乘撒盐车来到一家一元店,买了一些厨房用品后,到市博物馆前撒了10分钟盐,然后回到撒盐车养护库房。两个半小时后,撒盐车从养护库房出来,来到一家食品超市,三人又买了一大包食品,放到车上。最后,撒盐车把三人送到家门口,司机则开车回家,把车停在了路边,一天的工作就此结束。
类似这样的现象很普遍,每年被记者们实地拍摄到的就有数百例,可市政府对消极怠工人员的处罚却仅仅是扣除一天工资。
没有工作也要创造工作
与市政工人和环卫工人的懒惰相反,坐在政府办公室里的官员们却分外忙碌。有时,他们甚至为了有活干,而精心“创造”出一些工作。
我刚来加拿大时,就遇到过一件怪事。当时听华人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如果家庭年收入低于38000加元,可以申请每月80加元的住房补贴。我按照对方提供的地址找到了一栋不起眼的小楼,在一楼等候厅里取了个号,排了一小时队,终于轮到了我。走进办公室,一个满脸笑容的白人女官员请我坐下,和我攀谈起来。她问我身边的女儿几岁了,然后从盒子里抓了一把糖果递给我女儿,她还觉得“招待不周”,又起身从身后的柜子里拿出一大叠儿童画册,抱到我女儿面前。这一切都做完了,10分钟快过去了,她才开始问我:“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我说了此行的目的,她拿出一个大本子,详细地给我讲解了申请的条件和流程,然后说:“首先,你必须填一张表格。”我向她索要表格,她双手一摊,无奈地说:“想要获得表格,必须电话预约,接待预约工作另有他人负责。”
无奈,我只能回到家里,打了六次电话,才打通并预约成功,拿到了四张表格。我在等候厅里填完表格后,取了一个号,等了10分钟把表格交给了那名女官员。她看了一眼,抱歉地说:“我们只接受邮局寄来的表格。”我只好到附近的邮局,花87加分买了邮票和信封将表格寄了出去。
过了些日子,我和一位加拿大朋友谈起这事,并表达了对当地官员“没事找事”行为的不解,朋友笑着解释:“政府官员必须这样干,否则他们太闲的话,议会就会要求裁减经费。而每一次电话预约,官员们都有通话记录,每次来往通信,官员们也会当作工作量,在年终统一报给经费委员会。”至此,我才恍然大悟。
2011年,我买了新房搬完家后,再也没收到过当地政府的退税。过了几个月,我给税务局打电话询问,对方告诉我只有我丈夫才有权询问。我向对方解释我丈夫英语不好,打电话问不清。对方回答:“让你丈夫写一个授权书,授权给你,一个月后,你就有权询问了。”等了一个星期,对方寄来了授权书的表格。我让丈夫写好授权书,我俩签上名寄了出去。一个月后,我再打电话询问,对方问了很多问题,其中一个是:“你们家庭2010年的退税额是多少?”我一时找不到数据,对方说:“对不起,我们不能接受你的询问。”我气得大声喝问:“难道我无权得到我应得的退税?”对方态度非常好:“你有权得到退税,但你必须写信询问。”
我这回彻底服了,绕了两个月弯子,一些加拿大官员无非就是想让你多写信给他们,而每一封信,都将为他们创造工作量助一臂之力。
不急不忙的救火队
刚到加拿大时,我经常发现有消防车鸣着汽笛,呼啸着从街上驰过,本以为这里火灾特别多,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使我明白,这些消防车大多是在作秀。
搬家前,我们一家租住在公寓大楼里,这栋楼里百分之九十的住户都是华人。除夕那天夜里12点刚过,忽然楼内的火警铃声大作,电梯自动关停,大家顺着安全梯向楼下跑。到了楼下大厅里,大家一聊,并没发现哪里失火,于是猜测是谁家做年夜饭炒菜油烟太浓,厨房里的警铃报警了。
等了十几分钟,大家一致确认没事后,正准备各自回家睡觉,忽然楼外警笛声大作,原来,消防车到了——公寓里的报警系统与消防队连接,消防队会第一时间接到失火警报。但消防队大楼离这里仅1000多米,过了十几分钟才赶到,速度也太慢了!只见一个消防员睡眼惺忪地走进大厅,一见有人要往楼上走,他立即阻止。随后,又陆续进来几个消防员,在一楼转悠了一圈,再到楼外看了一圈,半个小时过去了,才宣布没事,让大家回家睡觉。我困得不行,进屋刚要睡下,楼下又响起了警笛声,开窗一看,又有三辆消防车赶来救火。我很奇怪,究竟是那辆离开的消防车没向消防总部报告,还是这三辆车明知没事,故意要开过来?无论怎样,这三辆消防车也增加了一次出警记录,为明年的市政财政拨款增加了一个砝码。
慢点就慢点,反正也没真着火。但是,真着火了,情况会怎样呢?说来也巧,我还真碰上过一回消防队救火的“壮举”。一天清晨5点多钟,我去公寓后面的山坡上散步,忽然瞧见不远处的一栋别墅里正冒出浓烟,一群人围在周围,急得乱跳。等了七八分钟,五辆消防车呼啸着赶来。我凑上前,想看一看加拿大消防员救火的英姿。只见车门慢慢打开,一群穿着棕色服装的消防员一个个慢慢地走下车,我发现他们个个大腹便便,丝毫不像中国消防员那样健壮的样子。他们在车前站了一会,望着别墅里冒出的浓烟,交流了几句后,其中两人返身上车,取下两只顶端带铁钩的长杆,接着,他们以散步般的速度,慢慢靠近别墅,等两个拿长杆的消防员把一楼和二楼的玻璃窗一块块敲碎后,消防车稍稍靠近了一些,伸出梯子,一群人又开始研究起来。这时,屋里的烟越来越浓,已经隐约看见火光了。消防员们似乎终于做出了决定,端起水枪,向屋里射去……
我因为有事先回了家,第二天再路过那里,那栋小楼已变成了黑乎乎的一片废墟。我想,如果消防队员动作快一点,完全可以保住这栋小楼。后来,我与一位加拿大朋友聊起这事,他露出不屑的神情说:“消防队的第一要务是保证消防员的安全。”我又说:“可是,那栋楼房本来可以保住的,现在却变成了废墟。”朋友说:“没关系,保险公司会赔偿给房主一大笔钱,足够他盖起新楼房了。”我愕然,难道因为房主会得到理赔,消防员就有权利纵容火势蔓延?
这些社会弊病,像蠕虫一样,慢慢地侵蚀着加拿大社会的机体。多年来,兴利除弊的呼声不绝于耳,各政党多次痛下决心,但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弊病反而越来越严重。想想也是,不能怪历届政府没有诚心改正,但谁能管得了这些人?你把怠工的人开除?相关行业工会会找你算账,下次大选,这个工会的几万张票都会投给竞争对手,真可谓进亦难退亦难。
编辑 陈陟 czmochou@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