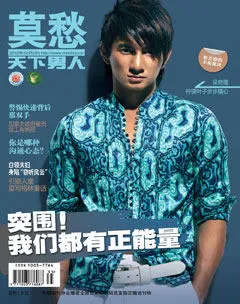“我”的四个面孔
我们都是千面人:公开场面上热情开朗,回到家里沉默寡言;面对上司毕恭毕敬,与同事周旋灵活机动;买东西锱铢必较……
大多数情况下,对付这些相互矛盾的自我,我们游刃有余。我们在这些不同的面具之间换来换去,甚至没有觉察,除非听到别人提醒:“你怎么这样?我简直认不出你来了。”别人这么一说,我们马上又会觉得自己的形象四分五裂,模糊不清。
心理学家认为,从童年开始,“自我”就是“我”同外部世界的交接点,它让我们随机应变,以适应所处的境地,回应别人的问话。但是,如何在适应外界的同时又不失去自我?心理治疗师简·特纳说:“如果我在说话或做事时感觉不自在,那就说明我背离了真实的自我。当一个人表现出真实的自我时,他会感到安全、清醒与和谐。”因此,在寻找真实自我的过程中,要特别关注内心隐秘的情感,倾听它的声音。
心理学学家克里斯多夫·安德烈认为,自我的面孔虽然千变万化,但大致可以分为四种主要类型。
窒息的“我”
思凡有过这样的经历:上大学时,有一次和朋友闲聊,请朋友说出他最大的缺点是什么,朋友说他是个非常虚伪的人,为人一点也不真诚。朋友的批评一下把思凡说懵了,因为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个随和而善良的人。
因为我们害怕冲突,压抑自己的攻击性,就产生了窒息的自我。简·特纳认为,害怕冲突源于我们对基本安全感的需要。“当心灵深处有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小声嘀咕时,我们害怕它会招来危险,就会立即把它压住。从远古人那儿遗传下来的记忆中,我们保留了‘反对别人会威胁生存’的观念。”所以我们以为,如果遇事同别人争辩,也许老板会开除,警察会罚款,小商小贩还会嘲笑我们。低调做人至少不会惹上大麻烦,但遗憾的是,这需要压抑内心深处的欲望、期盼和梦想。
若想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应该慢慢懂得,说服别人最好的办法是开口讲话,别人的粗暴反驳并不是什么致命的灾难。可以先从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开始这么做,然后遇到重大事件时也试着这么做。
变形的“我”
热恋中的丽莎像变了一个人,朋友们为此忧心忡忡:“我们都认不出她了。”这是典型的弗洛伊德笔下的变色龙女人,她认定自己的本来面目不值得别人爱,于是在无意识中改变了自己的人格,换成了一个自以为对方喜爱的样子。
变形的我通过别人的认同发挥作用。它没有独立的存在,只能依赖别人的眼光,自愿做别人的囚徒。它是如此强烈地渴望成为另一个人,为此不惜奉献自己的快乐和幸福!当矛盾的自我冲突不断时,就会产生焦虑、暴怒等情绪甚至生病,这些都是信号,表明我们在寻找自我的途中迷路了。
心理学家建议:我们应该学会区分“我本来是什么样”以及“我应该是什么样”,把内心深处真实的自我表现出来,这并不会妨碍你和他人的交往,反而会获得对方情感上的认同。
教条的“我”
谁要反对他,谁就要倒霉了:因为教条的我是强行装出来的,害怕差异和不同。他工作时说一不二,回到家像个暴君,对孩子充满威严,但在其他场合,却表现得相当令人愉快。这个看上去明晰、威严的我,实际上极度脆弱。在威武庄严的外表下,他生活在被别人摧毁的恐惧中。
马克在公司里总是温文尔雅。回到家,得知妻子想离开他时,一下子变得蛮横无礼,他对妻子大喊大叫,说要走尽管走好了,他就是这样,永远也改变不了。这些话的真正含义是,他害怕妻子的离去会把他摧毁。如果一个一向和蔼可亲的老板,暴怒之下把文件扔到某个下属的头上,他这么做,无非是害怕别人比自己优秀。
教条的自我在青少年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个阶段,人往往拒绝任何妥协,容不得反对意见。简·特纳解释说:“青少年没有别的办法确认自我,但是成年以后,我们知道自己是谁,这就意味着我们懂得该在什么时候说‘不’,什么时候说‘是’。成熟的标志就是学会保持平衡。”
自在的“我”
这是自我的成熟期。通过倾听自己的情绪和感觉,接触到最深层的自我,能够说出我究竟是谁。
心理学家认为,我们只有与自己达成统一,才能与自我的不同侧面和平共处。我们都知道,当我们处于不同的环境,面对不同的人时,会有不同的表现;但是在所说、所想、所做和所感之间,我们大致能够保持一条连贯的脉络。不管是行动上还是言语上,最要紧的是与真实自我的那个最坚硬的核心保持一致。也就是说,说话做事时,我们不应当违背自己最基本的价值观。更何况,只有了解自己最真实的需求,才能懂得别人的需求。这样一来,在尊重自我与尊重他人之间,我们就能达到平衡。(摘自《心理月刊》)
编辑 钟健 1249768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