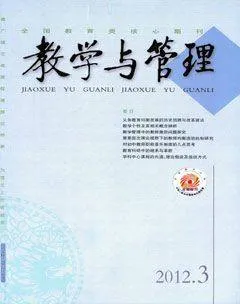孔子“仁”、“孝”、“礼”德育模式的当代反思
青年是提升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力量,能否成为德才皆备的人才,关系着国家、民族的未来。作为儒家创始人,孔子在教学实践中找到的“仁”、“孝”、“礼”的德育模式,在德育工作倍受各级各阶层重视的今天,是值得我们思考与借鉴的。“仁”是孔子伦理哲学中最高的信念,是抽象的存在,不是具体的存在,因而直接用“仁”的思想教育学生是空洞的,也难于把握具体的尺度,反而使目标变得模糊。孔子为了避免这种误会,他想到了另外两个概念加以引领,以便把握住“仁”的关键——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第一个概念为“孝”,从“仁”的基础层面加以引导,使学生做到“不背本”;其二为“礼”,从“仁”的表达上加以限定,使学生在行为上做到“不逾矩”。
一、“仁”的目标体系:体现个人与社会的发展需要
德育目标的制定不是教育者主观的臆想。教育者首先必须考虑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社会的人才目标,其次又不能不考虑个人的发展需要——个人的成才目标。社会的人才目标与个人的成才目标并不是同一个层次的,带有全局性、普遍性、根本性的社会人才目标决定着个别性、特殊性、具体性的个人成才目标。在孔子的学问体系中,“仁学”是根本的,在德育上也是他的目标。这个目标可具体分作两个紧密联系的方面,其一,认识客观世界的发展方向——虽然“礼坏乐崩”,但最终必然指向“天下有道”;其二,按照客观世界的发展方向去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爱人”与“克己复礼”。“爱人”与“克己复礼”可以在不同人身上有不同体现,但“爱人”与“克己复礼”必须成为社会的普遍行为。因而可以这样认为,“仁”恰恰是能把处于不同层次的社会成才目标与个人成才目标统一起来的总目标。由此可见,孔子“仁”的德育目标的思想精髓,在教育理论迅速发展的今天仍然有其合理的部分。
“仁”是指人的内在道德品质,能否具有优良道德的品质,主要决定于个人的道德修养,而不是决定于他人的影响。所以无论是“爱人”还是“克己复礼”,都要求每一个人从自身、自觉、自愿的前提出发,否则就不能叫做“仁”了。“仁”在孔子的哲学体系中是抽象的存在,因此要做到“仁”,并不能把它理解为哲学本体的“仁”,而是要找到“仁”的境界,把抽象的本体还原成具体的存在——“为人由己,而由乎人哉”,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做到自身、自觉、自愿。在德育工作开展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今天的学生恰恰缺少这种自身、自觉、自愿的心态,在“爱人”与“克己”两个方面做得不到位。
在校园里提倡同学之间要相互关爱。但不少同学在理解“爱人”时常常将之理解为最需要帮助,也只有在别人需要帮助时,自己的“爱”才能体现出来,这种“爱人”是不到位的,有条件的。弱势固然是值得同情的原因,但不能成为被人爱的原由,因为爱人是没有条件的。所以孔子这样解释爱人:“君子学道则爱人”(《阳货》)。爱人是一种精神的高度,而不应是物质的高度。
在《论语》中,关于“仁”的解释比较经典的除了“爱人”,就是《颜渊》篇中孔子对颜渊的回答了:“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孔子的这句话,重点在于克己,即严格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使个人的行为符合客观世界的规范,形成良好的个人品德。青年阶段正是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青年人必须充分地认识客观世界,按照客观世界的要求通过“内省”、“自省”、“克己”等修养方法努力改造自己主观世界,按照社会发展的要求去规划自己的发展目标,最终实现个人与社会发展目标的高度统一。
二、“孝”的根基培养:合情合理的接受途径
学校德育目标的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重要方向标。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里明确提到了民族精神的作用,而“孝”文化本身就是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一个基础,在德育教育体系中,应得到重视。可以把它作为德育的一个重要内容,用它最朴素的亲情功用去满足学生自我发展与完善的需要。因为孝“是最起码的伦理道德,是人自幼就有的一种朴素感情。以孝为起点培养个人的善良品质,是一个符合德育规律的循序渐进的过程”[1]。只有这样,最终才能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进而对和谐社会的建设能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论语·阳货》中孔子与弟子宰予有一段关于“仁”与“孝”的争论,争论中宰予与孔子同时看到了社会的焦点问题“礼坏乐崩”——社会旧的价值体系崩溃了,人们的思想处于混乱状态,主体的需要产生了——结束混乱。至于怎样结束这种混乱的状态,两人想到的方法并不一致。宰予主张从社会矛盾本身入手,采用政治手段,迅速解决混乱;而孔子主张从社会矛盾产生的根源上入手,从社会关系的最基层面“孝”入手,做到本正源清。从二者手段的功用上讲,虽然都能满足了社会的需要,但者却有本质的区别。宰予的措施是激进的,能迅速消除矛盾所表现出来的混乱现象;孔子的措施是保守的,虽然不能迅速消除矛盾的现象,但从长远打算,却能解决矛盾的根源。
从师生二人的争论可以看到,“孝”突破了家庭伦理关系,深入到整个社会政治生活。在功用上,客体“孝”既能满足主体合情的需要,也能合理地解决社会问题,对社会与自身的和谐发展能起到积极作用。儒家学者就是利用“孝”的合情合理的功用,认为它是“仁”的基础,并把它在社会生活中到处推广。《学而》篇中提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为政》“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孝经》第二章中,孔子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因此,今天的教育应该反思,“孝”德教育必须突破陈旧的看法。“孝”不仅仅在于使某个家庭能和睦相处,更重要的在于能培育出中国特色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的培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它的建设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只有对各种社会问题有了一个根源上的认识,深入到合情合理的最基层社会,才能真正构建起来。
三、“礼”的强制约束:实现德育目标的重要手段
德育方法对于实现德育目标,完成德育任务以及保证德育的实际效果具有重要意义,是不可替代的手段。在孔子的德育体系中,为了保证“仁”的目标的实现,就必须选择合适的方法——“礼”的强制约束。这体现了今天德育的一个基本原则:自主性与社会性相统一。
道德作为抽象的概念,只有与它的具体形式——礼仪相联系,才能被人们感知,进而认同,最终自觉践行这些基本规范。同时,社会是“人们相互作用的产物”[2],要使整个社会中的人,相互作用时呈现和谐状态,就必须要用规范性的东西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而制定社会的价值导向体制则能起到积极的作用。事实上礼仪是道德向人们提出的基本行为规范,通过这些外在的行为规范去传递道德的内在价值,达到由外烁内的效果,进而使道德在人身上自觉执行,做到自主性与社会性的高度统一——“道德仁义,非礼不成”。
《论语》中孔子言论恰如其分的证明了这个事实:先言“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又言“不学礼无以立”,再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最后到七十岁时能做“从心所欲,不逾矩”。因而对学生加强“礼”的教育,一定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礼”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现在有不少人认为作为古代社会的“礼”,在很多地方已经与今天的社会显得格格不入,所以没有必要去讲“礼”。但不论我们愿意与否,“礼”作为中国人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通过两千余年的生活积淀,已深入到中国人的民族性中。因此我们要做的并不是讲拿来主义,生硬地把古代社会的“礼”,一成不变地套用到今天的社会生活中来;而是要批判地继承,把握“礼”的精髓——社会性,才能提升品德与修养。
自五四运动后,人们形成了对“礼”的一般认识,即“礼”是教条的、保守的、僵化的,应该被打倒的。但这种认识并不真实,并没有真正研习过“礼”。事实上孔子“把‘礼’以及‘仪’从外在的规范约束,解说成人心的内在要求,把原来的僵硬的强制规定,提升为生活的自觉理念”[3],这样就使得“礼”与“仁”两者相得益彰。《论语·八佾》“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俭是节俭,戚是哀恸之情;礼或丧,与其流于虚文,不如表现质朴与哀戚为佳。可见在孔子时代早先留下的礼节,已不能合拍,成了繁文缛节,所以孔子逆时流的提出,质朴与哀戚才是“礼”的本来面貌——社会的真实需要。“俭”与“戚”,要植于仁心,强调自身内在的心理依据,使“礼”与道德修养发生密切的关系。而这种联系正是从社会成员的道德情感角度出发,符合一般规律,将自主性与社会性巧妙地统一到一起。因此梁漱溟曾指出,礼文“或则引发崇高之情,或则绵永笃旧之情,使人自尽其心而涵厚其德,务郑重其事而妥安其志。”[4]也就是说“礼”并不是僵化的,而是与社会情感时俱进的。
参考文献
[1] 刘任丰.对传统孝德的思考.教学与管理,2007(3).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4]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责任编辑 陈国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