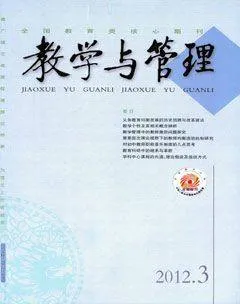地域话语系统的教学价值追寻
在不同地域学校的课堂中,存在着规范话语系统和地域话语系统。话语是传承文化的载体,不同的话语系统便造成了文化间的阻隔。学生课堂话语的不适应,会形成语言认知缺陷,难以建构对课堂教学内容的意义。新课程带来的教育根本理念是关注生命发展,因此,课堂教学应从“人的生命发展”这一高度来认识与实施,要贴近学生的现实生活,允许地域话语的参与,并有效实现地域话语转换为规范话语。
一、课堂教学中的话语系统
1.课堂中的规范话语系统——课程话语和教师的介入性话语
课堂中的规范话语系统首先表现为课程话语。课程内容要体现国家的意志,体现主流意识形态,代表主流文化话语。师生“教”和“学”的课堂交往活动都受各个课程层面上的制度性话语所支配和控制。课程的话语形式是文本的,是以规范的现代汉语文字、词汇、语法、修辞表达的,是课程专家和教材编制者以文字符号的形式进行理性表达的结果。课堂中的规范话语系统还表现为教师的介入性话语。教师课堂教学话语形式是规范的口语(普通话),是教师根据其知识储备和相关生活经历,结合学生的认知水平、认知结构和相关生活经验等方面的特点,对以课程教材编制者为课堂教学言说主体的课堂教学话语系统,进行双向解读、感性表达的结果。教师就是在课堂中引导学生对教材编制者的话语内容展开“意义与关系的重建”,是同教育内容对话、同学生多样的认识对话、同自身的对话而展开教学的。
2.课堂中的地域话语系统——方言和少数民族话语
课堂教学话语系统除了以课程专家、教材编制者和教师为言说主体的规范话语系统外,还有以学生为言说主体的地域话语系统。学生的课堂学习,就是将其对教师的课堂教学话语系统由感性到理性的把握,还原为与其学习、生活经验和已有知识相关的事实。所以,学生课堂学习的话语系统,具有生活上的还原性和规范上的待提升性。地域话语系统包括方言和使用汉语文字符号的少数民族话语。每一种方言都有自己的语音系统、词汇系统和语法修辞系统。不同地域的话语系统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异,南、北方的方言差异更大,相互间甚至不能通话。大多数少数民族的话语系统虽然借助汉语文字符号,但仍然具备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等基本言语要素。在他们族群聚居的地域中,通行的话语是他们本民族的母语,传承着他们各自的族群文化,与规范的共同语所承载的主流文化也有较大的差异。
二、两种话语系统的文化阻隔
1.课程话语的制约
课程话语是传承先进主流文化的代表,具有规范性。从课程运作层次看,国家课程话语表现出统一性特点,具有法律权威或行政权威以及强制性;教师所教课程的话语,是由教师决定并组织学生学习的课程,是教师对国家课程和学校课程的觉察认识与自己的课程理想相互作用的结果。它包括文本的教学实施方案和有声的课堂教学活动实施。教师的权威和学生的接受心理,决定了教师所教课程的中心地位和导向作用。所学课程的话语,是学生在有组织的教学活动中按照学校和教师的要求而实际学习的课程。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教师的所教课程制约着学生的所学课程。而学生中通行的是地域话语,特别是处于亚文化地域的山区乡村,由同乡构成的族群话语在交流中具有很强的优先性。而地域性话语在教学中不具有合法性,教师课程话语是排斥以学生为言说主体的地域话语的。但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载体,人们世世代代在一定的地域中生活、交往,形成了地域文化及话语。每一种话语都与其特定的文化相对应,受文化观念的影响与制约。地域文化难以进入校园,学生原来的地域文化、生活经验与规范话语承载的主流文化就产生了阻隔。
2.学生认知结构的制约
课堂话语系统是由不同范围的言说对象及相应的不同特质的描述性、解释性语言构成的,而言说主体认知结构水平及状态的不同,又决定着不同特质的描述性、解释性语言。课程教材编制者、教师和学生三者由于主体间认知结构的不同而存在话语差异。话语系统不同,所承载的文化也有差异,在理解事物和表达方式方面就存在差异,课堂教学言说的对象就难以被学生所理解,学生的所得就仅是教师所教课程的一部分。
三、课堂话语的教学价值迷误
在文化哲学的视角下,人在其生命存在的整个过程中,都在进行价值的追求,当价值预设形成之后,就会作用于活动,当活动不可能达到人精神预期的效果时,如果继续坚持这种价值预设,而按它对活动加以强制或“改造”,就会形成人们难以料到的消极后果。而人们由于在实际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的类型不同,需要解决的迫切性不同,就会在诸多价值中向某些价值倾斜,轻视以至忽略另外的价值,这就形成价值迷误。
教学活动特别注重语言的规范性,这是一种价值设定。在教学中主要体现在“言”与“意”的关系上。例如语文教学,在处理“言”与“意”的关系时,往往强调对“言”的准确解读和规范表达,排斥学生的地域话语;但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心中的“意”并非都在“言”之前就已存在,而是在“言”这种生命存在活动的过程中,“意”才逐渐明确起来的。因而“言”的原创性同“意”的明确化是同一个生成的过程。语文教学中规范话语的排他性会抑制学生理解和表达的欲望,失去了富有个人色彩的、精确而多样化的表达,以及对世界认识的多样化,“意”的明确化就难以生成。
文化要受到一定的地域性制约,不同地域的族群有对文化的不同诉求,其话语系统所展现的文化世界也各不相同。学生就是根据其生命存在的文化世界的实践体验来认知、理解所学课程的。他们会按照自己的意向来改造、言说客体,使它适合于自身,这就很容易跟所教课程产生偏差。学科课程和教师代表主流文化的教学话语,对于学生来说并非熟悉的,学生的地域话语对教师来说也有一定陌生度。文化是在人的交往实践中传递的,师生交往中的文化传递,必然导致双方各自认知图式、行为习惯和心理倾向发生不同程度的冲突,这会妨碍相互的理解和课堂交往。学习主体的自我意识被封闭在丧失了社会亲和的环境之中,失去了自我话语,导致教师以实体思维方式来理解教学,理解学习。由此,课程便成了“传递知识课程”,脱离了学生自身经验的实际感受,也就丧失了生成、发展、整合的契机。学生作为生命的人、学习的主体被空场了;教师丧失了“我”的人生经验,成了传递知识的工具,作为生命的人也被空场了。课堂因为师生的“被空场”而置于一个没有社会环境的世界,教学对学生的思维训练、情感陶冶和品质培养也就“悬置”了。
人是通过自身的行为使内在的文化意向外化为价值的实现过程的。学生学习知识,是对知识意义的自主建构。而“传递知识”的教学,向学生传递的是一种毫无“原创性”的,难以唤起想像力和创生新思维的知识。学生发现不了“传递知识”学习的意义,无法将这些知识“经验化”到自己的生活世界中,就会沦为“学校教育的不适应者”。教学应关注学生生命各个层面和谐、协调的发展。教师在作出一种价值选择的时候,对于价值本身的成立条件以及它的成立限度,应该有认真而谨慎的研究,以免陷入片面性和超时性的价值迷误。
四、地域话语的教学价值追寻
1.从“传递中心课程”转向“对话中心课程”
知识是不能传递的,只能通过对话来实现学生对知识意义的建构,课程教学方式必须从“传递中心”转向“对话中心”。话语是教学的必要手段,教学话语是对教学内容的阐述、演绎和解说,只有通其“言”才能明其“意”。话语可达成或通向对“意”的理解,但也会局限理解、变异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学的理解就是话语的理解,教学活动就是话语活动。教师如果不能融入当地文化生活,对当地话语缺乏认识,在课堂教学中就可能难以与学生交往,形成教学困难。课堂教学应从文化上理解学生,允许地域话语的参与,再予以规范化引导提升。
2.从“生活化还原”转向“理性提升”
“生活化还原”即将教材内容贴近学生现实生活。学习是认知、情感和意志的综合体现,当学生以有意义的方式对任一情境作出反应时,会对情境的各个不同方面作出多种多样的反应,即“共时性学习”。“教师对任何学生学习情境的处理方式,从好的或坏的方面影响着这些共时性学习的总和”。一种学习行为的进行会有多种心理因素参与,学生对学习对象进行意义建构时,总会或多或少地牵动其他方面,形成“共振效应”,收获的就不单是“言”的知识,他会跟自己的生活经验、已有体验联系起来,获得对“意”的理解和情感倾向,还可能获得学习的方式方法,增强学习信心。这些关系是相互交织的,教师应关注学习的共时性,关注学习与生活的联系,关注学习的情境性与多样性,关注学生对学习内容的多种反应。既要顾及学习的主要目标,又要顾及学生的伴随性学习,才能更好地引导学生利用地域话语中与学习内容相关的各种因素的协同作用,有效实现从课程内容的生活化还原到理性的提升。词汇是话语要素中变化最频繁、最迅速、最活跃的因素。将表征新知识的词汇转换为当地通行的话语词汇,进行贴近学生的生活化还原,再现学生熟悉的生活情境,有助于激活学生的原有经验。学生通过关联比较,对学习的新内容产生体验、迁移,就能建构起新内容的内在意义。“如果想方设法把教材转译成儿童的逻辑形式,并极力鞭策诱使他前进,那么,就很可能在他的早年介绍这样的观念和作风,以使他在日后的生活中成为有教养的人。”
学生对所学习的新内容实现意义建构之后,再指导他们进行地域话语与规范话语的理性转换提升,用规范话语进行表达再现,近似于“双语教学”那样,有利于使学生在加深理解、巩固知识的同时,掌握规范话语的运用技能,提高规范话语的水平。例如,学生校外用方言交谈,词语丰富而生动,与课堂上有天壤之别。陈永根老师设计了一堂语文课:要求学生用方言来说说自己亲历的一件事,然后,选取一位学生的发言,让其他学生现场解说成普通话,最后作总结:其实好多美妙的语言就存在于我们平时的交谈中,就看你有没有能力发现它,并把它“翻译”好,大家可不可以把你今天说的内容写在纸上呢?这一次,学生的作文水平仿佛一下子高了不少。陈老师的感悟是:教师应使课堂问题贴近学生的生活,贴近学生的知识结构,课堂才会活起来,教学效果才会好。课程是为学生的课程,把学生生活中的创意带进课堂,才能使学生在熟悉的情境中建构新的意义。
3.从“单向度的人”转向“完整的人”
教育的目的是完善“人”的建构,使人成为拥有丰富内心体验和感受,对民族文化精神自觉认同的“文化”的人,而不是能够熟练运用规范语言,却与民族文化、情感有隔膜的“工具”的人。课堂教学排斥作为学生母语的地域话语,而学生又缺乏将地域话语转换为普通话的意识和能力,在课堂上便难以参与,教学便失去了师生间的交往和互动。由是,“传递知识”成为常用的教学方式。课程教学重视了知识、技能,却忽略了情感、态度、价值、体验,工具理性取向下的学生发展只剩下一个向度——技术性向度。人是多维关系的存在,人与人的关系是“完整人”的一种本质性规定,即使适应“传递知识”教学方式的学生,由于失去了人与人的关系及其与自身、与生活环境的关系,充其量也只是个单向度的“知识人”、“工具人”。
人本主义认为,人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人本身就是最高价值的体现。这对课程价值观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学生为本的课程价值取向。听与读是学生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而学生对课堂教学话语的不适应,就会严重影响他们的语言、认知及社会性的发展,还会引发他们自卑、焦虑、厌学等一系列的心理问题。用共同方言交往的双方容易产生亲缘感、亲和力,利于消除心理隔阂。对语文教学来说,尤其要鼓励学生积极积累话语素材,在普通话和方言及少数民族话语的碰撞中,比较并体悟话语的意蕴,感受语言的独特魅力,提高语言素养,增强语言创造力。学习层级表明,学习任何新的知识、技能,都需要具备某种先前的学习。学习是累积的,学生在长达十几年的生活和学习中,累积了许多生活经验及自己的认知方式,这是深入学习、继续发展的基础。课堂教学应尊重学生的地域话语,引导地域话语跟普通话转换提升,使学习成为与学生个人意义密切相关的意义性学习,实现认知和情感的统一。罗杰斯就认为:“意义学习把逻辑与直觉、理智与情感、概念与经验、观念与意义等结合在一起。当我们以这种学习方式学习时,我们就成了一个完整的人。”
地域话语是我们情感与学习的需要,规范话语是我们工作和终身学习的需要,是促进交往沟通、收集与筛选信息的需要。规范话语与地域话语是互相补充和融合发展的。新课程文化的建构是一个文化冲突与文化适应的过程,只有从文化上理解他人,才会更好地认识他人、学习他人和发展自己,因此,我们应关注课程改革中话语系统重建背后的文化假设与教育实践行为的转换。
参考文献
[1] [日]佐藤学.课程与教师.钟启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2] 李鹏程.当代文化哲学沉思.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3] [美]威廉.H.克伯屈.教学方法原理——教育漫谈.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4] [美]布鲁纳.教育过程.邵瑞珍译.北京:文化教育出版社,1982.
[5] 陈永根.原来方言也能如此精彩.小学青年教师(语文版),2006(6)。
[6] 莫雷.教育心理学.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7] 李广,马云鹏.课程改革中的文化冲突与文化适应.教育发展研究,2008(22).
(责任编辑 张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