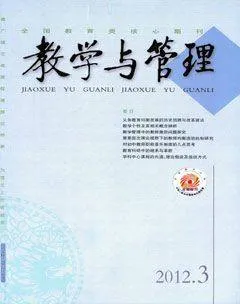论卡西尔人学思想及其对教育的关照
一
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1945)是20世纪德国著名的哲学家。他的人学思想在西方现代哲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认为:“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这看来是众所公认的。在各种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一切争论中,这个目标始终未被改变和动摇过:它已经被证明是阿基米德点,是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中心”。[1]教育的对象是人,对人的理解和把握是一切教育活动的逻辑起点。卡西尔的人学思想对我们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观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卡西尔在1923~1929年就完成了三卷本巨著——《符号形式的哲学》,该书从文化的角度对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建立了文化哲学体系。在此基础上,他又出版了《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引》一书,精辟地总结了他的人学研究成果。这两部书是了解和掌握卡西尔人学思想的钥匙。
二
“人是什么”是一个千古之谜。自古希腊开始,先哲们就开始思考和追问这个问题。但由于当时人们对世界本原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对人自身的认识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从普罗泰哥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和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这两个命题提出后,人们才从对自然的关注转向关注人自身。从此,对人的研究成为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当时人们对人的认识主要集中在人是具有理性的,这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重要特征。亚里士多德指出,“没有任何东西比理性更属于人的了”。[2]在他们看来,理性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也是人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最根本最伟大的力量。到了中世纪,在宗教思想统治下,人们对人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转向,认为理性是使人走向堕落的原因,是罪恶的源泉,正是由于具有了理性才使亚当和夏娃被驱逐出了伊甸园,这样,人开始了背负原罪的枷锁在人间挣扎地生活。所以,理性是罪恶的源泉,人的本质不是理性,而是反理性。这种观点在整个欧洲中世纪持续统治了近千年。但以哥白尼的“日心说”的发表为标志的近代科学彻底否定了这种观点,宣扬科学的基础是理性,人是理性的动物又重新成为对人的本质的定义,尤其以笛卡尔和黑格尔为主要的代表,前者力图以几何学定义人的本质,建立精确的几何人类学,后者更把理性推向顶峰,认为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社会和精神,过去、现在和未来,就是“绝对理念”的正、反、合三段式的推演。但理性是否就是人的本质的体现呢?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就把人定义为纯生物学上的一般动物;尼采公开宣扬人的权利意志;弗洛伊德突出人的性本能;马克思则推崇人的经济本能,等等。卡西尔认为,以上“每一种理论都成了一张普罗克拉斯蒂的铁床(普罗克拉斯蒂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强盗,他捉到旅客后,便将旅客缚在床上,然后或砍,或拉长,以适合其睡的床),在这张铁床上,经验事实被削足适履地塞进某一事先想好了的模式之中”。[1]他不是要否定这些理论,而是力图在这些分数之间寻找出一个公分母,使所有这些理论、经验形成一个中心指向,从而全面揭示人的本质。
为了回答“人是什么”,卡西尔从考察人类世界和自然世界之间的区别入手,首先区分了信号和符号之间的差别,认为“信号和符号属于两个不同的论域:信号是物理的存在世界之一部分;符号则是人类的意义世界之一部分”。[1]人与动物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动物只能对信号作出条件反射,只有人才能把这些信号改造成有意义的符号。人不是生活在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的,而是生活在符号宇宙之中的。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等是符号宇宙的各个组成部分,它们是织成符号之网的不同丝线,是人类经验的交织之网。人的世界就是由各种符号构成的世界,符号是人创造的,人通过符号认识事物,离开符号这个人为媒介物中心,人就不可能看见或认识任何东西。而且,“人能发明、运用各种符号,所以能创造出他自己需要的理想世界,而动物却只能按照物理世界给予它的各种信号行事,所以始终不知何为‘理想’,何为‘可能’”。[3]符号系统赋予了人一种创新的能力,使人能够不断地把理想变为现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卡西尔提出人是符号的动物这一命题。
卡西尔认为,人运用符号创造语言、神话、艺术、宗教等文化,也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人类的全部文化都是人自身以他自己的符号化活动所创造出来的产品,而不是从被动接受实在世界直接给予的事实而来。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也只有在文化活动中,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作人不断解放自身的历程”。[1]这是因为,“人的突出的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行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1]人的劳作怎样,人的本质也就怎样;人的创造性活动如何,人性的面貌也就如何。人——符号——文化成了三位一体,是卡西尔人学思想的结构体系,人学就是符号哲学,文化哲学。在卡西尔看来,人并没有什么与生俱来的抽象的本质,也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永恒的本性;人的本质是永远处在制作之中的,它只存在于人不断创造文化的辛勤劳作之中。因此,人性并不是一种实体性的东西,而是人自我塑造的一种过程,真正的人性无非就是人的无限的创造性活动,人的本质在于创造。
可见,卡西尔对人的本质的界定是从动态的角度入手的。他把人的本质看作是人在运用符号不断生成文化的创造过程之中形成的,人的劳作的特性决定了人的本质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逐步生成的,存在于创造活动之中。他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是一种动态的功能性的定义,而不是像以往的对人的本质的静态的实体性的定义那样,把人性看成是一张普罗克拉斯蒂的铁床,对经验和事实材料等进行增减以适合于已经设计好的模式。总之,卡西尔的人学思想把人看成是永远处于发展创造过程之中,人没有固定的本质,创造才是人的本质。他的人学思想对于我们理解教育,重新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观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三
一切教育活动的开展都建立在我们对人的理解之上,有什么样的人性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活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素以善恶来判定人性,孟子主张“性善论”,荀子主张“性恶论”,朱熹主张“性三品”。在不同的人性观指导下,教育者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活动也就不同。这些人性观跟卡西尔提到的在他以前的西方有关人性的思想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人性或者说人的本质看成是固定不变的,是一张普罗克拉斯蒂的铁床,然后对经验材料进行适足削履式的调整以使其符合已经设计好的模式,它们都是对人的本质的静态的固化的理解。教育的对象是人,人是教育活动的中心议题,怎样看待人、理解人、引导人是一切教育活动首先必须在认识上解决的问题。目前,我们正在构建和谐社会,倡导以人为本的教育,卡西尔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和定义能够为我们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观给予有价值的启示。
卡西尔对人的本质的理解的最为关键的一点是,他把人性看成是动态发展的,不断生成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静态的,认为不存在永恒不变的本质。教育的对象是人,具体地讲,是指处于成长和发展中的儿童。在卡西尔看来,儿童的本质肯定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逐步的生成之中的。这跟萨特所主张的人是“存在先于本质”的观点是一致的,认为人的本质就是人的存在本身,人的本质不是他人所赋予的,而是自身在不断的实践活动之中所形成和创造的。加拿大现象学教育学大师马克斯·范梅南也认为,“何谓儿童?看待儿童其实就是看待可能性,一个正在成长过程中的人”。[4]儿童身上潜藏着许多可能性,作为教育者不能用一成不变的眼光看待他们,应该给予他们积极的期待,发现儿童身上的闪光点,使儿童把自身所蕴藏的潜能发挥出来。但反观我们现实的教育实践,不难发现,教育现实中存在着大量的对儿童的固化认识,最为明显的是“差生”现象的普遍存在。一旦某个儿童被贴上了“差生”的标签,也就意味着给他宣判了“死刑”,他在教育者心目中的差生形象就难以改变了。教师岂不知,差生也有转变为好学生的可能性,关键在于教师持有怎样的儿童观。从卡西尔的人学观点出发,教师要把儿童看成是一个个处于不断发展和成长过程中的人,儿童的本质并不是静态固定的,而是动态地发展形成的。儿童是怎样的不仅取决于现在是怎样的,更要着眼于他们将来会是怎样的,他们是动态发展变化的,而不是静止不变的。教师职责的关键在于,要给予儿童积极的期待,以至耐心和信心,引导儿童朝向积极的正面的方向发展。
卡西尔还指出,人的突出的特性是人的劳作,“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圈。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1]人的劳作是怎样的,那么人的本质就是怎样的。人的本质是在人的劳作中形成的,而人在劳作过程中创造的语言、艺术等等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在表现。对于儿童来讲,他们究竟是怎样的,取决于他们所进行的活动,他们的本质是在他们所进行的活动中形成的。当然,卡西尔所说的劳作并不是普通的劳作,而是运用符号创造文化的活动。但在更深层的意义上,他揭示了人的本质是在人的活动中形成的这一真理。对于儿童来讲,他们也只有在参与各种劳作活动,即利用已有的文化符号系统不断创造出新的文化形态的过程中,他们的人性的圆圈运动才会逐渐展开,人性也会日臻完善。在中外教育史上,有些教育家和学者就很注重儿童活动能力的培养,最为典型的代表人物有美国的教育哲学家杜威和中国的教育家陶行知。杜威倡导儿童要“做中学”,痛斥把儿童当成是简单地进行灌输的容器,反对教条式的教学,主张儿童积极参与课堂、动手制作、实验等,自己去发现真理。陶行知提出了“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思想,创立了“小先生”制等,鼓励儿童积极行动,参与学习活动、生产活动、建设活动,等等,认为儿童身上具有无数智慧,主张成人从来都不要小看儿童的能力,要充分发挥儿童的聪明才智。儿童正是在不停地劳作中发现真理和创造文化的同时,也在发现着自我,塑造着自我。儿童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本应该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得到全面的发展。然而,在当前的教育实际中,儿童的劳作被片面化,被简单地理解成是单纯的理智训练,那些能够提升儿童审美能力、劳动能力,以及身体素质等的活动被排除在了儿童劳作的范围之外。这样,由于儿童的劳作是片面的,势必他们的发展也就是成为片面的了。所以,要使得儿童获得圆满的发展,就必须让他们参与丰富多彩的活动,在劳作中,他们在创造新事物的同时,也就创造出自身完满的人性。
在卡西尔看来,人不是一个被动的存在,而是一个积极生成的存在。人不是自在的存在,而是自为的存在。人是“懦夫把自己变成懦夫,是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而且这种可能性是永远存在的,即懦夫可以振作起来,不再成为懦夫,而英雄可以不再成为英雄”。[5]人是什么样的取决于人自身的选择及其行为。卡西尔认为,人具有主体性和能动性,能够利用符号去创造文化,而且在创造文化的同时不断地走向自由,以达到自身的解放。教育的过程其实也就是儿童获得自由,实现自身解放的过程。儿童作为教育过程中的主体,他们具有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对来自外界的教育影响,并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而是在进行积极主动的选择。在教育过程中,我们要把儿童当成真正的教育主体来看待,要考虑到他们自身身心发展的需要。在教育目的的确定上,我们不能仅仅关注社会发展的需要,更要关注儿童自身的发展和成长的需求以及他们的身心发展的阶段性、差异性等特点,把能够促进儿童的身心和谐发展作为教育的根本诉求。在教育课程内容的设定上,我们应该从儿童的立场出发,要结合儿童的兴趣和爱好来选取教育内容,要照顾到儿童的生活实际需要,有助于他们更好地社会化,同时,教育内容还要具有文化性,能够真正有益于儿童的精神世界的充盈和完满,以及他们的创造性的培养和发展。在教育教学方式和方法的选择上,我们不能采取简单的灌输式教育,而是要想方设法发挥儿童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参与到教育教学过程中来,可以采用合作学习、小组讨论等方式来进行。在教育评价上,我们不仅要关注儿童现在的状况,更要着眼于他们未来的发展,不要给儿童作出盖棺定论性的评价,儿童今天的状况并不能代表他们明天的发展,要给予他们积极的期待。
总之,卡西尔的人学思想对于我们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观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提醒教育工作者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儿童,人的本质是在活动中创造生成的,没有永恒不变的本质,儿童正处于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之中,更是如此。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要重视儿童的生成性、劳作性和主体性的发挥,以促进他们的完满人性的形成。
参考文献
[1]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2] 莫迪默艾德.西方思想文化.长春:吉林出版社,1988.
[3] 甘阳.古今中西之争.上海:三联书店,2006.
[4] [加]马克斯·范梅南.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李树英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5] [法]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责任编辑 付一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