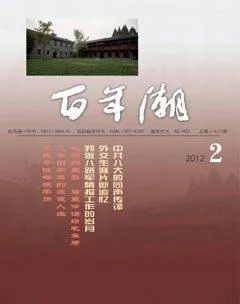父亲田家英的收藏人生
2011年10月27日,《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法书展》在国家博物馆开幕。小莽苍苍斋是父亲田家英的书斋名,展览的展品是父亲生前的旧藏。参观展览的人们,无不对田家英在传统文化传承上的认知和作为深表敬佩。但人们只知道田家英学识渊博,很少知道他缘何萌发了收藏清代学者墨迹的想法。下面,我根据我和母亲的记忆,讲讲父亲的收藏以及相关的往事。
父亲去延安前在家乡读书的时间,算下来,总共不过六年。他的学识和知识主要来自于自学。
他是四川成都市人,不幸3岁丧父,9岁失母,原本殷实的家境日渐败落,12岁被迫辍学当了学徒。直至15岁,靠卖文的收入考入初中。然而仅一年,又因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被校方开除,1937年秋去了延安。
少年时代,父亲曾梦想成为一名作家,12岁便发表文章,赴延安前,已在成都的报刊上发表了130多篇散文、小说和杂文,在自学的经历中,他逐渐对中国文学和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
到延安后,父亲19岁就在马列学院担任中国近代史教员,为了讲好课,他通宵达旦地攻读史学著作,打下了一定的功底,也更加关注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
学习成长中,父亲有幸结识了著名学者范文澜,两人并成为忘年交。在范老的教诲和影响下,他对中国近代史研究逐渐形成了方向,或许可以说,范老是他走进清史研究大门的引路人。
在杨家岭图书馆,父亲借阅到一本梁启超作序、萧一山著的《清代通史》,很感兴趣,他佩服作者的治学精神和勇气,但他认为萧一山的书受时代的局限,新的史料和研究成果未能采用,是很大的缺憾。从那时起,父亲便萌生了有生之年写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清史的想法。
父亲收集清人墨迹,还应该说与毛泽东主席的熏陶分不开。
从1948年开始,父亲担任了毛泽东的秘书,和主席朝夕相处。20世纪50年代有段时间,毛泽东几乎每天晚上都把父亲叫去,交办工作后,两人就谈古论今地聊起来,从历史、文学、典故到古今人物,可谓志趣相投,无话不谈。一次谈得畅快,毛泽东和父亲戏言:待你死后,墓碑上什么字也不要留,我送你五个字“读书人之墓”,你看怎么样?说完毛泽东开怀大笑。毛泽东喜欢好读书的人,父亲也从毛主席处受益匪浅。
母亲清楚地记得,20世纪50年代,一次她和父亲去王府井古旧书店的路上,聊到治学时,父亲讲了一段话,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父亲说,治学不应脱离现实社会。多年来研究中国近代史,使他逐渐形成了一个看法。他认为,清朝是个很有代表性的朝代,可以说是集封建社会之大成。了解清代历史,可以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而我们从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不研究中国的过去,不了解封建社会形态的实质,是搞不好的。早在延安时期,他就有志于写一部清史。现在条件比过去好多了,只是工作太忙,但可以先着手收集资料,为写作和研究做准备。他告诉母亲,他的这种想法和认识曾和主席谈过,得到了主席的首肯。
从那以后,父亲开始了对清代学者墨迹的不懈收集,直至1966年。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父亲从北京、杭州、上海、武汉、广州等文化名城,收集到千余件藏品。他办公桌上经常放着一本萧一山编的《清代学者著述表》,凡收集到某人墨迹,就在书上这一人名前画一个红圈。他有志将书中一千几百位学者的墨迹,尽可能收全。
清代学者,大多在经、哲、史、地、音韵、金石或天文历法等方面有所造诣,他们留下的条幅、楹联、册页、信札,不仅书法艺术水平高,且内容丰富。尤其官吏兼学者的书简、信札,涉及范围广,时代特征鲜明,能够真实地反映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学术、人文的面貌,史料价值更高。父亲收集的信札达300余家近600通,多数为清代学者之间的信函往来。
曾和父亲一起工作了17年的逄先知同志说过:收藏清代学者墨迹,是田家英的业余爱好,却成了他全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使他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更加充实、更加丰富。
“文化大革命”之初,父亲含冤去世。在那段特殊的年代,他坚持实事求是,是一个诚实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气的人,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很少随声附和,很少讲违心话。1962年政治上受挫折后,他的心里极端苦闷,然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使他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清人墨迹的辑藏中,这个爱好给了他精神世界极大的安慰。
父亲的文化性格,体现在他的收藏中;同时,收藏活动也陶冶着他的情操。
父亲有几件非常珍爱的藏品,如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一幅《观操守》行书中堂,是林则徐遭贬黜后所作,语意含而不露,从容安详。“观操守在利害时,观精力在饥疲时,观度量在喜怒时,观存养在纷华时,观镇定在震惊时。防欲如挽逆水之舟,才歇力,便下流;从善如缘无枝之木,才住脚,便下堕。”它告诉人们:一个人的操守、精力、度量、存养、镇定要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才体现得最真切、最完备。可以说,这幅墨宝,是林则徐高尚情操和思想境界的真实写照。
又如谭嗣同的一幅扇面《送宋恕》,行隶兼有,秀美中透着刚劲,被父亲视为珍品,这不仅因谭嗣同英年早逝,墨迹传世很少,更主要是他敬重谭嗣同舍身取义的气节。父亲欣赏时,有时情不自禁地吟诵谭嗣同的诗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父亲甚至将谭嗣同的斋名“莽苍苍斋”前冠一“小”字,用“小莽苍苍斋”为自己的书斋命名,以表达对这位爱国义士的敬仰。
面对即将来临的“文化大革命”风暴,父亲曾说“人不能有傲气,但不能没有傲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些品行和他一向仰慕的爱国志士“士可杀,不可辱”的思想精髓不无关联。
20世纪60年代初,为扭转“大跃进”运动造成的被动局面,父亲多次受毛泽东嘱托,带队到农村调研。
由于父亲从小经历过艰苦的生活,他一生对劳动人民始终怀有深厚感情。当他目睹了老百姓缺粮断炊或逃荒或病饿致死的惨景,同参加调查的浙江省委副书记林乎加讲述了清人郑板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父亲感慨地说:“一个封建社会的县官尚且如此关心百姓疾苦,何况我们共产党人呢!”
在四川,父亲在县社队干部大会上说:“我是一名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使大家挨了饿,对不起各位父老,共产党员看到这种情况是很痛心的。我一定接受委托,向毛主席反映真实情况。”至今当地干部群众记得父亲说话时泪流满面、声音哽咽的情景。
在浙江,一起参加调查的同志回忆,田家英对他们说:“办不办食堂并不改变社会主义,不要怕戴右倾机会主义帽子、怕受打击。人生最惨的事无非是妻离子散,死于非命。难道我们的命比老百姓的命大一些吗?我们革命不就是为了老百姓嘛!为老百姓而死又有什么不好呢?违反群众利益的事情,我们一定向上反映。”
60年代,父亲将林则徐著名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刻成图章,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说,“如果有利于国家,就不顾生死去做,哪敢为了个人的祸福躲避或追求什么”。“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一饭膏粱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这些诗句反映了他在那个年代坦荡赤诚的襟怀。
凡是接触过父亲的人,都对他有这样的评价:田家英做人真实,待人真挚,为人真诚。父亲性情活泼,为人豁达,他有一方图章“活泼泼地”,是从地摊上淘来的古印,常爱盖在书上,很代表他的喜好和性情。
他和我们在一起从不说教。怀念父亲,常常想起他带我们去王府井旧书店,出中南海东门,走在故宫护城河沿。夕阳西下,金光洒满宫墙,拉着父亲的大手,听他讲永远讲不完的故事,那种幸福至今温暖我们的心田……
多年来,我们按照父亲的心愿去努力。父亲为研究历史而收藏,同时,也为保护祖国文化遗产而收藏。他说过,这些藏品是人民的,将来应让它为弘扬祖国民族文化发挥作用。
1991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田家英收藏展”之后,母亲董边将包括吴伟业、龚鼎孳、王时敏、龚自珍、林则徐、何绍基等100多位清代著名学者、志士仁人的墨迹捐献给了国家,并由我们主编陆续出版了《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法书选集》上下卷,即将出版的还有小莽苍苍斋藏信札集、诗词集等。
每为父亲的小莽苍苍斋收藏做出一点事情,每听到专家们的好评和社会的反响,就更加唤起我们对父亲的怀念。
父亲的知心好友梅行这样说:“人死后是不会再有知觉的,家英并不会知道这些,但个人的情操、品性、业绩是可以流传下去的,在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增添人们的精神力量。这就是彻底唯物主义者的愿望。”
我以为他的话,是对父亲田家英人生追求最好的理解,也是对我们今天的努力最好的鞭策。
(责任编辑#8195;刘荣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