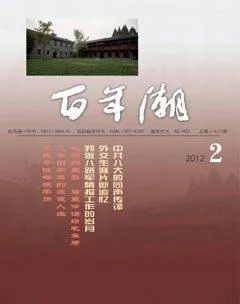外交生涯片断追忆
我于20世纪60年代初进入外交部,几十年中主要是参与和主管中越关系事务,曾任亚洲司科员、副处长、处长,其间曾四次被派到驻越南使馆工作,先后任二秘、一秘、研究室主任、政务参赞,1994年3月至1995年10月任驻老挝大使,1995年12月至2000年7月任驻越南大使。现在退休了,我愿将自己亲历和印象较深的一些事写出来与读者分享。
李先念出席胡志明葬礼:
冷对柯西金
1969年9月2日,越南胡志明主席逝世,享年79岁。周恩来总理作为胡志明的老朋友,于9月4日立即赶往越南首都河内吊唁。此外,中方又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出席9月9日举行的胡志明葬礼。
9月8日,李先念一行刚刚抵达河内,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阿劳动党的一位政治局委员就提出要到中国大使馆会见李先念副总理,说有要事相商。李先念虽不知道要谈什么事情,但鉴于当时的中阿关系,立即表示欢迎。会见时,阿方提出,在第二天胡志明主席的葬礼上,希望李先念不要同苏联代表团团长、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有任何接触,也不要同他打招呼。李先念同意了阿方的要求。
9日上午,我跟随中国驻越南大使王幼平提早来到举行葬礼的河内巴亭广场,按照越方的安排,站在看台上为外交使团划定的位置。当时中苏关系尖锐对立,越方在礼宾安排上颇费了一番心思。越南主要领导人排成一行,站在高高的主席台中央,而让李先念和柯西金分别站在他们的两侧。尽管如此,柯西金仍多次向李先念点头示意,但李先念信守承诺,都装作没看见,不予理睬。葬礼结束后,李先念和柯西金分别从主席台两侧走下来。柯西金看见李先念后,紧走几步,想同李先念打个招呼,而且把手都伸了出来。但李先念仍装作没看见,转身走开了。这一切,阿尔巴尼亚代表团都看在了眼里,甚为满意。
当日下午,越南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司长黄保山向中方转达了苏联方面的如下信息:苏联代表团团长柯西金的专机定于10日清晨离开河内回国,希望中途在北京停留两三个小时,同周恩来总理见面,特征求中方意见。大使馆立即向国内作了报告。10日清晨,大使馆收到国内的答复,同意苏联专机11日在北京停留,周恩来总理将在机场同柯西金会晤。但王幼平大使当时已去机场为中国代表团送行。那时通讯设备十分落后,没法用电话联系,大使馆参赞陈亮立即驱车赶到河内嘉林机场,向李先念和王幼平报告。但当陈亮急急忙忙赶到机场后,为李先念送行的越南总理范文同说,柯西金的专机已经在一个小时前起飞回国了。对于柯西金未等到中方答复便离开河内,李先念十分生气。
当天下午,越南外交部黄保山司长紧急约见王幼平大使说,他本人在这件事上犯了“严重错误”,受到范文同总理的严厉批评,目前正在作检讨。作为补救措施,越南外交部已约见苏联大使,转达中方的答复,让苏联大使立即报告柯西金。黄保山特别强调,这件事的责任完全在他个人,特向中方表示歉意。黄保山的道歉和检讨,如实地反映了越南领导人在中苏关系上小心翼翼的心态。当时越南的抗美斗争需要中国和苏联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强有力支持和援助,但中苏之间又尖锐对立,越南担心在处理中苏两国的关系上出现任何差错,都会影响到中苏对越南的支持和援助。客观地说,作为具体工作人员,柯西金的专机先行离开河内,同黄保山本人没有任何关系。
实际上,柯西金在胡志明葬礼上受到李先念的冷遇后,对于中方能否同意他在北京停留,心中更加没底。如果他在河内期间收到中方不同意他在北京停留的答复,则更加没有面子,于是便决定先行离开。当柯西金的专机抵达塔什干时,收到了莫斯科转来的中方同意安排会见的答复,莫斯科指示柯西金仍要去北京同周恩来见面,这样柯西金又折返去了北京。
11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首都机场同柯西金举行了会晤。尽管在当时中苏关系的大背景下,这次会晤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善两国关系,但在两国边界问题上达成了以下谅解:双方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在争议地区双方武装力量脱离接触、双方发生争议时由边防部队联系解决,从而使两国边境局势和两国关系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
会晤结束时,周总理对柯西金说:你这次主动要来,我们得到消息晚了,但我们的答复是快的。虽然你走了一段弯路,总还是起了一点效果。中国有句成语叫“不虚此行”。柯西金解释了他为何走弯路的过程,并表示他并不遗憾,很高兴到北京来。
周总理陪外宾回延安:
当众作自我批评
1973年6月,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率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当时越南的抗美斗争正处在重要关头。虽然根据越美双方1月签订的《巴黎协定》,侵越美军已于3月全部撤离了越南南方,但南方尚未解放。十几年来,周总理代表大后方中国,为支援越南抗美,不知耗费了多少心血,他当时虽已身患重病,但仍亲自出面接待来自抗美前线的客人,除主持会谈外,还带病亲自陪同客人到延安参观访问。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第一次回延安。专机抵达延安机场后,越南代表团成员和中方陪同人员的车队缓缓进入市区。尽管事先没有报道周总理回延安的消息,但不知怎的,至少有十几万延安各界群众不约而同地涌上街头,把道路堵得水泄不通,致使车队无法前行。北京陪同前往的公安部副部长于桑不得不走出汽车,站在人群中,为车队开路。大约半个多小时后,车队才到达宾馆。当时我作为翻译坐在越南副总理黎清毅的汽车里,他对我说:“看得出来,延安人民是在欢迎周恩来总理。”
下午,在客人听取介绍延安情况前,周总理对接待人员说,中午趁大家休息,他要悄悄地登宝塔山。为了不让群众发现再造成交通堵塞,周总理换乘吉普车前往,并绕道而行。不料吉普车陷进了泥里,是当地的同志和警卫人员一起把车抬出来的。现在回想起来,那次周总理登上宝塔山,可能是要向延安的父老乡亲做最后的告别吧!
接着,周总理陪同客人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当看到1949年10月26日毛主席给延安人民的复信时,周总理停下脚步,指着复信中的几句话说:“早在20多年前,毛主席就嘱咐延安人民要‘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但这一条我们做得很不够,很不够。对于周总理谈到的延安经济情况,我们从北京去的接待人员并没有多少切身体会。但仅从几个小时的观察,便可看到当时延安的商品供应十分匮乏,宾馆的小卖部货架基本上是空的。为了表示对北京去的工作人员的一点心意,当地外办仍决定卖给我们每人2斤延安核桃。
当晚,延安革委会宴请越南客人,周总理和陕西省领导同志出席作陪。宴会上准备了当地的土特产,如煮玉米、煮土豆等。客人们吃得很香,越南总理范文同说,他一口气就吃了两个土豆。宴会进行到将近一半的时候,周总理站起来,当着越南客人的面说,解放都这么多年了,延安的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人民的生活还这么艰难,我作为国务院总理,对此负有直接责任。今天我要当众作自我批评。说到这里时,在场的陕西省委书记马上站起来说,党中央、国务院和周总理对延安的工作和经济建设始终十分关心,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他表示一定记住周总理的指示,要尽快把延安的经济搞上去。
20多年后的1995年,我任驻老挝大使期间回国述职、休假。外交部组织我们部分正在北京的驻外大使、参赞到延安参观学习、考察。旧地重游,看到延安经过改革开放后的一片繁荣景象,回想起周总理抱病去延安的情景和总理的讲话,无比激动。敬爱的周总理把毕生精力和心血都献给了党和人民,始终同人民保持着血肉联系,深受人民的衷心爱戴。正像一首诗所写的那样:“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 总理和人民在一起,人民和总理心连心。”
一顿“丰盛”的早餐:
礼宾工作来不得半点疏忽
我在外交部没有参加过礼宾工作,但通过多年的观察和实践,深深感到,礼宾工作在整个外交工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乍看起来,礼宾工作非常具体、单调甚至有些琐碎,实际上,这些具体、单调甚至琐碎的事务正是完成重大外交任务所必不可少的,它需要有很强的政策性、细致的工作作风,更需要有高度的责任心,稍有疏漏,便会造成误会,甚至产生很坏的对外影响。
1964年9月底,越南总理范文同率党政代表团访华并参加新中国成立15周年庆祝活动。离开北京后,由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陪同到上海、杭州、南宁参观访问。当时负责此次接待的是国际司一位副司长和亚洲司一位处级干部。我作为年轻翻译,也参加了全程的接待工作。这次接待去外地的绝大部分交通工具是专机,只是从上海到杭州一段,出于好客,做了特殊安排,改乘专列火车。按计划安排,客人们将于10月4日上午8时离开上海,乘专列只需一个多小时,宾主在火车上用早餐,可以一面品尝上海的风味小吃,一面领略铁路沿线的江南风光,别具一番情趣。客人们对这一安排表示非常满意。为此,上海锦江饭店的厨师做了精心准备。
4日上午,客人们准时离开上海,在车站举行了隆重、热烈的欢送仪式。专列上也布置得美观、整洁。罗贵波和范文同在车厢正中位置就坐。火车启动后,宾主愉快交谈,准备品尝丰盛的早餐。但十多分钟过去了,仍不见服务员端来早餐。礼宾官员赶忙去催问专列服务员,对方却答称未听说要在专列上用餐一事。这时,负责具体落实早餐的那位亚洲司处级干部猛然想起,原来头一天晚上他忘记了通知锦江饭店,要提前把早餐送到列车上。在无奈的情况下,罗贵波指示,看看专列上有什么现成可吃的东西。但列车长说只有少许大米、咸菜和几个生鸡蛋。于是决定临时熬大米粥,现煮鸡蛋。又过了约20分钟,服务员在范文同和罗贵波面前摆上了两碗大米粥、一碟咸菜和几个煮鸡蛋。其他客人和陪同人员只得“买参观票”了。客人们照样谈笑风生,若无其事。但面对现场的情景和气氛,中方接待人员的尴尬真是难以言状。那位当事的处级干部更是悔愧交加,回北京后主动写了书面检查。听说当时正在上海的李富春副总理得知此事后,还发了脾气。
类似的礼宾差错,我还见证过几起。我想,外交工作就像一部机器,而礼宾工作则是这部机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机器的各个部件都能正常运转,不发生故障,才能生产出优质的产品。
难忘的出差感受:
内宾被当成外宾接待
1974年秋,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阮友寿在出访亚非国家后,经北京回国。为体现我国对越南抗美斗争的坚决支持,外交部领导经请示中央,决定对阮友寿一行给予高规格接待。按照接待计划,亚洲司一位副司长带领我和礼宾司一名干部前往新疆乌鲁木齐迎接。总的说来,任务完成得很顺利。新疆革委会主任赛福鼎同志出面宴请了客人,气氛热情友好。在乌鲁木齐,我们还争取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到百货公司看了看,想买点新疆特产。但当时国内各种日用商品都十分匮乏,谁知新疆的商品供应比北京更困难,买东西不仅要凭票证,即使有票证也不一定有货。只见百货公司的柜台上用红绿纸写着“红糖白糖都没有”、“香皂肥皂都没有”,意在告诉人们不要白花费时间排队。
那时交通还很不发达。虽然外交部派了三叉戟专机去迎接客人,但我们三人临去时仍须乘坐班机,中途要在兰州和哈密降落两次,而且要在兰州过夜。甘肃省外办的同志对来自外交部的我们十分热情。亚洲司副司长问他们都接待过哪些国家的外宾,外办负责人坦率地说,还没有接待过外国人。于是他们便把我们三人当做了外宾来接待,除安排参观和宴请外,还请我们到体育馆观看了一场杂技表演。一般说来,请客人在体育场主席台就坐,规格就已经很高了。但外办领导认为坐在主席台还不够高,于是在圆形的体育场里特意为我们三人摆放了一张长桌,上面铺有白桌布,放有茶杯。演员们就在我们身旁表演,让四周的群众一边看杂技表演,一边看我们三人,弄得我们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既尴尬又难受。就这样一分一秒地熬到了演出结束。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非常感谢甘肃省外办的同志,是他们给了我们一次难忘的出差感受。
当翻译不容易:
需要博闻多识
我刚参加工作时,外交部有一个“翻译室”,那里集中了英、法、俄、西班牙和阿拉伯五种语言的高水平专业翻译,专门负责为中央领导人做口头翻译和重要文件的文字翻译。我们学亚非国家语言的干部都分配到各地区司,虽不是专职翻译,但也不时承担一些翻译工作。几十年来,我曾有机会为周总理、邓小平、谭震林、陆定一、乌兰夫等领导人和巴金、华君武等文化名人当过翻译。更多的是在中越两国陆地边界谈判和划分北部湾谈判中,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当翻译。
对于如何才能当好翻译,不少老同志都谈过他们的亲身体会。我的一点粗浅体会就是除了要熟练掌握所学的外语,还要尽量多读书,多掌握各方面的知识。这样在翻译现场才能比较主动,才能尽量少出现尴尬局面。在这方面我可以讲三件事。一件事听来的,一件事是现场见证的,一件是我的亲身经历。
1975年夏,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和夫人访华。毛主席在会见马科斯总统夫妇时,谈及了当时的个人心态,说国内有人攻击他,称他为秦始皇。机敏的马科斯总统立即宽慰说,菲律宾有一条谚语:哪棵树遭人抛击的石子越多,就说明那棵树结下的果实越丰硕。接着,马科斯问,不知中国有没有类似的说法。毛主席脱口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这几句话原出自于三国时期魏国人李康的《运命论》,但在场的翻译从未听说过,更不懂是什么意思,一时不知如何翻译。毛主席只好把这几句话写在纸上,逐句给翻译讲解,才算解决了问题。
1975年的一天,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宴请越南驻华大使阮仲永,我担任翻译。阮大使在交谈中提到越南有很多人都喜欢中国的唐诗。韩念龙说,中国把古代最伟大的诗人称为“诗仙”、“诗圣”或“诗伯”。接着便讲述了一个故事,说中国宋代有一个书生,他在一个月夜乘船游采石江,忽然看见有一条船迎面划来,船上挂有一个牌子,上面写有“诗伯”二字。书生感到船上的人过分狂妄,便即席吟诗两句:“谁人江上称诗伯,锦绣文章借一观。”花音未落,只见对面船上有人答称:“夜半不堪提绝句,恐惊星斗落江寒。”书生听了大惊,急忙把船靠上去想当面求教。谁知那人下船后便消失在夜色中,没了踪影。原来是李白显圣。当时我对韩念龙引用的几句诗闻所未闻,精神立即紧张了起来,故事虽听懂了大概,但由于卡在关键的诗句上,一时惊慌地愣在那里,不知所措。韩念龙耐心地把几句诗写在纸上边讲解,边让我慢慢翻译,总算给我解了围。事后,我在冯梦龙的《警世通言》中读到了这个故事。如今几十年过去了,但当时的狼狈相在我的记忆中却怎么也抹不掉。
1989年秋,江泽民总书记在北京宴请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那时,江泽民同志刚到中央工作不久,同西哈努克还不很熟悉,席间便对西哈努克自我介绍说,我是江苏扬州人。接着又说,中国的诗词中提到扬州的地方很多,并当场背诵了李白的两句诗:“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在场的柬语翻译很快把这两句诗翻译了过去。但江泽民同志从西哈努克的表情中意识到客人可能没有听懂,便问翻译“烟花”一词是怎样翻译的。翻译说,他理解“烟花”是妓女的意思。江泽民马上纠正说,“烟花三月”是描写三月的扬州烟雾迷蒙,繁花似锦。那位翻译当然很不好意思,又把“烟花”的含义重新翻译了一遍。
从以上事实说明,虽然一名翻译不可能什么都懂,但不断扩大知识面,不断充实自己,始终是一名外事翻译的任务。
美国驻越大使彼得森:
曾经的战俘也能当大使
我担任驻越大使期间,同其他国家的使节有过不少交往。他们的身世大都是职业外交官,也有几位来自东南亚国家的使节,是军界人士,而美国大使则是一名曾经的越战战俘。
1995年5月,越南同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97年7月,美国首任驻越大使彼得·彼得森抵达河内赴任。外电对他的“戏剧性”身世做了颇多报道。
彼得森大使时年61岁。他出生在佛罗里达州一个工人家庭,在家中十个孩子中排行第九。越战期间,彼得森在美国空军中服务,曾多次执行轰炸越南北方的任务。1967年9月的一天,当他第67次驾驶飞机准备轰炸越南北方一条铁路时,被越南防空部队发射的导弹击中。他立即跳伞逃命,但降落伞挂在了一棵芒果树上,结果他摔在地上,腿部、肩部和手臂骨折。越南民兵发现彼得森时,他正躺在树荫下,已昏了过去。民兵首先脱下他的皮靴,因为美国大兵光着脚便无法走路。就这样,彼得森成了战俘,被关在河内的监狱6年,直到1973年关于越南停战的《巴黎协定》签订后,才获释放。离开越南前,彼得森发誓永远不再返回这个“倒霉的地方”。然而,世事难料。回国后,彼得森仍在空军中服务。1981年转而经商。1991年至1996年是佛罗里达州民主党议员。1995年5月,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名彼得森为美国首任驻越大使。彼得森赴任抵达河内机场时说,这是他第二次来到越南,但第一次来时没有“护照”。他说:“我相信,我们将不再彼此视为过去的敌人,而当做是好朋友。”不久,他同澳大利亚驻越南使馆的越裔女商务参赞结婚,并在河内举行了颇为隆重的婚礼。
彼得森和我是同龄人,他的经历引起了我的兴趣。越战期间我曾在中国驻越使馆工作过5年,对美国飞机轰炸越南北方的情况记忆犹新。我很想了解这位曾经的战俘,在大使的岗位上如何同他曾经的敌人进行交往。奇怪的是,他的表现出乎我的意料,到任后既不像其他国家的新任大使那样前来拜会,在各种外交场合也从来不主动打招呼。
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使用导弹袭击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使馆馆舍严重破坏和人员重大伤亡。5月10日,彼得森来到中国大使馆,向我面交了一封以他个人名义的慰问信。信中说:“上周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被北约军队误炸,对于由此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悲剧性的损失,我表示最大遗憾。我想向你特别向这次可怕事件的受害者家属,表达我个人和所有美国人最深切的慰问。”我严厉批驳了他信中所谓“误炸”的说法。彼得森没有反驳,只说“中国政府和人民有充分理由对此表示愤慨”。这次会面不到一刻钟,气氛可想而知。不知什么原因,从那以后,彼得森的态度有了些变化。
2000年2月上旬,越南总理潘文凯为各国使节举行新春招待会。彼得森夫妇主动走到我面前说,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在不断发展,我们两人在河内没有理由不加强交往,希望今后能经常就各种问题交换意见。我表示同意他的想法。3月上旬的一天,彼得森在官邸宴请我夫妇和另外五六对其他国家的使节夫妇。他把我和夫人安排坐在长桌的中间,与他夫妇面对面。整个宴会中,也基本上是他同我交谈。我告诉他,30多年前我在越南留学时,就住在他官邸的隔壁,门牌12号,他官邸的门牌是14号。彼得森说,这样看来我们早就是邻居啦!他表示希望在河内的中美两个大使馆加强交往。我说,我的同事告诉我,每次到美国大使馆,进门手续都非常繁琐,要穿过好几道安全门,这样我去美国大使馆就不方便啦。彼得森说,这一点还要请大使阁下多多谅解,美国人在越南的处境与中国人完全不同,安全上不能说已有了保证,因此必须采取一些防范措施。至于大使阁下,您什么时候到美国大使馆,我一定提前到大门外迎接。我说,最近美国国防部长科尔访问越南,希望能安排时间给我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彼得森说,已经有好几位大使有这样的愿望,他将安排时间把他们一起请来。我表示也愿与其他几位大使一道前来。但彼得森说,对中国大使,他一定要亲自到中国大使馆做单独介绍。不久,他果真来到了中国大使馆。
4月下旬,我在使馆新装修的客厅宴请韩国、澳大利亚、奥地利、以色列和美国大使夫妇。彼得森夫妇提前到场,还带来了一瓶美国红酒。由于是多边活动,没有单独同彼得森更多交谈。整个宴会气氛友好,还拍了几张照片。
2000年7月,我结束了在越南的4年半的任期回国。遗憾的是未能请彼得森谈谈他这个战俘是如何当上大使的。
(责任编辑#8195;谢文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