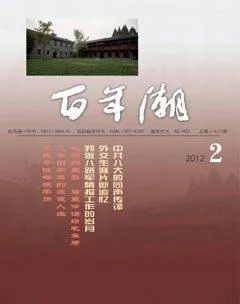法学大家马克昌
马克昌(1926—2011),河南西华人,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与中国人民大学高铭暄教授合称为中国刑法学界的“北高南马”。从教61年,所培养的大量高级法律专业人才,被海内外称为法学界的“马家军”。作为辩护律师,参与上世纪80年代初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审判,令世人瞩目。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特约咨询员,多次参与刑法修订的研讨咨询工作,临终前仍关心着刑法第八次修正案的出台,并且对这次修正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2011年6月22日在武汉去世,享年85岁。
2011年初,马克昌在病房接受央视《大家》栏目专访,讲述自己的法学人生。言谈举止间,充满了对中国法治进步的热情与期待。
“出庭就要像个律师,
该辩的就要辩”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马克昌的名字并不熟悉,但正是这位老人,30年前曾参与了一场举世瞩目的特别审判。
1980年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案件即将开庭,尽管这个消息举国皆知,但当时任武汉大学法律系副教授的马克昌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会与这场举世瞩目的特别审判联系在一起,更没想到自己会成为辩护律师组的成员之一。
记#8195;者:让您去参与这样一场审判,您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马克昌:要说很大的内心冲突,当时也没有。中国的政治形势变化很大,可以说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别人就担心,参加这个辩护,万一形势再发生变化,你年龄这么大了,又再吃亏,那就划不来了。
记#8195;者:那时候您已经50多岁了吧?
马克昌:54岁。在那种情况下,有些同志就不愿意干。但是我没有这样想。我认清了形势,“四人帮”这伙人祸国殃民,可以说是天怒人怨,不可能翻过来了。所以,我没有丝毫的顾虑。
接到参与案件审判的通知时,距离马克昌恢复工作不到两年的时间。在这之前的20多年里,武汉大学法律系被撤销,马克昌也被打成“右派”,先是被下放到农村劳动,之后回到学校的伙食科当出纳,最后被调到图书馆当了17年的图书管理员。但当受命担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辩护律师时,马克昌表现出了法律工作者极高的专业素养。
记#8195;者:对于您个人来说,正是因为他们,最宝贵的20多年的青春年华都被浪费了。国家的命运也遭受了重大的挫折。您在给他们辩护的时候,内心难道不会觉得很矛盾吗?
马克昌:那还是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不能感情用事,还是要理智一些。
记#8195;者:某种程度上,您觉得自己代表的不仅仅是自己,是这个国家法律重新恢复了尊严的时刻的到来。
马克昌:对。别人当然也说,他们那么坏,你们怎么还替他们辩护呢?也有人骂,这些人竟替那些坏人说话。当时,我们考虑,他们再坏,但他们有些权利自己不知道、不会维护,我们作为法律人,应当依法对待他们,该维护的还是要维护,不应当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在开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之前,1979年我国颁布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第一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这两部法律也成为了审判“两案”主犯的法律依据。在讨论完起诉书之后,马克昌被指定为被告人吴法宪的辩护律师。
记#8195;者:您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吴法宪时的情景吗?
马克昌:那大概是1980年11月16日,我们到秦城监狱去看吴法宪。进秦城监狱手续很严格。监狱长介绍了“两案”主犯每一个人的情况,然后发给我们一个牌子。监狱长一再交代,这个牌子要好好保存,不能丢,丢了就出不来了。我们一听,这可严重了,出不来住哪里呢?所以我们就一直很注意保护那个牌子。吴法宪被领出来后,我和周亨元一块和他谈,大意是说:现在我们当你的律师,你同意不同意?如果同意,请你写一个条子,说同意马克昌、周亨元为辩护人。吴法宪马上写了条子,递了给我。我一看,这一笔字写得相当漂亮。过去宣传说吴法宪是草包,我感觉是有点冤枉他了。单从这一笔字来看,他就绝不会是个草包。
记#8195;者:吴法宪当时没有任何排斥的情绪?
马克昌:没有。吴法宪不想死,很配合。我们向他交代,起诉书上控诉的罪行,究竟承认不承认,事实情况如何,要如实说,这是犯人的权利。
1980年11月20日,是新中国历史上有着特别意义的一天。这一天,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马克昌作为辩护律师之一坐在法庭的辩护席上,而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律师在我国第一次公开集体亮相。在法庭上,公诉方宣读了对“两案”主犯的起诉书,提起公诉后,法庭宣布十名被告人分别由第一审判庭和第二审判庭审理。
11月23日,特别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判被告人吴法宪。马克昌和另一位律师周亨元一起作为吴法宪的辩护人出庭。
记#8195;者:您给吴法宪作辩护,辩掉的罪行有几条?
马克昌:辩掉的罪行,有两条最为重要。一个是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分裂国家。那是真正的反革命罪。但事实上,吴法宪对此并不知情。我们当时问他知道不知道林彪准备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事情,他说不知道,现在才听说。所以,我们就在法庭上说,吴法宪根本就不知道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事情,肯定没有参与这件事。后来,起诉书中就没有再提这条罪行了。
记#8195;者:对这一条,还有什么证人、证据吗?
马克昌:江腾蛟可以证明这一点,他是当事人。江腾蛟交代,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是他和林立果等人一块商量出的第二套方案。江腾蛟明确说,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他们几个人不知道。既然不知情,这个罪就不应当给吴法宪安上。
另外一条罪行是暗杀毛主席。当时,吴法宪为表对林彪的忠心,把林立果调进空军,并指示空军,林立果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林立果利用这个权力,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建立了反革命组织,叫“联合舰队”,而且搞了一些特务器材,组织进行暗杀毛主席的一些活动。起诉书上把这些问题也算到吴法宪头上。我们当时问吴法宪,你交权以后,林立果进行的这些活动,你知道不知道?吴法宪说不知道。当时也没有确切证据证明吴法宪知道林立果的这些活动。所以,暗杀毛主席这一条后来也去掉了。
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十名主犯的审理,一共历时两个月零五天,共开庭42次,出示证据873件,出庭作证的证人有49人,有6万多人次参加了旁听。
记#8195;者:法庭辩护结束后,好像还有人发出惊叹,说还真的是辩护。
马克昌:对,对。有一些听众说,这还是真辩护了。
记#8195;者:听到这样的话,您心里是什么感觉?
马克昌:我当然高兴了,这正是我的主张。我们律师在讨论的时候,大家意见不一。有人说,这都是国家定下来的,我们到那儿去,不就是做做样子吗?只要外国人看到中国还有辩护律师,就达到目的了。我是不赞成的这个观点的。我说,既然让我们来辩护了,那出庭就要像个律师,该辩的就要辩。
记#8195;者:其实您真正维护的,不是哪一个人,而是法律的尊严。
马克昌:对,对,还是维护法律的尊严。
1981年1月25日,特别法庭开庭宣判,被告人吴法宪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这一天,“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这一历史性的世纪审判也到此结束。
记#8195;者:今天回过头来看,您怎么评价当年那场特别辩护?它的特别意义在哪里?
马克昌:我认为,“两案”审判是我们国家的进步。现在看来,这次审判也有不少地方值得反思。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次审判是一个里程碑,是我们建设法治国家、走法治道路的里程碑。
记#8195;者:为什么?
马克昌:此前的一些政治案件,很少说公开审判,更谈不上让律师辩护。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所以说它意义重大。
“希望自己教好法律,教好刑法,
让学生树立法治观念”
担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辩护律师是马克昌一生中最受世人瞩目的时刻,而他真正的身份是一名研究刑法的学者。
1950年,马克昌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律系。由于学习成绩突出,深受法律系主任韩德培教授的赏识,留校任教。不久他又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攻读刑法学专业的研究生,师从苏联刑法学家贝斯特洛娃研究刑法理论。
记#8195;者:您那时候是新中国第一批刑法方面的研究生?
马克昌:对,那是新中国第一届研究生,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
记#8195;者: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刑法方面的研究生,您当时对自己的未来,包括对这个新的国家的未来,期待跟过去应该不一样吧?
马克昌:那当然不一样了。既然学习法律,就希望我们能够建成一个法治国家。当时具体的想法,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教好法律,教好刑法,让学生树立法治理念。
那时,年轻的马克昌对自己和国家的未来都充满着希望。研究生毕业后,他回到武汉大学,担任法律系讲师。但是,随后而来的反右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让他的人生和学术生涯受到了极大的挫折。
直到1979年,53岁的马克昌受命与老师韩德培教授一起,重建武汉大学法律系。1980年,武汉大学法律系正式开始招收本科生。
鲍遂献(马克昌指导的首届博士):1980年武汉大学法律系刚刚恢复重建,第一届招收了60个学生。讲课的都是一些大家,包括马老师都亲自在一线为本科生授课。我们这一届学生,从这些老一辈法学家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们严谨的作风,他们的学识,对我们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
1991年,65岁的马克昌申请卸任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让人们没有想到的是,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马克昌书写了他学术生涯中最为精彩的篇章。
十年时间,他相继出版了《犯罪通论》、《刑罚通论》、《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比较刑法原理》等十余本著作。
而所有的著作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昌2002年出版的专著《比较刑法原理》,这本著作由刑法基础理论、犯罪论和刑罚论三部分组成,是一部全面系统研究西方刑法理论的专著。同行们认为,这是目前我国比较刑法研究最权威的范本。
从1998年开始,72岁的马克昌开始动笔撰写专著《比较刑法原理》。80万字的书稿,一个字一个字地工整地写出来,一共写了四年。一尺多高的稿纸,凝聚了马克昌一生的学术积累。这部著作出版时,他76岁。
莫洪宪(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他当时是爬格子,一格一格那样爬出来的。所以,这本专著出版的时候,我们这些已经毕业的博士生,现在在高校任教的老师们说,看了这本书以后,我们没法活了。我们觉得导师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专注地做学问,对我们年轻人来讲,压力很大。我们更应该像先生一样,把自己的毕生精力,投入到教学科研当中去。
2003年,《比较刑法原理》一书获得第六届国家图书奖,这也是当年法学界唯一获奖的书籍。
高铭暄(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马克昌教授是我素来尊敬的一位刑法学家。他功底深厚,兼通中国、外国,不仅对中国刑法学有很深的造诣,同时对外国刑法学,特别是大陆法系德国、日本刑法学,也是非常熟悉的,而且有深入的研究,可以说是新中国刑法学的奠基人之一。
“逐步减少死刑,
但现在还不能废除死刑”
在从事刑法理论研究的同时,多年来马克昌一直积极参与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工作。1997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决定对1979年颁布的刑法进行修订。马克昌作为专家受邀参与讨论。
记#8195;者:您觉得在1997年这次刑法的修订当中,哪些修改是最重要的?
马克昌:有几个原则的改变应该说是最重要的。其中一个,就是废除类推,改成罪行法定。
记#8195;者:这是什么意思?
马克昌:简单地说,就是法律没有规定的,就不能定罪处罚。
刑法面前人人平等也是一个重要原则。
再一个就是罪责刑相适应,过去一般简称罪刑相适应。意思就是说,刑罚的轻重不仅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相适应,而且也与犯罪分子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记#8195;者:加一个“责”字有什么意义呢?
马克昌:因为光说是罪,就是犯的罪大罪小的问题。但是嫌疑犯后来坦白了,交代了,又检举了,又立功了。这就减轻了他的责任。所以,加一个“责”字,就要求法官判处刑罚时,不仅要看犯罪的客观社会危害性,而且要结合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把握罪行和罪犯各方面因素综合体现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实际上我们国家也是这样做的。嫌疑犯立了功,不是就会判轻一点吗?
这几个大的原则都是非常好的,体现了我们国家法治进程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新刑法出台后不久,就我国现阶段是否应该取消死刑的问题,国内许多学者产生了争议。对此,马克昌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记#8195;者:这些年来,死刑是否应该取消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您的态度是什么?
马克昌:我主张逐步减少死刑,但现在还不能废除死刑。这是我的基本观点。废除死刑是各国发展的一个趋势,而且联合国人权公约,也主张能废除死刑的尽量废除死刑。在没有废除死刑的国家,也只能对极其严重的罪犯判处死刑。
记#8195;者:您觉得不轻易地判一个人死刑,是不是体现了对生命权的尊重?
马克昌:是。这是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标志。
记#8195;者:为什么您觉得中国现在废除死刑还不具备条件呢?
马克昌:首先是因为中国有自身特别的传统。“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中国老百姓的一个口头禅。“杀人者死”是中国文化沉淀在人们思想习惯中的观念,要想改是很难改的。再一个原因,中国很大,而且社会治安的状况一直也不理想,一旦废除死刑,有些老百姓会受不了,可能引起一系列后果。比如:你把我家里人杀了,你不会死,那好,我也杀你家里的人,反正我也判不了死刑。这样社会秩序就很难维持。所以得等人们的文明程度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逐步废除死刑。
熊选国(马克昌曾指导的博士生): 1997年刑法修订之后不久,马老师就提出要完善死刑核准制度,把死刑核准权收到最高人民法院来。这样就等于说,马老师在死刑问题上,从观念到实体程序都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应该说都是比较符合中国国情,也符合我们现代法律制度的。
最近几年,在国家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马克昌认为应将“宽严相济”作为我国基本的刑事政策,并在理论上对其进行了系统论证。在他的呼吁和推动下,刑法理论界、刑事立法和司法部门基本达成了共识,将宽严相济作为基本刑事政策贯彻到立法、司法和执法实践中。
“我们国家应当是打击犯罪和
保证人权并重”
国家法治的进步和发展是马克昌一生的理想和追求。对于未来,他说,希望我们的刑法能逐渐从国家刑法走向市民刑法。
记#8195;者:我看到您提出了一个观点,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您的一个理想,就是从国家刑法到市民刑法。
马克昌:是我的一个愿望,一个理想。
记#8195;者:该怎么样理解您的这个观点?
马克昌:国家刑法实际上可以叫做权威刑法,它对人民的自由、人权是不怎么强调保护的,强调的是保护国家利益。市民刑法就跟它有点相反了,强调保障人权,保障自由,当然也维护秩序。总的来讲,市民刑法对人权自由考虑得更多一些。我们国家应当是打击犯罪和保证人权并重,既要打击犯罪,还要保障人权,这样我们国家才能慢慢走向文明。
2010年7月,马克昌因病住进医院,虽然身体非常虚弱,但他依然在病房里构思撰写下一本著作《百罪通论》。
李占洲(马克昌指导的博士):马老师为了写好这一部分的罪名,每天都翻阅大量的资料,包括一些案例。又经过很深入的思考,才开始动笔,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在纸上。马老师对学问认真细致严肃的态度,让我们非常感动。
2011年6月22日晚19时16分,武汉大雨滂沱,马克昌先生在这一刻悄然远去,享年85岁。得知这一撕裂人心的消息,不禁想起采访结束后马克昌先生在《大家》栏目的留言簿上写下的“促进学术繁荣,弘扬民主法治”这句话。这既是他对《大家》栏目的鼓励,更是对中国法治建设的美好期望。任重而道远,我们尚需努力,相信这是对先生最好的怀念!
(本文素材由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提供,节目播出时间:CCTV-10每周六22∶10,周日7∶45、16∶55)
(责任编辑#8195;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