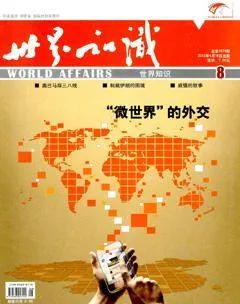“超级代表”真的管用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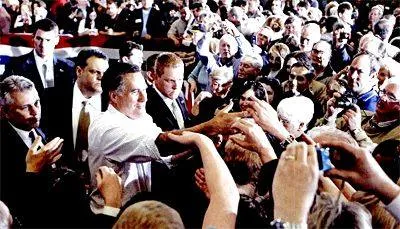
面对新一轮调整,“超级代表”到底何去何从,可谓是未来观察美国选举政治走向的一个重要看点。
4月3日,马里兰州、成斯康星州以及华盛顿特区三场初选揭晓,罗姆尼轻而易举地将三地收入囊中。至此,共和党2012年总统候选人提名程序已决定了1193位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归属,超过全部代表数2286的一半。当赛程过半之际,即便罗姆尼在代表数量和竞选经费上都远远超过了党内其他候选人,但共和党仍旧无法及早终结“内耗”,只能期待4月24日桑托罗姆在家乡宾夕法尼亚州落败后退选的可能,或者要等到6月5日产生172个代表的加州初选后才能明朗。
虽然普通民众分歧仍然鲜明,但共和党精英层早已心有所属,从资深大佬老布什家族到“茶党”少壮派人物马尔科·卢比奥、保罗·瑞恩,都纷纷公开为罗姆尼背书。而在罗氏所得到的代表票中也包括32票的“超级代表”票。根据统计,罗姆尼目前得到了所有已产生代表票的54.3%,而其中竟然拿下了86.5%的“超级代表”票,党内精英对其的支持力度可见一斑。不过,旨在“同业审查”的这种“超级代表”方式因2008年民主党初选恶斗而遭遇改革,目前已无力化解共和党这场初选拉锯内耗了。
“超级代表”的兴起
“超级代表”制度安排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是与现代初选制度相伴而生的。由于缺乏党内精英和民选官员的参与,完全依靠普通民众选举产生的总统候选人不尽人意。同时,缺乏政党官员等华府圈内人支持的候选人即使能够获得总统职务,在上台后也很难形成党内有效联盟来共同处理国家事务。为了改变这样的负面状况,1982年民主党高层组建了亨特委员会,推动大幅度增加了政党领袖、党内民选官员、各州党组织和政府官员的代表席位,形成了一群所谓的“超级代表”。设立“超级代表”的初衷,除了提高这些政党精英与官员的投票积极性,更重要的用意是希望依靠党内精英的政治判断与经验对全国党代表大会所产生的缺失进行有效的纠正。
亨特委员会改革之后,民主党的“超级代表”规模呈现逐年递增趋势,所占比重也越来越多,从1984年的14.4%(568位)增长到2008年的19.3%(853位)。以2008年为例,当时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4233位代表中,除了3253位由初选产生的承诺代表外,853位“超级代表”由国会议员、民主党内高级官员、州长、前总统和前副总统组成。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支持任何一名候选人,因此也被称为“未承诺代表”。与民主党相同,共和党也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跟进了相应改革,如2008年2380位代表中存在463位“超级代表”,占比19.4%,超过了民主党。
在现实的初选政治运行中,不足总数20%的“超级代表”发挥着超过其比例的实际影响力。比如,他们可以在初选前就表态支持某位候选人,从而提升后者的知名度与曝光度;又如,在没有承诺的约束下,他们可能在整个选举过程中根据候选人的表现而不断改变自己的支持对象,进而对普通选民产生潜移默化的左右;最为重要的是,“超级代表”可能在候选人均未获得半数以上承诺席位的特殊时刻最终决定提名,比如在1984年和2008年的民主党初选中就是如此。
“超级代表”的争辩与调整
“超级代表”制度已推行了30年,虽争论不绝于耳,但的确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自初选制度确立以来,政党的影响力日趋下降,初选从以“政党为中心”转变为“候选人为中心”。随着初选制度向普通公众甚至是非本党支持者敞开大门,提名总统候选人不再是政党内部的“家务事”。只要有志于问鼎白宫的候选人都可以参加党内初选,组建竞选团队,筹募资金,无需获得党内领袖们的推荐。初选制度让那些富有个人魅力且懂得个人营销的候选者占尽优势,他们可以利用充足的经费营造有利于自己的舆论氛围,利用良好的个人才华充分感染民众。为了赢得“媒体游戏”,候选人必须机智灵活、随机应变、富有魅力、口齿伶俐,但这些并非成为一个好总统所必需的首要素质。缺乏甄别机制,即缺乏“同业审查”或“同行评议机制”,则无法考察候选人是否具备当选总统所需的各种素质,这种考察通常是由其他政治活动家进行的,他们对候选人有真正的了解,自身也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政府的工作,并且知道评议结果跟自己密切相关。
2008年年初,曾参与制度草拟、并因1984年作为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而刷新美国女性参政史的杰拉尔丁,费雷罗曾在接受采访时,对“超级代表”这一“精英主义”制度赞赏有加。她的理由有三:其一,由于初选的投票率极低,所以其结果并不能够真正反映民主党的利益;其二,很多州的民主党允许采取开放式的选举,选民中可以有民主党人、中间选民甚至是共和党人,所以选民的投票结果并不能完全代表民主党的利益诉求;其三,候选人在拉票的时候为了迎合那些非民主党人的意愿,也不能完全代表民主党的利益。因而,“超级代表”才是民主党真正的“代言人”,他们应该站在政党立场去引领民意而非服从民意。
当然,也有很多政客和学者强烈反对“超级代表”制度,并极力希望两党取消这类“特权人群”。他们的理由极为简单而致命:“超级代表”违反了“一人一票”这一民主制度的最基本原则,即每个投票者都应该有相同的权利去影响投票结果,他们的意愿应该由承诺代表直接在全国代表大会上得到表达。
2008年民主党总统初选为围绕“超级代表”制度的争论提供了一个新答案,并引发了新一轮改革。在当年初选前夕,希拉里在“超级代表”中拥有极大优势,但出人意料的是,最终大部分“超级代表”转投到奥巴马阵营,在总共724位“超级代表”中就有478位支持奥氏,约占66%。“超级代表”的临阵倒戈,看似服从了民意的趋势,但事实上奥巴马在选民票上也仅仅微弱领先于希拉里,“超级代表”的选择无疑扩大了奥巴马的领先优势,俨然成为压垮希拉里的最后一根稻草,帮助民众作出了最终选择。正是因为在2008年民主党初选中“超级代表”的夸大作用,两党在2012年竞选周期中相继对其进行了压缩:由于民主党不存在竞争性初选提名,因而压缩幅度较小,保留了627位“超级代表”;而共和党初选因为事关能否夺回白宫的大局,因而仅保留了126位“超级代表”,由各州的共和党组织领袖出任。这是“超级代表”作为制度安排出现以来的首次压缩,或将是一轮新制度改良的转折点。
“超级代表”或再获重视
面对新一轮调整,“超级代表”到底何去何从,可谓是未来观察美国选举政治走向的一个重要看点。虽然在理念上遭遇攻击,但在具体选举实务运作中,“超级代表”到底发挥了何种作用,2008年的民主党初选中“超级代表”的决定作用应该如何评价呢?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和乔治亚州立大学的三位学者在2011年发表了基于2008年民主党初选“超级代表”选择逻辑的调查研究论文,其发现值得一提。在所有133名接受调查的“超级代表”中,有37%表示在初选进程中改变了自己的支持对象。当被问及改变的原因时,有超过1/4的人称因为他们觉得奥巴马是最终可以获得提名的人,毕竟奥氏获得了更多选民票。当然,也有约8%的“超级代表”称自己改变的原因是被奥巴马的魅力所打动。这一研究说明,当超级代表支持的候选人不能获得多数普通选民的支持时,他们可能会自觉调整来迎合大众的选择。
如此来看,既然“超级代表”难以发挥引领民意的作用,那负有“同业审查”使命的他们是否需要继续存在呢?美国俄勒冈大学的学者对此进行了一项模拟研究,即基于2008年民主党初选数据,将其换算为“取消‘超级代表’”、“胜者全得决定本州‘超级代表’倾向”以及“根据候选人选民票比例分配本州‘超级代表’倾向”等三种改革方式。几种模式计算对比之后发现,现行的“超级代表”方式与全部取消“超级代表”、仅由承诺代表选择的方式结果一致,并未主观改变民意选择;而在其他两种改革方式下奥巴马和希拉里都不可能超过半数,其势均力敌的胶着状态将被继续拖延,无法保证民主党初选顺利完成。从这个角度看,“超级代表”事实上维护了政党利益,平衡了分裂的民意。
从这两个研究的发现与结论观察2012年共和党初选时,如今的“超级代表”则陷入了极为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他们明显支持罗姆尼的倾向,并非是迎合党内的民意。目前,罗姆尼虽然在选民票和代表票上都遥遥领先,但其39.7%的选民票少于支持桑托罗姆和金里奇的保守派总和的47.7%,并非占据民意多数,因而“超级代表”的判断更像是精英的政治判断;另一方面,“超级代表”虽然因罗姆尼的胜算最大而坚持选择,但因被空前压缩,无法发挥任何决定性作用,无力加速党内整合。在左右为难的情况下,如果最终获得提名的罗姆尼被党内恶斗拖累而最终败选的话,“超级代表”制度或将再次获得适当的重视,回归2008年之前的扩张态势,围绕其的利弊之辩也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无法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