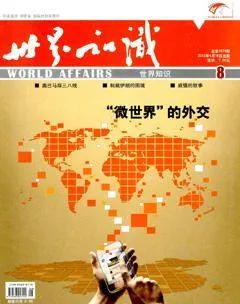不为人知的《战争与和平》
苏联时期有一位叫艾·叶·扎伊坚什努尔的学者在托尔斯泰博物馆经过仔细核对笔迹、对比墨色,整理出了《战争与和平》的手稿。这部手稿被认定为是《战争与和平》初版的原貌。这一研究成果引起了学界不小的轰动,于1983年被刊载在当时苏联著名学术研究资料汇编《文学遗产》上。
经过俄罗斯扎哈罗夫出版社资深编辑们审读、编辑加工并参考1873年的版本,2000年《战争与和平》初版终于问世。
《战争与和平》是一部关于人与命运的百科全书,展现了人性中的善与恶、爱与恨、生与死、智慧与迷误、战争与和平。《战争与和平》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其首个版本一直是学界争论之谜。想要探寻这个版本,还要回到19世纪60年代。
早在19世纪50年代,托尔斯泰想创作一部有关十二月党人的小说。为了追溯主人公青年时光,他将目光聚焦到1812年。托尔斯泰从1863年开始创作,到1866年完成。作品的前几部分以《1805》和《战争》为题发表在《俄罗斯通报》上,托尔斯泰想出版此书,但因为种种原因此愿未偿。而后他带着自己的手稿回到雅斯纳亚·波里亚纳庄园,继续进行艰苦的创作和反复的修改。
这部小说被公认为是一部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的史诗,热情歌颂了人民在战争中的巨大作用。但托尔斯泰本人在《战争与和平》的初版中却曾有这样一席话:
“迄今我只书写公爵、伯爵、部长、参议员及其后代,恐怕以后在我的历史中亦将不会有别的人。或许,公众会不喜欢;或许,对于公众来说农夫、商人、粗人的历史更有趣些,更有教育意义一些,尽管我全部的愿望是拥有尽量多的读者,但我不能迎合这样的趣味。”
这虽然令人难以置信,但确实如此。作者只是在《<战争与和平>尾声势中说,“我是在努力写人民的历史”,“在《战争与和平》里我喜欢人民的思想”。
托尔斯泰的创作思想的确发生着不断的变化。在写作生涯后期他曾深情地写道:“有个时期我曾经以自己的才智、门第自傲,现在我知道了,如果说我身上有什么好的东西,那就是一颗敏感而又能够爱的善良的心。”他就是用这颗心去体味人民的历史和思想的。
这部著作有一个重要的文学特色就是哲学的议论、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寻及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有些学者认为,《战争与和平》后来的版本中,“议论有时似乎与叙事本身结合得不够紧密,显得与艺术描写不够协调,而且某些议论前后重复,使人读起来不免觉得比较累赘”。
对于这个问题,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尾声》里说:“我的大多数读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读到历史的尤其是哲学的议论时,要看看这些议论在何处结束,于是翻过几页,继续读下去。我感觉对不起这些读者,因为我插进一些议论把书给糟蹋了。但在描写时我发现,这段历史不仅没有人知道,而且人们所知道的和所记载的与史实完全相反,于是我不禁感到必需证明我所说的话,必需表白我写作时所根据的观点。”而在1866年的初版中,“和平”的内容远远大于“战争”的叙述,因此也缺少了大量的议论,叙事比较连贯,更多地展现的是托尔泰作为艺术家的一面,而非哲学说教者的一面。
在人物命运的安排上,初版中安德烈在首次负伤时感受到的只是“如此强烈地爱这个生命”,“如果命运赐予这个可能”,会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去活,并且安德烈在书中活着。而在后来的版本中,安德烈死亡前体味到的是“爱阻止死。爱就是生。爱是上帝,死意味着爱的粒子回到永恒的本源”,“死就是从人生中觉醒”。这一主人公命运的改变表现出托尔斯泰对“死亡”这一人类永恒的终极命题的深深思索和感悟。初版中全书是以奥特拉德诺耶领地重新热闹、兴旺起来,并在同一天举办了两场婚礼作为结尾的,童话般美好的结局也体现着作者对旺盛的生命力的向往和追求。
考量《战争与和平》的初版,不难看出它质朴和“粗糙”的一面,但更为重要的文学价值是读者能够从中看到这位伟大作家原初的思想和未被影响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