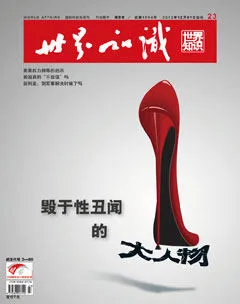发展中美关系必须增信释疑

经过几十年的交往,中美两国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双方的关系却依然脆弱、不稳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两国间一直存在战略互疑。
中美两位知名学者王缉思、李侃如合著的《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2012年3月在两国以中英文出版)直接针对这一问题,深入研究彼此对对方的认知,清晰、坦率地摆出各自对对方的怀疑,寻找其存在的根源,并为如何解决或减少相互战略怀疑提出了若干建议。
怎样看待中美间的战略互疑
对此研究成果,总的看,肯定的意见为多,但也出现了一些反对或是不赞成的声音。主要有三种,一是认为何必要把问题讲得那么明白,为保持两国关系发展,也许还是模糊点儿好。二是认为中美间本来就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战略互信,战略互疑才是两国的现实,双方应致力于管理两国竞争而非消除战略互疑。三是认为,从总体看,两国的“互疑”并非处于历史最高期,中美关系目前仍处于一种较好或相当好的状态,两位学者的观点似乎过于悲观了。
我不赞成第一种意见,因为无论是否有真凭实据,战略互疑确已成为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重大障碍。将这一长期以或明或暗形态存在的问题摆上桌面,不仅有益于逐渐改变两国政策中“两张皮”现象(当面讲合作,背后重防范)对政策执行带来的困惑,而且有益于两国对症下药,减少因理解和认识不够形成的误解。正视与有效应对两国间的战略互疑,将是两国关系走向成熟的重要表现。
我更不同意第两种意见。因为这显然有悖两位作者的初衷。建立中美战略互信的现实目标是做到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清楚了解对方底线,努力发展信任措施,并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积极开展合作。通过多年的交往与磨合,中美双方已经建立了一定的战略互信(甚至在台湾问题上也有所表现),只是还很不够。此外,对于中美关系来说,进行竞争管理、危机管理与建立战略互信,同样重要。如果只强调前者,显然对中美关系过于悲观,是将中美关系等同于当年的美苏关系;如果只强调后者,又过于乐观,超越了现实。从长远看,使后者发挥主导作用应是中美双方共同努力的方向。
至于第三种意见(以奥巴马政府前高级官员贝德为代表),在一定意义上我是赞成的。这种意见认为应更积极地看待中美关系,但遗憾的是,当前中美两国的许多人,包括一些重要的官员,并不这样看待,而是对中美关系持相当消极的看法。
加强军事交流,展开“小多边对话”
关于两位作者最后提出的政策建议(涉及经济贸易、军事战略、网络安全、小多边对话、公众情绪),我认为既中肯、务实,又很有见地。我仅就第二、第四这两点建议谈一点支持的意见。
首先,关于“军事战略”。长期以来,中美两军关系与两国其他方面的关系相比,明显滞后,战略怀疑深,合作少,并往往成为两国政治摩擦的牺牲品(两军交往曾被中止多达六、七次)。“三大障碍”(美对台售武、美舰机对华近岸侦察、美国内歧视性法律)和“三大差距”(两国军力差距、任务差距、体制差距)更使两军交流困难重重。然而,如果以辩证的观点看,在一定条件下,最薄弱的环节可能恰是最有潜力发展和最有可能突破的环节。因此,我非常赞成两位学者的建议,即以“有高层政治领导人参与,与各自军方一起”的方式来加强两国军事安全对话。我认为,两国军事安全对话的目标应是使双方误解逐步减少,使双方共同利益可以通过切实合作不断加强,并通过建立与完善危机管理机制和建立起有别于美苏、美俄之间的战略稳定机制,使双方确实存在的尖锐分歧(主要在传统安全领域)得到有效的控制。
其次,关于举行“小多边对话”。我认为,无论从改善中美关系还是从加强地区安全着眼,逐步、适时地举行一些包括中美在内的三边安全对话都是很有意义的,这样做既有益于减少国内对他国联合对付我们的担忧,又有益于扩大多边对话。此外,如果中美韩或中美日能举行三边安全对话,还可能为未来中国与美国双边开展军事同盟对话打开希望之窗。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同盟仍将长期存在,这是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当然,要使这些对话较快开展并取得成果很不容易,但这不应成为不作为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