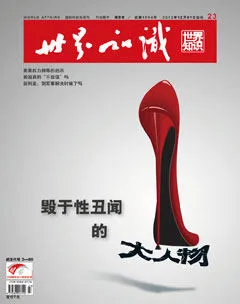最后的莫言
再过些日子,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将前往瑞典领奖,届时无疑将再次引起举世的关注。
莫言的获奖圆了中国人的一个梦。中国其实与诺贝尔文学奖蛮有缘的。早在1938年,美国女作家赛珍珠以《大地》一作获奖。这部作品的素材就取自邻近我家乡的皖北宿县。几十年后的2000年,一位名叫高行健的法籍华裔作家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但从各方反应来看,这位高作家的获奖实在是没有什么公信力。直至来自山东高密的莫言众望所归地摘取今年的奖项。
这是一位真正的中国本土作家获奖,其意义远非前两位可比。梳理中国近现代文学史,有资格获取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有很多,比如鲁迅、林语堂、沈从文等。但为什么偏偏是莫言而不是其他中国作家呢?这不能不提到莫言背后的一个人。在莫言获奖之后,许多行家都称,莫言能获奖,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她的努力。这个人就是瑞典翻译家陈安娜女士。
陈安娜开始翻译莫言作品大约是在1994年到1995年前后。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苔之歌》、《生死疲劳》等三本小说的瑞典文版译者均为陈安娜。最近的一本《生死疲劳》在哥德堡书展上被隆重推荐,这部作品陈安娜2006年就开始翻译,费六年之功,全稿修改至少七次,直至今年5月才出版。除陈安娜之外,另外一个功不可没的人是美国翻译家葛浩文。没有他把莫言的多部小说译成英文,莫言的影响力也难以进入西方。作为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国际级大师,数十年来,他已将莫言的十多部作品介绍给英语国家的读者。
翻译无疑成为中国文学作品走向世界的一个关键。因了陈安娜,莫言才被瑞典文学院认知,才有了今天莫言的辉煌。以著名的德国法兰克福书市为例,每年都有许多国家的书商和出版机构带着自己的作品参展。中国也曾有幸在前两年成为该书市的主宾国。但即便中国成为当年的主宾国,中国作品的影响力也非常有限。须知,在有“全球最大书展”的法兰克福书市上参展的,95%都是英文作品。除了华人之外,世界上有多少人能说汉语?又有多少人能读懂中文?中国作品再出色,没有翻译这个媒介,最终还是无法如愿走出国门,也就无法让更多的民族、更多的读者欣赏。翻译一直是、在很长时间内仍将是中国作品走向世界的主要瓶颈。
好歹有了莫言。当莫言获奖的消息传到国内,用“洛阳纸贵”来形容莫言作品的畅销程度绝不夸张,甚至还有所不及。这是莫言的幸事,但绝不是中国文学界的幸事。在读者和粉丝们纷纷涌向莫言作品专架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把目光同样投到其他中国传统文学作家的作品上呢?
这让我不禁联想起在德国的时候。乘火车长途旅行时,经常看见车厢里的旅客捧着一本简装书在静静阅读,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无人抽烟,无人喧哗,更无人打牌、嗑瓜子……
这就是德国,这就是欧洲。其实早在二三十年前的中国,也曾有过这样的读书型社会出现。那时的人们在刚刚走出了“文革”的文化沙漠之后,对知识的渴求是今人所难以想象的。尤其是青年,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读书:公交车上、校园的一角、昏暗的路灯下……
可惜的是,商品时代和信息化时代来得过于迅猛,对刚刚形成的读书社会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年轻人不再流连于书籍,而是沉迷于网络;学生不再为思想和理想读书,而是为考本读书……
理想在沉沦,信念在沉沦,文学在沉沦……一切为了生存。尤其是文学。难以想象,在书市萎缩、读者萎缩的情况下,文学还怎么生存?先是诗歌渐渐走入历史,继而是散文、是小说。后者还在挣扎,只不过换了一种活法:如果网络小说也能称为小说的话。
惟愿莫言的惊艳获奖不是中国文学的回光返照,而是中国文学重新复苏的信号。惟愿中国的作家继续在书斋中十年磨一剑,而不是成为电视剧的写手。
希望今天的莫言不是最后的莫言,希望中国的文学界还能向世界输出更多的莫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