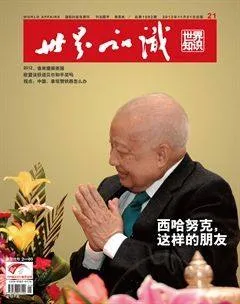选举的需要:“第一个是金钱……”

在美国民众当中,对“金钱政治”的厌恶和对更为彻底改革的渴望已渐成主流。
每到美国大选年,人们都会把美国大选中的金钱政治这个话题扒出来晒一晒。这一届美国大选已接近尾声,根据目前官方公布的数据统计,到今年8月,两党候选人所筹集的竞选经费已超过13亿美元。照此态势估算,2012年总统大选的两党候选人筹款或将最终飙升至20亿以上,仅奥巴马一人就可能超过10亿,进而再度刷新记录。正是因为这种几乎无限制接受大财团捐款行为的“横行”,为美国选举政治留下了关键一笔,也增添了美国金钱政治的又一层迷思。
金钱政治的扭曲
“金钱是政治的母乳”。1966年,加州州议会领袖杰西·安若这么一句不经意的玩笑,却因犀利而精准的表达而广为流传。事实上,回溯美国政治发展史,没有任何一场选举是不需要财力支持的。早在1757年,国父乔治·华盛顿竞选弗吉尼亚地区议员时,就曾购买了29加仑郎姆酒、50加仑郎姆饮料、34加仑葡萄酒、46加仑啤酒以及2加仑苹果酒充当竞选物资。1896年和1900年两度辅佐威廉·麦金莱当选总统的竞选经理马克·汉纳更是不加掩饰地坦言,“要赢得选举,需要两个东西,第一个是金钱,第二个我就记不得了”。
长期以来,由于美国民主制度下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的天然链接以及选举制度与过程对巨额资金的旺盛需求,金钱俨然是美国政治舞台上多元利益之间的润滑剂与关系链,呈现出无法控制的恶性膨胀。根据学者和民间智库统计,2008年整个选举周期的总开销约为31.25亿美元,是1976年的17.6倍,其中以总统大选开销最为惊人:从1976年的6690万美元窜升至2008年的17.59亿美元。如果将这32年中的通货膨胀率考虑在内,总统竞选经费激增了约9.5倍。当通向白宫的跑道上被铺满了黄金之时,是“驴”还是“象”最终染指总统宝座已并不那么重要,最大的赢家都是某些特殊利益诉求的垄断经济精英而已。而“金钱选举”的常态化,无疑消磨了美国政治的理性,侵蚀着公众的长远利益。
首先,金钱政治对大选结果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扭曲。能让普通选民知晓某候选人、博取知名度,就是获得其投票支持甚至胜选的基本砝码,而这恰恰需要财政投入才能实现。笔者曾在2008年大选前夕分别走访过美国西部蒙大拿州米苏拉县的两党竞选站。奥巴马这厢门庭若市,义工众多,且所有竞选材料均供随便领取;而麦凯恩那边却门可罗雀,只有一位学生实习生当班,连一枚竞选胸章都要捐出五美元后方可带走。如此明显的财力差距,基本已可铸定输赢。同理,金钱在今年共和党初选中也发挥了巨大的“魔力”。金钱帮助奥巴马和罗姆尼如愿以偿,但也留下了无法弥补的后果:前者是美国公众迟迟等不到所谓的“奥氏变革”,后者是共和党只能接受一位只会讨好选民而无坚定政治立场的骑墙候选人去挑战奥巴马。不得不承认,金钱令选民作出了未必最佳的选择。
其二,金钱政治导致在内政外交决策中大量的利益交换。金钱对选举政治的牢牢控制,使得候选人的选区概念凸显异化。他们不仅要代表其所在选区(或全国)选民的利益,还要兼顾所谓的“金钱选区”,即那些垄断资本的利益。从美国政治经济的地缘分布上看,美国东海岸的新英格兰—纽约地区、西海岸的加州地区、中西部的五大湖地区以及南部的得州地区等皆为“金钱选区”。在双重选区的约束下,当选总统不仅要依照国家利益与民众福祉来制定内外政策,还要尽可能地符合寡头经济精英的特殊利益偏好。比如,近年来的三位共和党总统里根、老布什以及小布什均不同程度上接受了石油等能源公司的巨额捐助。作为回报,里根任内推动取消了对石油、汽油等的价格管制,而布什父子则先后发动了两场伊拉克战争,最终将这个石油储量世界第五的国家控制在手。民主党方面的情形如出一辙,克林顿和奥巴马均接受了更多IT信息科技产业的财政支持,前者上任后积极推动信息高速公路等计划,吹起了美国“新经济”号角;后者则极为重视网络传媒的发展普及,身体力行地将其使用于政治动员与竞选当中。
其三,金钱政治甚至还令买官鬻爵在当今美国变成现实。在金钱政治的庇护下,某些捐款人的确能够通过给总统候选人较多数额的钱财,拿到挤进“旋转门”的通行证。当选总统手中握有众多政治资源,除了政策倾向之外,把某些官位奉送给那些为自己的竞选大掏腰包的富翁也是划算的“买卖”,其中典型的莫过于美国两百多位驻外大使了。根据美国外交服务协会的统计,几乎历任总统都存在着这种行为,甚至尼克松和克林顿任命大使中的30%是政治捐款人。2009年5月,刚刚上任不久的奥巴马意外提名54岁的约翰·鲁斯出任驻日大使,在华府引发了轩然大波。这位身居加州的职业律师对日本乃至亚太事务一无所知、且丝毫没有国际经验可循,与美国往往派出包括前副总统、退休国会领袖在内的政坛贤达出使日本的传统做法大相径庭,惟一可能的解释就是鲁斯曾为奥巴马2008年的大选捐助了50万美元,且实际贡献可能还要高于这个官方上报的数字。
跳不出的“怪圈”?
客观讲,随着金钱在总统选举等重大政治活动中的泛滥,美国政坛内外的部分有识之士也认识到其对国家利益与政府决策的巨大负面影响。从1867年开始,美国就颁布了多项法案,禁止或限制海军、政府雇员、公司、政党组织、民众参与政治捐款或用于选举的开销。
在美国通过细节性立法阻击金钱政治之际,一种被称为“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组织却开始崭露头角。虽然国会在1943年和1947年推出相关法律,最终均未能有效限制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急速蔓延与扩张。
1974年,国会通过了修正案,为个人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直接捐款放宽了限额。这次改革在两年后又遭遇违宪诉讼,最终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允许政党组织自由将捐款用于提升投票率或注册率的造势活动当中。
上世纪80年代以来,“软钱”和“捆绑”成为美国选举政治的新名词。2002年,国会两院经过艰难的拉锯,推动通过了《两党竞选改革法案》,内容包括禁止全国性政党接受“软钱”、提高个人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组织给予候选人的捐款额度,等等。至此,“软钱”乱象得以暂时偃旗息鼓。又据《纽约时报》报道,2008年初选中两党的六位参选人共计至少接受过2000名个人的捆绑捐款。依照2002年立法中提高的个人捐款限额计算,捆绑方式为当年的两党参选人吸纳了约500万美元。
更为重大的变故发生在2010年1月,当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公民联盟诉联盟选举委员会”一案中所作出的判决打开了“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潘多拉魔盒”。这种可以较为自由地接受捐款用于投放特定议题政治广告的新型组织在2010年中期选举中“牛刀小试”,又在2012年大选中“大显身手”。虽然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并不承认与某位候选人的联系,但该现象的存在几乎彻底突破了以往所有对金钱政治的立法限制,金钱再次一泻千里地淹没了权力中心。
纵观这段曲折历程,美国竞选财政的改革尝试似乎走不出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制度调整永远为金钱政治留下漏洞甚至后门,而金钱政治的再度肆意则标志着下一次不完全改革的开端。这样周而复始之下,彻底除去金钱对民主的锈蚀沦为了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客观而言,一系列繁复的制度调整都只将视角放置在竞选财政运作的技术层面,从未在根本上改变美国围绕“金钱民主”展开的经济结构与政治模式,意识形态的局限性暴露无遗。与此同时,数次尝试皆为从上至下的、由国会发起的、以立法方式实现的制度改良。作为主导者的国会议员本身也以连选连任、延续政治生命为基本目标,不但无法与“金钱政治”绝缘,甚至在连任压力下对金钱的希求更甚。在这种情形下,政治人物不可能推进彻底的改革,必然会为自身利益考虑而留有余地。此外,对金钱政治的数次制度限制几次遭遇司法权干涉的例子,也充分说明美国政治在分权制衡的语境下,其碎片化已走向极致,为多元的特殊利益诉求预留了细密的渗透孔道。正是因此,甚至出现了联邦最高法院为了美其名曰的“保护言论自由”,而默认“大金主”们通过政治行动委员会等方式左右选情的宪政尴尬。
随着2012年选战好戏的连台上演,金钱再次粉墨登场。根据美国广播公司和《华盛顿邮报》在今年3月初进行的民调,69%的受访者不赞同将政治行动委员会等组织合法化,仅有25%的人认同其合法地位。由此可见,在广大美国民众当中,对“金钱政治”的厌恶和对更为彻底改革的渴望已渐成主流,美国的政治人物必须予以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