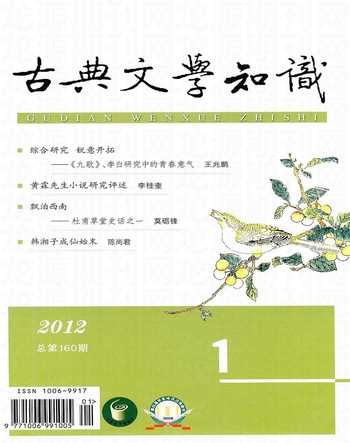《博物志》与《拾遗记》
顾农
一
西晋大作家张华(232-300)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固安县南)人。其父当过郡守,死得很早,所以他小时候很苦,靠牧羊维持生计,而能自学成才。正因为他没有受到正统教育的束缚,眼界特别开阔,“学业优博,辞藻温丽,朗赡多通,图谶方伎之书莫不详览”(《晋书·张华传》)。他青年时代写的《鹪鹩赋》得到阮籍的夸奖,被认为是势头最好的青年作家,且有王佐之才。张华广泛涉猎当时几乎所有的知识领域,回答并解决过许多难题,令人们大为惊讶,认为这个人实在渊博到难以理解(详见《世说新语·品藻》“刘令言始入洛”条);后来颇有些关于他的神奇故事,内容虽不可信,却可以表明他具有超乎想象的博学。
张华渊博的学问集中地反映在《博物志》一书中。该书据说原有四百卷,后应晋武帝的要求,压缩精编为十卷。王嘉《拾遗记》卷九云:
张华字茂先,挺生聪慧之德,好观秘异图谶之部,捃采天下遗逸,自书契之始,考验神怪,及世间闾里之说,造《博物志》四百卷,奏于武帝。帝诏诘问:“卿才综万代,博识无伦,远冠羲皇,近次夫子,然记事采言,亦多浮妄,宜更删剪,无以冗长成文。昔仲尼删《诗》、《书》,不及鬼神幽昧之事,以言怪力乱神;今卿《博物志》,惊所未闻,异所未见,将恐惑乱于后生,繁芜于耳目,可更芟截浮疑,分为十卷!”即于御前赐青铁砚(此铁是于阗国所出,献而铸为砚也),赐麟角笔(以麟角为笔管,此辽西国所献)、侧理纸万番(此南越所献。后人言“陟里”,与“侧理”相乱。南人以海苔为纸,其理纵横邪侧,因以为名)。帝常以《博物志》置于函中,暇日览焉。
《拾遗记》乃小说家言,其中可靠的史料很少。在今本《博物志》中仍有若干“浮疑”之处,不知是删削未尽,还是这些内容在当时并不算是什么“幽昧之事”。《拾遗记》有不少内容是杂抄自先前的古书(古人著书可以如此,在传播手段相当薄弱的时代,这种做法自有它的合理性),也有民间的传说,以张华之博雅,原本《博物志》卷帙甚多是可能的;而现在看到的十卷本也未必就是其压缩精编本的原貌,大约已经后人的增删改动。集外佚文甚多(有二百多则)即足以表明今本《博物志》与原书相差甚远。古代的小说特别是唐以前的小说往往有这一类虽有原书作为根据而变化相当不小的情形,而且无从复原,只好当作某种集体创作来欣赏和研究——署其大名的作者只不过是这个集体的一个主要代表。
《博物志》旧有版本甚多,今所通行者为范宁先生的《博物志校证》(中华书局1980年版);又有王根林先生校点本,收在《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中。
今本《博物志》的内容约可分为杂录和志怪两大部分,而以前者为主(卷一至卷七)。《四库全书总目》将此书列入小说中的“琐语”一类,根据正在于此。杂录中多载罕见的风俗和事物,例如有这样一种“异俗”——
楚之南有炎人之国,其亲戚死,朽其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乃为孝也。(卷二)
如此处理后事,从中原人的立场看起来自然奇怪得很,但这种“剔骨葬”的办法在某些边远地区是实行过的,而且延续了很长时间。又如关于火浣布(石棉布)的记载:
《周书》曰:西戎献火浣布,昆吾氏献切玉刀。火浣布污则烧之则洁,刀切玉如腊(蜡)。布,汉世有献者,刀则未闻。(卷二)先前曹丕在《典论》中否认世上有火浣布的存在,被刻石立为经典,而后来实物出现,闹了一个大笑话。“切玉刀”这东西,张华只说“未闻”,并不否认其存在,态度就谨慎得多。对于常识以外的事物断然予以否定,很可能是危险的事情。
又如海蜇是当时中原人少见的,《博物志》中也有记载:
东海有物,状如凝血,从广数尺,方员(圆),名日蚱鱼,无头目,腹内无肠藏,其所处众虾附之,随其东西。越人煮食之。(卷三)
如此等等。此外又有若干普通人不具备的知识和窍门,例如前代有道之士总结的长寿秘诀:
皇甫隆遇青牛道士姓封名君达,其论养性(生)法即可放(仿)用,大略云:“体欲常劳,食欲常少,劳勿过极,少勿过虚。去肥浓,节酸成,减思虑,捐喜怒,除驰逐,慎房室。春夏施泻,秋冬闭藏。”详别篇。武帝行之有效。(卷五)
按,皇甫隆乃是汉魏之际的著名寿星,曹操曾特别写信向他请教,皇甫隆的回答大约就是他得之于封君达的这样几条基本原则:一要经常活动,但不过量;二要节制饮食,但不过头;三要少吃脂肪,少吃盐,少瞎动脑筋,保持正常的情绪,不追逐名利,谨慎地安排好性生活;四要根据季节的变化调节自己的状态,与自然同步运行。“除驰逐”这一条曹操大约做不到,其他应该是可以实行的。这几条确实精彩,现在的科学家给大家讲养生长寿之道,大抵也还是这些意见。
又如书中介绍一种补品“黄精”道:
黄帝问天老曰:“天地所生,岂有令人食之不死者乎?”天老曰:“太阳之草,名日黄精。饵而食之,可以长生。太阴之草,名曰钩吻,不可食,入口立死。人信钩吻之杀人,不信黄精之益寿,不亦惑乎?”(卷五)
黄精就是野生姜,据说经常服用确实有延年益寿的功效,嵇康就非常相信这一点,曾经在《与山巨源绝交书》里特别提到过;张华大约也很相信此事。魏晋问人所服之药最著名的是五石散,那是比较高级而且危险的东西,黄精比较靠谱,而且花费要少得多。
还有一些知识大约是张华个人的心得,例如他曾详细地谈起如何将胡须染黑:
胡粉、白石灰等以水和之,涂鬓须,不白。涂讫著油,单裹令温暖,候欲燥未燥间洗之。早则不得著,晚则多折,用暖汤洗讫,泽涂之。欲染,当热洗,鬓须有腻不著药,临染时,亦当拭须燥温之。(卷四)
张华本人有一部美髯,一向加意保养(详见《晋书·陆云传》),这方面的要领包括染须的知识自然是他关心的;这里讲得如此细致具体,郑重其事,应当是包含了他的独得之秘。
张华对于这一类知识特别重视,注意加以记载。当然他也记录了不少未必可信的传闻之辞。这样的文字,当时正属于“小说”的范围,而到今天已经不能算是小说了。
今本《博物志》的后三卷即“史补”和“杂说”上下,志怪小说的意味相对比较浓厚一点,虽然张华仍然关心知识性而不甚注意讲故事,但某种意义上总算比较靠近今之所谓小说了。试看下列三则:
《止雨祝》曰:“天生五谷,以养人民。今天雨不止,用伤五谷,如何如何!灵而不幸,杀牲以赛神灵;雨则不止,鸣鼓攻之,朱丝绳萦而胁之!”(卷八)
旧说云: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飞阁于查(槎)上,多赍粮,乘槎而去。十余日中,犹观星月日辰,自后茫茫忽忽,亦不觉昼夜。去十余日,奄至一处,有城郭状,屋舍甚严,遥望宫中多织妇。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牵牛人乃惊问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说来意,并问此是何处。答曰:“君还至蜀郡,问严君平则知之。”竞不上岸,因还如期。后至蜀,问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计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时也。(卷十)
魏明帝时,京邑有一人,失其姓名,食啖兼十许人,遂肥不能
动。其父曾作远方长吏,官徒送彼县,令故义共传食之,一二年间一乡中辄为之俭。(《北堂书钞》卷一四三引)读来都意味深长。《止雨祝》条表明,人对于神灵往往采用两手,或送上供养,或加以威胁,一定要达成为我所用而后已。鲁迅先生说过:“我们中国人虽然敬信鬼神;却以为鬼神总比人们傻,所以就用了特别的方法来处治他。”(《华盖集续编·送灶日漫笔》)这里正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乘浮槎上天遨游,见到牵牛织女的奇闻,可算是一则关于宇宙航行的科幻故事。上得去,下得来,高人严君平都有准确的计算:设想得相当周到。最后那个关于官二代的故事颇富于象征性,正是这种胃口极大、吃得很肥的家伙,把一方的老百姓吃穷了。
二
《拾遗记》(一作《拾遗录》)的作者王嘉(字子年)乃是前秦的著名方士,《晋书·艺术传》和《高僧传·道安传》中都有他的传记,其中皆大写他的种种奇迹,很像一个活神仙,而可靠的生平资料甚少,只知道他活动的年代约相当于东晋早期至中期,早年先后隐于东阳谷和终南山,最后深得前秦苻坚的礼遇,成为一个近于国师式的人物;后秦姚苌对这位高人也很尊重,但很快就因为他有不利于自己的言论将他杀掉,其时应在四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九十年代初。
《拾遗记》据说原有十九卷,二百二十篇,早已残缺,后由南朝梁的萧绮收拾残稿重新编为十卷,并加评论,以“录日”二字领起,以区别于原文;但对于原文萧绮大约也略有改动润饰,内容或略有增添——古人编辑前人著作,往往自认为有此种权力。这样的重编本同本来意义上的伪书还不是一回事,有人认为全书都出于萧绮的假托,未免言之过重。《隋书·经籍志》杂史类著录《拾遗录》二卷,题“伪秦姚苌方士王子年撰”,另有《王子年拾遗记》十卷,题“萧绮撰”。似此,则该原书之残本到初唐仅存二卷(后又有分作三卷者);而萧绮的整理批评本因为篇幅大增,遂分为十卷,并且流传至今。今所通行者有齐治平先生校注本《拾遗记》(“古小说丛刊”之一,中华书局1981年版);又有王根林先生校点本,也收在《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中。
《拾遗记》的前九卷按历史顺序排列,从三皇五帝到“晋时事”,而第十卷却是昆仑山等八座名山。这样的结构似乎很奇怪。但《拾遗记》所写的历史并非事实上的历史,而是集中了一批传说,“事皆诞谩无实”(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六章《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下)》),近于《穆天子传》。《隋书·经籍志》列入杂史类,而所谓杂史,往往是“前史所遗,后人所记,求诸异说”(《史通·杂述》),到《直斋书录解题》开始另列入小说类。中国古小说的先导之一,正是杂史。《拾遗记》第十卷中的地理乃是《山海经》式的地理,同样“诞谩无实”,记载山川灵异、远方奇物,也正是古小说的渊源之一。所以这里表面看上去显得杂糅混乱的史、地结构不过是藉以安顿其所志之怪的框架,恰可一经一纬,互相呼应,使《拾遗记》成为一部内容丰富的志怪小说集。或以为此书有“史学化”的特色,其实王嘉之志决不在史学,只是借来一用而已。该书卷七至卷九魏、吴、蜀、晋部分记录人物逸事的成分增加,略见史料,但仍多非理性的奇闻,始终未脱志怪本色。
今天读《拾遗记》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其中颇有科幻的成分,事实上王嘉的许多大胆想象后来都变成了现实。例如宇宙飞船:
尧登位三十年,有巨查(楂)浮于西海,查上有光,夜明昼灭。海人望其光,乍大乍小,若星月之出入矣。查常浮绕四海,十二年
一周天,周而复始,名日“贯月查”,亦谓“挂星查”。(卷一)又如机器人:
时异方贡玉人、石镜。此石色白如月,照面如雪,谓之“月镜”;有玉人,机戾自能转动。(卷三)
又如潜水艇:
始皇好神仙之事,有宛渠之民,乘螺舟而至。舟形似螺,沉行海底,而水不浸入。一名“沧波舟”。(卷四)
又有近乎导弹的飞剑:
有曳影之剑,腾空而舒。若四方有兵,此剑则飞起指其方,则克伐;未用之时常于匣里为龙虎之吟。更有人工降水降温:
时天下大旱,地裂木燃。一人先唱“能为雪霜”,引气一喷,则云起雪飞,坐者皆凛然,宫中池井,坚冰可琢。(卷三)
书中甚至还提到近乎外星人的羽衣飞人:
溟海之北,有勃鞮之国。人皆衣羽毛,无翼而飞,日中无影,寿千岁。食以黑河水藻,饮以阴山桂脂,凭风而翔,乘波而至。中国气暄,羽毛之衣,稍稍自落。帝(按,指颛顼)乃更以文豹为饰。献黑玉之环,色如淳漆。贡玄驹千匹。帝以驾铁轮,骋劳殊乡绝域。其人依风泛黑河以返其国也。(卷一)
如此等等,王嘉的想象力不能不叫人佩服。他的叙述都非常简要,给读者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中国古代志怪小说中一向有科学幻想的成分,但无此密集有趣。
王嘉还有若干至今尚未实现的幻想,似可供科学家参考,或可作为动漫的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