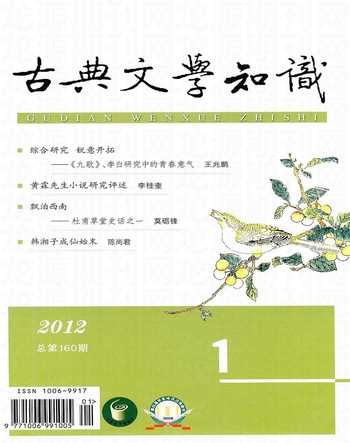刘永济及其词学研究
巩本栋
一
刘永济先生是近现代学术史上著名的学者和词人。
先生(1887-1966)字弘度,别号诵帚,晚号知秋翁,斋名易简、微睇等,湖南省新宁县人。刘先生出身于仕宦家庭,祖父刘长佑曾任清朝的直隶、云贵总督,父亲刘思谦也曾在广东、云南等省做过几任知县,然不能随波逐流,不久便弃官归隐了。刘先生自幼即随祖父、父亲生活和读书,关于这段经历,我们现在已不能详,然这给他带来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刘先生十九岁时离开家乡,先在长沙明德中学,后到上海复旦公学学习,开始接受现代科学知识的教育并受到民主思潮的影响。1910年,他考入天津高等工业学校,次年又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希望能够到国外学习工科,以实现其最初从事实业救国的愿望。后因不满学校当局的蛮横无理,放弃了官费留学的机会。
辛亥革命之后,直到1917年,刘先生多寓居上海。当时,近代著名词人况周颐、朱祖谋都在上海作寓公,刘先生便向他们问学,得到两位老前辈的特别赏识。这对他后来的词学研究和创作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17年,刘先生应他的老师长沙明德中学校长胡元琰之邀,回母校任教。1925年,在清华大学的吴宓先生介绍刘先生到清华任教,先生因胡校长的挽留,未能应聘。两年后,由吴宓先生再度介绍,刘先生始到沈阳东北大学任中文系教授。然不数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沦陷。刘先生离开东北大学,挈妻子儿女几经辗转,先后在浙江大学、湖南大学任教,后来到了已迁至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并于1942年起兼任武大文学院院长,直到]949年全国解放。在这期间,刘先生虽生活相对平静,但仍旧以一个正直知识分子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的忧患之心,关注和面对着世事与人生。
解放后,刘先生在精神上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他不顾年老体衰,努力从事教学与科研,除了给学生上课、指导研究生之外,还给中文系的青年教师讲授词学等,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如《文心雕龙校释》、《屈赋通笺》等,也都陆续修订再版,又完成了《唐人绝句精华》,并开始《文心雕龙辞典》的编撰。党和政府也很尊重刘先生。1956年,他被评为一级教授,并先后当选为政协武汉市常委、湖北省文联副主席、《文学评论》编委等。
在五十年代的一些政治运动中,刘先生也曾受到批判和冲击,甚至被打成“内定右派”,但他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双百”方针,对自己的国家和他毕生从事的教育事业,始终抱着极大的信心。他那积极正直、真诚谦逊的品格,也并未改变。然而,可悲的是他最后却没能幸免于1966年开始的那场浩劫。一夜之间,他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封建遗老”,遭到残酷的政治批判,积累多年的研究资料也散失殆尽。1966年10月2日,这位年近八旬、一生热爱祖国、刚正不阿的著名学者,竟被批斗致死。直到1979年,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从噩梦中醒来,刘永济先生才得以彻底的平反。历史终于给了他公正的评价,刘先生的高尚品德和精深学术也必将得到不断的发扬和永久的流传。
二
刘永济先生是一位十分渊博的学者。在五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在古代文学的领域内,从研究到创作,作了多方面的探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且不算未及收集的单篇论文和未完成的残稿,即就已成书者论,便有二十种之多(今大致已收入中华书局新版的《刘永济集》)。
刘先生早年从事文学理论研究,在《学衡》杂志上发表过《文鉴篇》,对文艺鉴赏有极精微的剖析,为学界所重。在明德中学时,他给学生讲授文学概论,贯通中西,要言不烦,所成讲义,取名《文学论》,曾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重印多次。到武汉大学以后,刘先生在文学理论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心雕龙》。在四十年代,他就完成了《文心雕龙校释》一书,诸所诠释,能得刘勰原意,堪为继黄季刚先生《文心雕龙札记》后的又一力作。刘先生谈到自己的这本书,曾说:“季刚的《札记》,《章句篇》写得最详;我的《校释》,《论说篇》写得最详。”以精于小学推黄季刚先生,以长于持论自许,亦是平情之论。
刘先生在东北大学时,因主讲中国文学史,曾拟写一部《文学通史纲要》,后因改教其他课程,只写到隋朝,先连载于《学衡》,1945年取名《十四朝文学要略》,由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此书重视文学名义的辨析、体裁异同的由来、艺术手法的发展、社会作用的变迁等,于每一纲目下分系许多原始材料,在观点和结构上都有许多特点。刘先生在此时期还写过一部《唐乐府史纲要》,以绝句为唐代的乐府,是较早的研究唐代乐府史的专著。与此书堪称姊妹篇的是刘先生晚年选释的《唐人绝句精华》,共选录唐人绝句788首,于每首诗的诗意、手法、风格等,均作了精到的分析评论,书前引言对唐人绝句的源流正变、艺术价值等,亦有扼要论述。
刘先生一辈子服膺屈原,研究屈原,于并世诸家中,独树一帜。他本拟撰写的“屈赋学五种”,生前完成了四种。《屈赋通笺》初稿于1932年,反复订补,1953年才写定。首为序论六篇,然后对《楚辞》中可以断定为屈原作品的《离骚》、《九辩》、《九歌》、《天问》及《九章》中的《惜诵》等五篇,每篇都分解题、正字、审音、通训和评文五项,加以考究。其有关全书总义有待商榷者,则别为《笺屈馀义》十九篇。二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61年合为一册出版。《音注详解屈赋定本》是刘先生根据《屈赋通笺》中所作的结论写成。原来只据校文写成定本,题为《屈赋定本》,附在《通笺》之后,1954年刘先生又加以注解,独立成书,并于1959年改定,易名《屈赋音注详解》。《屈赋释词》卷上释虚词,卷中释词汇,卷下释句例,是用王引之《经传释词》和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之法,从语言学角度研究屈赋的一部专著。
词曲研究是刘先生学术生涯中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其中词学方面,有《词论》、《唐五代两宋词简析》、《微睇室说词》和《宋词声律探源大纲》,我们将在下文详作介绍;曲学方面,则有《宋代歌舞剧曲录要》和《元人散曲选》,这两种也是刘先生授课时的讲义,书前各有序论一篇,颇多发前人所未发的意见,如认为宋代歌舞剧曲的结构有纵列横列之分,元人散曲有阴刚阳柔之分等,都很值得重视。
在刘先生已完成的研究著作中,以“楚辞学”、“龙学”和词学方面的较多,学林也很自然地推崇先生在这些领域的造诣,然实际上刘先生治学之广,读书之多,是很惊人的。他在群经、诸子、小学、史学及佛学方面,在目录、校勘、版本方面,在地理沿革、名物制度等方面,修养都很深厚。所以他研治古籍,就能左右逢源,多所创获。从有关《楚辞》以及其他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先生对古文字学和古史的造诣;从有关《文心雕龙》等著作中,又可以看出先生对玄学,特别是《庄子》的造诣;而从其诗词的创作与研究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先生对禅学的研究也是很深的。他所以很少发表文学研究以外的东西,只不过是因为他并不以为读了书就一定要让别人知道罢了。刘先生的著述篇幅都不大,要言不烦,取其足以达意为止,显然属于“简约得其英华”的南学,而不是“深芜穷其枝叶”的北派。黄庭坚评陈师道“读书如禹之治
水,知天下之络脉,有开有塞,而至于九川涤源、四海会同者也”。刘先生的治学也正是如此,或着眼理论,或侧重作品,由博反约,同时又都是注意“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
三
由博反约,刘永济先生在词的创作和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刘先生少年时期曾在其姑父松琴龙家中得读古今词集,增养了词学研究的兴趣。辛亥革命后,他在上海向近代词学大师况周颐请益,曾撰《浣溪沙》一词,词曰:
几日东风上柳枝,冶游人尽著春衣,鞭丝争指市桥西。
寂寞楼台人语外,阑珊灯火夜凉时,舞余歌罢一沉思。
惠风老人喜谓:“能道‘沉思一语,可以作词矣。词正当如此作也。”当时,另一位词学宗师朱祖谋亦寓居上海,其主沤社,曾分题咏绿樱花、红杜鹃。刘先生非社中人,而况氏命试作,疆村老人一见而称之为“能用方笔者”。刘先生从况、朱两位先生学词的这番经历,对他后来词学创作和研究发展的影响,是极为重要的。
清人张惠言等推尊词体,有意识地以比兴说词,认为:“‘意内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词选序》)于是过去被人们视为小道的词,也逐渐成为可以而且应当反映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和词人对这些事件的思想感情的一种文体。这使得词在这以后的一百多年中,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创作上,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其中像周济之主张“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陈廷焯之提出“沉郁说”等,都已在理论上对张惠言的比兴说作了补充和发展。王鹏运和朱祖谋作词、论词皆承常州词派,而况周颐则在理论和创作上都很有成就。他既主张“词贵有寄托”,又以为这种寄托“所贵者流露于不自知,触发于弗克自已。身世之感,通于性灵,即性灵,即寄托,非二物相比附也”(《蕙风词话》卷五)。这些观点,在当时和后来都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刘永济先生的词学,正是继承了这些前辈的业绩的。刘先生作词受朱祖谋、况周颐影响,但取径更广。他不独如席启駉先生所说的,“为梦窗词,而往往似白石,意其胸襟性情或近之欤”(《刘永济词集序》),而且又如朱光潜先生所品题的,“谐婉似清真,明快似东坡,冷峭似白石,洗净铅华,深秀在骨,是犹永嘉之末闻正始之音也”(《刘永济、词集》卷首)。同时,他还对冯延巳的词下过很大工夫。所以,他的作品可以说是将冯之深婉、苏之豪放、姜之清剐、吴之丽密,融于一炉,而自成一格的。
刘先生词学研究的特色,是以作品为中心,即通过创作、阅读、鉴赏、考证和批评等一系列方法来对作品进行探索的。他在词的创作上的造诣,使他对作品的阅读和鉴赏,往往能作出十分恰当的选择和深具会心的剖析;而他进步的词学观念和深厚的文学理论素养,又使他所做的许多批评和探索,带有很强的理论色彩和启发意义。
刘先生早年在武汉大学讲授词选,曾编有《诵帚庵词选》四卷,选录作品较多,晚年由博返约,又撷唐宋词的精华,写成《唐五代两宋词简析》。全书篇幅并不大,仅选词一百三十一首,然选择的眼光、体例和每首词后所作的评析,却很有特点。从选目上看,刘先生的《唐五代两宋词简析》,选唐五代词56首,宋代75首(其中北宋38首,南宋37首),并将所选全部作品分为九类。可以说是既重视词的创作的源头,又重视其发展流变;既突出了李煜、冯延巳、柳永、苏轼、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等人在词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又顾及了不同风格流派中其他有成就的作家;既注意到题材与主题的丰富多彩,也注意到词体的不断革新和风格的异同变化;既关注了士人的创作,也不忽略民间词的作用和意义,加之作品注释的简要,分析的精到,都有助于读者对唐五代宋词发展繁荣状况的全面了解。
1960年,刘先生为武大中文系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讲授南宋婉约派词,以吴文英为重点,并追溯周邦彦、姜夔、史达祖,后及王沂孙、周密、张炎,以见此派源流,撰成《微睇室说词》。其中选人吴文英词79首,周邦彦6首,姜夔6首,史达祖3首,吴潜1首,王沂孙5首,周密1首,张炎2首。这是在近人陈洵《海绡说词》和陈匪石《宋词举》之后,又一部说词的名著,也是先生对于宋词的晚年定论。
吴文英,字君特,号梦窗,又号觉翁,四明鄞县(今浙江宁波)人,是南宋末年的著名词人,有《梦窗甲乙丙丁稿》四卷。与当时的许多江湖游士一样,吴文英虽一生未仕,但以词章曳裾侯门,又难称独行;而其词虽丽密幽深,别具一格,然下者亦不免晦涩难解,故历来对其词的评价,或毁或誉,众说纷纭。如南宋张炎即以“质实”目梦窗词,认为它“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词源》卷下)。而自清中叶至清末民初,词家如周济、戈载、冯煦、陈廷焯、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况周颐、陈洵、杨铁夫等,则又大都对吴文英的词十分推崇,至有“近世学梦窗者,几半天下”之语(吴梅《乐府指迷笺释序》)。其中郑文焯手批《梦窗词》、陈洵的《海绡说词》谈梦窗词的部分、杨铁夫《梦窗事迹考》和《梦窗词笺释》,可以说从不同的角度,分别对吴文英其人其词,作了初步的研究。后夏承焘先生又撰《吴梦窗系年》,对吴文英的生平行事,作了进一步的考辨和论述。然继而对吴文英的词作出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更为全面的评价的,则不能不推刘永济先生的《微睇室说词》。
吴文英生活的时代正是宋王朝由衰败没落而终至走向覆亡的时代。吴文英生平与朝贵如贾似道、吴潜、嗣荣王赵与芮皆有来往,有词可证,然终其一生又始终未因此而得一官半职。如夏承焘先生所考,吴氏是一位“但有酬酢而罕干求,在南宋江湖游士中,殆亦能狷介自好者耶”(《吴梦窗系年》)。故宋王室国事日非的现实,在这位狷介之士的词中,似不能不有委婉的反映。而刘先生论词,又一向主张“苟其情果真且深;其词果出肺腑之奥,又果具有民胞物与之怀,而又若万不得已必吐而后快之势,则虽一已通塞之言,游目骋怀之作,未尝不可以窥见其世之隆污,是在读者之善逆其志而已”。因此他分析吴文英的词,也就往往会注意从“游目骋怀”之词而逆探其“民胞物与之怀”,尽管这在梦窗词中表现得并不总是很明显。我们看他说吴文英《贺新郎》(陪履斋先生沧浪看梅)、《八声甘州》(陪庾幕诸公游灵岩)、《三姝媚》(过都城旧居有感)等词,论南宋末“外患日深而朝廷阘茸,一味欺矇粉饰,势已岌岌而不知惧。故梦窗每抚今追昔,感慨甚深。此等情况,词中多有,虽或但切己身言,而世事即在言外,亦词人忧衰悯乱之情之发于文字者”,对我们解读梦窗词中隐约的忧国情怀和悲凉心绪,评价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尤有帮助。
据夏承焘先生《吴梦窗系年》,吴文英在苏州时曾纳一妾,后因故遣去;在杭州复眷恋一妓,未娶而妓殁。故其追念往事,缠绵往复,情不能已之作,集中颇多。如《踏莎行》(润玉笼绡)、《绛都春》(燕亡久矣,京口适见似人,怅然有感)、《齐天乐》(烟波桃叶西陵路)等等,皆是
其例。其他像写友情的《扫花游》(赠芸隐)、《解连环》(留别姜石帚)等,集中也有不少。况周颐论词,主张“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必佳”(《蕙风词话》卷一),刘先生论词亦然。他选讲梦窗词,于其感时哀世之作外,又特注意那些感旧怀人而情意真切的作品,注重挖掘其感情的真实内涵。
梦窗词向称难读,这一方面是因为有关的背景材料不足征的缘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其中有些作品在艺术上存在着过于修饰之病。所以,刘先生对梦窗词的解说,便主要是通过对其艺术技巧的分析来进行的。由于刘先生自己在词的创作上有丰富的经验和很高的造诣,就使得他的这些分析能够深入腠理,读之顿有化难为易、化晦涩为显明之感。像他说《三犯渡江云》(西湖清明)等很多作品,由词意蕴涵到组织结构,由用典、用语到音律声韵,无不详加分析。其体会之深刻细腻,分析之擘肌分理,令人赞叹。
在清末民初曾受到极大重视的梦窗词,自现代尤其是解放以后直至八十年代初,由于人所周知的原因,却受到了极大的冷遇,而在这期间,只有刘永济先生对梦窗词的研究是一个难得的例外。他从梦窗词艺术手法和技巧的具体分析人手,而着眼于这些手法和技巧所表现的南宋末年那个特定时代、特定人物的一份真实的思想感情,不穿凿附会,轻易拔高;也不空洞教条,盲目贬抑,从而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给梦窗词作了一个准确的定位。
《微睇室说词》之外,刘永济先生的另一部重要的词学著作是《词论》。如果说前者主要是一种教人读词、或日对作家作品进行具体研究的著作的话,那么后者则主要是一部教人作词、或日对前人的作词、读词方法从理论上进行总结和探讨的著作。
《词论》两卷,本是刘先生早年在湖南大学任教时的词学讲义,1940年,刘先生到时在乐山的武汉大学任教,所讲授的课程仍有词学一门,故续有增益,尤其是下卷,刘先生还准备以其为蓝本,提要钩玄,写成几十则词话,作为学词的纲领。
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无论是诗论还是词论、文论,一般都具有短小精悍的特色,有时甚至用省略过程,直抒结论的方式表达,而由于作家和评论家们往往具有丰富的创作经验和精湛的艺术技巧,他们的意见又是值得重视的。因此,对这些意见,就应当进行一番认真的疏通印证、归纳总结的工作。刘永济先生在《词论》中所做的,可以说正是这样一项工作。即如是书下卷,专论作法,实是一部词话选,古人论词的精要之语,多在其中。刘先生因其自身在词的创作上造诣颇高,所以他对这些精要之语的体会和疏通,也就往往十分精到,备见功力。且看一例。自南宋张炎论词发为“清空”之论,至清朱彝尊崇姜、张,以清空雅正为主,推阐提倡,号为浙派。然“清空”究作何解,并不很容易捉摸。刘先生从辞、意关系着眼,认为清空、质实之辨,不出意、辞之间。“意径而辞不逮焉,或辞工而意不见焉”,即为质实,而“清空云者,词意浑脱超妙,看似平淡,而义蕴无尽,不可指实。其源盖出于楚人之骚,其法盖由于诗人之兴,作者以善觉、善感之才,遇可感、可觉之境,触物类情而发于不自觉者也。惟其如此,故往往因小可以见大,即近可以明远。其超妙、其浑脱,皆未易以知识得,尤未易以言语道,是在性灵之领会而已”。清空之境界虽极高,然其意蕴、渊源却十分清晰。再看一例。况周颐曾提出“填词第一要襟抱”,然怎样才谓之有襟抱,又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却言之不详。刘先生则解释道:“按襟抱、胸次,皆非专由学词工力所能得,特功力深者始能道出之耳。襟抱、胸次,纯在学养,但使性情不丧,再加以书卷之陶冶酝酿,自然超尘。但道出之时,非止不可强作,且以无形流露为贵。……予最爱东坡《定风波》(沙湖道中遇雨)词,能于不经意中见其性情学养。其词曰:‘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诵之数过,而祸福不足摇之之精神自然流露。其冲虚之襟抱,至今犹能仿佛见之。”以苏轼词释襟抱之意,不但准确,尤为形象,真可谓“功力深者始能道出耳”。
刘先生撰为《词论》,其初衷固然主要是教人学词。然而,我们看他上卷通论词之名义、缘起、宫调、声韵和风会,下卷专论作词方法,分为七节:总术、取径、赋情、体物、结构、声采和余论,从词的起源、声律、词史的发展,到词的创作论的诸多范畴,几乎涉及到词学理论的所有重要方面;而其中每一节的撰写,又必先对有关的词学文献进行全面细致的考察,然后严加选汰,择取具有代表性的说法,进行归纳排比,或疏通印证,考辨得失,或发明引申,从容立论,多精详周密,平正通达,要言不烦。因此从总体上看,它实已建构起一个相当完整的词学理论体系。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尤其是词学理论的研究,无疑也是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