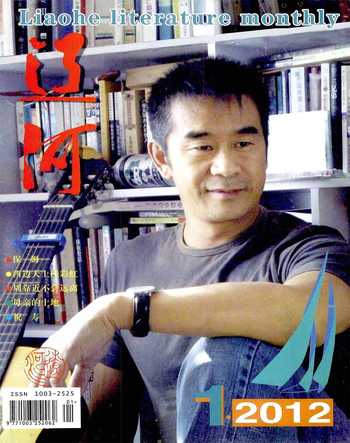火车 火车
郑家友
赤
麦根穿行在这座新兴城市钢筋水泥树起的森林里。麦根瘦高,行色匆匆,汗流浃背,直奔火车站。森林和森林里如织的车流人流构成了这座现代化城市的美丽画卷,也喧嚣出了雄浑的交响曲。其曲为其画所配,其画为其曲所佐,互衬,相得益彰。线杆似的麦根淹没在这画里曲里,由于他的瘦高很容易将其分辨。老阳在这座城市上空肆虐蒸煮,仿佛是对这位行者乃至这整座城市的考验。然而,这座城市好像面不改色心不跳。麦根却在不断甩头,汗水也便在这头的甩摆中淋漓。麦根两手提着物品,腾不出哪一只擦汗。麦根忍受着,扛着。其实此刻麦根的主要思维不在这里。
城市的森林并未尽善尽美,有的钢筋水泥依然外露,嘴歪鼻扭,犬牙交错。一座座高高的塔吊有的工作,有的静止地悬于半空。这座城市似乎依然处在半生不熟中。
对于麦根,此当是个不同寻常的下午,他的内心焦急如焚。加上老阳的淫威,内外煎烤,麦根感到自己就将化为灰烬。
大约半小时前,麦根在这座城市一处高高的脚手架上难耐地挥汗,接受着老阳的熏制与烘烤。腰间的手机突然响了。麦根抠出电话刚贴于耳,什么?麦根险些一头从脚手架上栽下来——他听到了母亲病危的通知!
麦根是这座城市的外来打工者。他从那座大山走出,风雨冰霜,转战南北,如今来到这座城市。麦根的故乡在那个叫端庄的地方。
麦根走过一些城市,有的城市没有火车站。但这座城市有。麦根不知道没有火车站的城市会有什么感觉?可麦根对有火车站的城市却感到特别好。尤其对火车站,倍觉亲切。假如这座城市没有火车站不通火车,他不知道此刻能有什么办法以赶上或超过火车的速度将自己送到母亲面前与母亲相见?当然乘飞机可以到达。这座城市却没有飞机场不通航。此刻的麦根为这座城市通火车而感到庆幸,也为自己能来到一个通火车的城市打工而感到走运!
归心似箭!麦根冒着汗雨,穿越一层层热浪和如蚁的人流车流,终于来到了火车站。低矮土旧的老站早已灰飞湮灭。取而代之的是恢弘、高大、明亮的现代化建筑。进入站内,上下楼有步行阶梯,也有滚动电梯。电梯敞开胸怀不停运转,时刻恭候旅客光临,忠诚而热情,辛苦而大气。不时看到保洁员的身影,这里处处显得干净。
此城叫金城,车站自然叫金城站。前面说过,麦根的故乡在端庄。金城与端庄,相距约五百公里,火车普遍提速后需行驶八小时。此前运行时间要更长些。金城到端庄是这条全线约一千二百公里的南北交通大动脉上的其中一段,金城在南,端庄在北。据说,这条铁路线为日伪时期所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特别是现在,它的地位更加突出。
金城和端庄均不是这条铁路线的始发站和终点站。在各自的两端以远,均有铁路线或笔直或弯曲地美丽延伸。
最早发往端庄的火车时间是15:40分的,车次为:K2018。就它了,麦根火速去买票。
买票的人很多,不知为什么,每个窗口都排着长长的队伍。有点浩浩荡荡的意思。麦根走过去接上其中一排的队尾,不久就被后续者夹在中间。有个后来者不排队,老爷般气宇轩昂理直气壮地直接挤到窗口那去了,仿佛他是这座城市的老大。嗨嗨嗨我说那位先生自觉点儿嗨,您是市长还是觉着长了三头六臂?一个声音鎯头般掷过去。笑话,市长、三头六臂谁干这个呀?这个声音更加重了那鎯头的力度。我着急!那位被砸者扁过头来。得了吧您,半夜借家伙,您用谁不用,您急谁不急?哈哈众笑。到后边排队去。窗口内女售票员把话甩给那被奚落者。那人离开……
麦根买完票举头看看墙上的钟,14:45分,离开车时间还有近一小时。对于归心似箭的麦根,一分钟的等待都是一种严酷的折磨与煎熬!这时的这个瘦高而黝黑的男人眼里全是火!
橙
麦根在外省打工。麦根家所属的那个省的省城火车站,也有一个人在急急地赶火车,时间也是在那个下午的某时。那个下午的那座省城也被那能揭掉人皮的灼热烤得到处起白烟。
那个焦急的赶火车者,是这座省城某高校的美丽高挑的女高材生。此女焦急赶火车的目的和麦根一样,也是回家探望病危的母亲。此女叫麦花,是麦根的胞妹。
麦花接到母亲病危的电话立刻哭了。她内心那块最柔软的地方如遭了刀割!不容多想,她简单收拾了一下,立刻离开学校直奔火车站。
然而不巧,火车站内巨大的电子屏幕列车时刻表如火的红字显示,最快最早开往家乡的那趟列车大约晚点四十五分钟。除此,通往家乡的另外车次最早也要一小时以后了。当然她不能选。这时这个漂亮又年轻且满脸书卷气的姑娘,如水的眼睛里充满了焦急。不由得拿出手机看时间。时间告诉她,如果不出意外,再有二十五分钟,本城有一班大巴车通往她的家乡端庄。二十五分钟与四十五分钟,麦花没有丝毫犹豫,她选择了二十五分钟。别说相差二十分钟,就是相差一分钟、半分钟,只要有差,她就要选最早那个。况且大巴走高速路,路线又比那段铁路线短,到家的时间不会比四十五分钟后的火车晚。经验告诉她,晚点的火车,有时晚点时间还会延长。那就更糟!于是,麦花脚板未停,立刻旋出火车站,叫辆的士,直奔本城的客运站。麦花知道,在本城乘车回家,汽车比火车票价要高一倍。麦花顾不了那么多了,此刻她想,母亲比什么都重要!
很走运,麦花乘上了通往端庄的大巴。却对麦花牵挂病危母亲的沉重心情没有丝毫安慰与削减。相反,她对那多花出一倍的长途车费感到心疼!她把这笔账记在了那个晚点的火车上。可是又能怎样呢?麦花觉得,她只能忍受!
大巴内的卫生及其他条件不错,风从打开的车窗灌入,解除了车内的暑热。窗外路旁沿途的白杨林,高密列岸,浓荫如堵,似坚强卫士,敬业守岗。路心隔离带,花木艳丽葱茏。这如诗若画似酒般的窗外景致及可人的习习凉风,能叫车内的每一个乘客熏醉怡然!麦花却无心品赏和感受这一切。她靠在座背上,微微闭上眼睛,陷入了对母亲更深的牵挂和对往事的一些回忆。
麦花早年丧父。父亲的离去,使她们的家塌了一大半,无疑也使她们本就贫困的生活雪上加霜。母亲柔弱的身体支撑起这个家,带着两个哥哥和她艰难度日。
为了这个家,为了二哥和她能够上学,大哥麦成十五岁就辍学同母亲一起扛起家庭生活的重担,直到结婚生子大哥也未离开过那座大山。他说他要在那座大山里陪伴母亲到百年。
二哥麦根比她大三岁。为了她能上大学,高中未毕业就背井离乡去远方打工了,挣钱为母亲治病养老,为她麦花挣学费。二哥知道大哥麦成为这个家付出太多。他要从大哥手中接过责任,继续扛着生活往前走,让大哥缓一缓,喘喘气儿。
麦花深知,这个家要是没有大哥是难以支撑的;要是没有二哥,她也不可能上大学。母亲过于劳累早已多病缠身。如今糖尿病综合症,就要夺去她的生命。电话里大哥就是这样转述给她的。母亲看病,她上大学,花的都是大哥二哥的血汗钱。今天,为了快快赶到母亲身边,多花去一半的路费,又怎能不咬她的心呢?同时她又十分担心母亲是否能够活着与她见面……想到这,两行热泪再度涌出,慢慢爬上她的面颊。
黄
不知道是不是与麦根作对,那趟通往麦根家乡的K2018次列车也晚点了,大约晚点四十分钟。这个消息是候车大厅检票口上方长方形的电子屏幕上发布的。接着,车站广播里,一女播音员也用纯正的普通话,字正腔圆极富魅力地将这条消息送到麦根的耳朵里。最后,那个女播音员承诺般又十分谦谨的说,由于列车晚点,给旅客带来的不便,我代表铁路部门向你们表示深深的歉意!没等这后边的话说完,麦根的火便腾地熊熊燃烧起来,顷刻燎遍全身。麦根十分内向,闻此消息他的第一反应也是惟一反应,就是霍地从座位上站起,眼睛死死盯着那个发布这条消息的电子屏幕。不知他是被这消息震傻了,还是希望这消息再变回去,恢复正点?要不就是想冲过去,找根大棒把那屏幕捣下砸碎!不,这后一条麦根做不到,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他的做不到,与个人修养和道德水准没有多少关系,更多的是因为他胆子小。这个大山里走出来的娃,几年的高中生活和南北闯世界,也没能把他的胆子练大。个子虽高,血管里流的血却始终受着父母遗传的制约。麦根的最大胆量和不安分,就是放弃高中学业外出打拼。那也是因为困苦的生活所迫。然而仅仅一个火车晚点,不会让他那么冲动不理智,世道也没有教会他那般无视法律和丧心病狂。父母没有把这种东西传给他。因为父母也没有。实际,麦根仅仅是被那条消息惊得瞠目,从而导致他因为拖延探望母亲的时间,而使他更加焦灼万分,心急若焚,仅此而已。麦根的汗更多了。
麦根渴了,他想,要是有瓶水喝该有多好!这并不难解决,大厅那边的小卖部就有,而且品种很多,口味各异,最多不超过几块钱就可以喝一瓶。麦根却没去买。他舍不得那几块钱。对于他,他认为那是一种奢侈。工地干活时,不论天多热,他多渴,旁边叫卖冷饮的声音有多高,他也从来不买。他认为工地的自来水完全可以解决他的这种渴求。为省钱,他不吸烟不饮酒,不找女人,不做一切乱花钱的事情,咬牙克制破费钱财的所有欲望,如一台机器,仅限自己运转在工地与宿舍之间。全工地所有民工中,麦根的衣着最简陋。麦根心里只念念不忘两件事:为母亲治病,供妹妹上学。
其实,麦根的提袋里背囊中就有饮料和水果,可那更不能动,那是买给母亲的。
这会儿的麦根已渴到极限!
忽然,他脑子一闪,便把眼睛拔离电子屏幕,转身拿起自己的物品,直奔候车大厅的洗手间。放下物品,弯腰、伸颈、转头,扭开外间的一水龙头,哗哗哗一顿饱饮,又钻进里间哗哗哗一阵力排,便十分惬意又心满意足地拎着东西离开了那里。
候车大厅在二楼,极其宽敞。高高的半透明顶棚使大厅十分明亮。大厅没有空调,但安着窗纱敞开的窗口并不使大厅感到闷热。
大厅内设有一排通往各地的检票口。不久,又有几次列车的晚点时间,相隔很短地相继出现在各自检票口上方的电子屏上。接着,女播音员又把各次列车的晚点时间复播了几遍,与其红色字幕呼应得很紧。
大厅里候车的人很多,候车的秩序却很好。不知是空间大吸了声音,还是因为别的什么,整个大厅显得安静。每个人都在各自的位置,或站或坐,守候着外面夏日午后的阳光,耐心地等待着自己车次检票时间的到来。即便是流动的脚步也显得很轻。K2018次列车晚点通知时,也没有听到旅客们的更大反响,只是有人咂舌,也有人说,怎么又晚点了?
可是大厅里又突然报出四个车次的晚点时间,厅内的候车者便慢慢开始骚动起来。一些人离开坐席开始在大厅里沙丁鱼般游来游去,或者向外走;而另一些人开始准备或已经在办理退票事宜。与此同时,抱怨之声如同细微的波浪开始在大厅里悄起、渐大,最后在大厅里翻滚。一个说,这破车怎么总晚点!另一个说,奇怪吗?这是铁路的家常便饭!又一个说,不仅这里,全国很多地方都有列车晚点,有一次我在湖北宜昌,一趟列车晚点竟长达两个半小时。更有一个说,有一次我在上海去九江做一单生意,因为列车晚点我迟到了,竟然损失三十多万!妈的,谁来为老子的损失买单?谁来为耽误旅客的时间负责?没有人,只有自己扛!这是一个操着外地口音的人,短小黑胖,颧骨很高,鼻孔和嘴唇均花朵般外翻。看来这人火气不小,声音也格外地嘹亮,估计他上“星光大道”能取得好名次……
大厅里没见警察,也没见保安。旅客们不断升温的嘈杂骚乱气氛,病毒般迅速在大厅里蔓延,最后,大厅里成了一锅粥。
瘦高的麦根待在一个角落里双唇紧闭,两眼圆睁,一言不发。任凭嘈杂的波浪将他推来涌去,随它这锅乱粥如何沸腾!
突然,那个检票口上方的电子屏上又跳出了这般字样:K2018次列车约晚点1小时50分钟。
什么,K2018次列车晚点时间延长了?麦根眼瞪若卵,立刻傻掉!
绿
不知是神助,还是那个病入膏肓者的生命如东院二妞、西院三丑手上脚下玩的那条橡皮筋儿,是那么有弹性。麦花到家时,母亲的生命之灯依然有着光亮,尽管那如豆的光亮很微弱。麦花的到来,如一根灯扦,拨向了母亲那如豆的生命之火,一瞬间使之爆出几点慰人的火星——母亲闭着的眼睛微微睁开,似乎一亮,随后又渐渐暗淡下去了。母亲的这一微动,使在场的亲人的眼睛也跟着为之一亮之后,紧跟着人们到底还是看到了母亲那盏生命之灯里的油究已燃尽,只剩下外面挂满油污的空瓶子和灯捻子头上的那点微弱的余光!而这点余光也已完全不是麦家母亲生命的顽强,而是因了某种未了的心愿而迟迟不肯熄去。至少可以理解为对麦根的等待。
是的,麦家母亲果然是在等待那个最让她扯肺牵肠放心不下的瘦高的儿子麦根。麦家母亲知道,为了给她治病,为了麦花上学,麦根至今没有条件娶上媳妇。麦家母亲这条即将断掉的生命之线,一端可怜勉强又无力地攥在她自己手里,另一端却牢牢地系在了麦根和麦根的终身大事上。她在等待麦根,她要看麦根最后一眼。
自从见到母亲,麦花便泪流不止。此刻围在母亲病榻前的所有亲人都心如刀悬,泪眼婆娑。这间石头老屋,本就十分低矮老旧,母亲的病危,夜幕的降临,更加为其披上了沉重的阴影,压抑得所有在场者喘不过气来。麦家母亲身如纸薄,面如土灰,双眼紧闭,乍一看,没有一点生命的迹象从她那里传导出来。如果没有那一丝微弱的呼吸尚在,简直就是一个死人。这条劳苦了一生的艰辛生命,在医院里住了数月,如今转回家来。医生说,回家等待吧,没有医治价值了!长子麦成,儿媳佟欢,幻灭,心如死灰!
北地那口土柜上的老钟,苍凉而迟缓地挪动着它那有皮无骨的脚步,岁月的巨手盘剥得它那绷紧的发条似乎也走到了尽头。
长兄麦成痛苦而沉重地把眼睛从母亲的脸上移到北地上的那架老钟,发出了一个声音,老二咋还不回来?这声音有些吃力而古怪,在场的人好像从来没听过,尽管那声音不大,却也听得清清楚楚,好像那声音不是她发出来的。疑惑之余,仿佛人们的眼睛都成了绿的。这声音让盯着母亲的所有绿眼再度涌出泪水。
青
麦根到达端庄已是凌晨两点。端庄是麦根的家乡,却不是麦根的村子,端庄是故乡的县城。母亲就是从县城的医院转回家中的。麦根家所在的村子叫李梁寨,在县城东北,距县城八十华里。李梁寨在等待,兄妹在等待,母亲更是在等待,等待麦根能跟她见最后一面。
时间如鞭在赶着麦根,母亲的生命在招唤着麦根,兄妹打爆了的电话在催着麦根。麦根是跑着冲出端庄站的。然而,瓢泼的暴雨给了麦根沉重一击!暴雨的万条巨鞭把站前所有裸露在天地间的人们都抽到了能躲避的地方。有人说这雨已下了三天三夜。真是十里不同地,百里不同天!
以往,无论在哪个时间段,只要有火车在端庄站停靠,只要无雨,出站口处的的哥的姐们就如苍蝇嗡嗡,招揽甚至争拉夺抢着旅客上车,嘴里叔、哥、婶、妹、如蜜地喊着,那甜度简直能沾掉你的牙!有时急了,雨水也挡不住他们拉客的脚步。今天没有,也许是因为雨太大,这些艰辛又可怜,挖空心思、搅尽脑汁、不择手段、不遗余力、千方百计去掏旅客钱袋子的出租车司机们都躲进各自的车里去了。大雨也把他们的车窗给封严了。一辆辆车仿佛一只只古怪的船漂泊在雨水中。
以往的打工生涯中,麦根也多次遇到过火车晚点,却从未赶过夜间回家,更没遇到过这般的瓢泼大雨。没说的,今天赶到这一步儿是逼上梁山,必须打车回家了,不然那八十里山路,在这瓢泼大雨中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徒步而赶的,况且危病的母亲在招唤,他不能负罪再耽搁时间了!
麦根冒雨钻进一辆出租车,说明去向,司机张口要价一百四十元钱。这让麦根大吃一惊!说,即便夜间行车最多不过六十元,况且天要亮了。
司机说,哥们儿,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天儿,你当是搂着小姐开房玩“划船”呢?何况去李梁寨全他娘的是难啃的山路,一百四十元是看你冒雨又心急,不然再加一倍也不去。麦根没有多话,脸却青了。青了脸的麦根钻出这辆车又钻进另一辆。不多会儿还是钻出,奔了第三辆。不知这第三辆司机要价几何,麦根没再出来。于是,那车开启雪亮的大灯,转出广场,消失在茫茫的黑色雨幕中。
紫
大约凌晨三点,麦家的母亲忽然睁开眼看了一下窗外,似乎是在看外面的天是否亮了。她的嘴也张了张,但终于没有发出声音来。在场的人不知道她想说什么?是想喊麦根?还是想吩咐交代什么?所有的人不得破解。其实母亲的嘴张得很小,眼也只开一条缝。但她向窗外看什么呢?不由得人们的眼睛也瞅向窗外。窗外的天还没有亮,也没有呈出蓝色,更不要说鱼肚白。最多那也不过是浓浓的紫色。外面的雨依然不肯退去,不知道它们要干什么?
母亲生命之线的最后一丝终于断了,心脏停止了跳动——麦家母亲走了!但她的眼依然那样微睁,嘴微开。看样子麦家母亲的离去没有多少痛苦。但她未合的嘴眼告诉人们她有未了的心愿!是的,她终于不能和她牵心连肺盼而未归的心爱的儿子麦根见最后一面,说最后一句话。就这样,麦家的母亲带着遗憾和万千的未表之意,举着沉重的脚步走上了西行之路。她留给儿女们的也是很多很多!
顿时,麦家那座低矮老旧的石屋里悲鸣爆起,顺着长子麦成推开的窗子荡了出去,飘进雨幕。悲鸣中,长子麦成没忘了给弟弟麦根打电话,可是,这次只听得电话中一声声的“嘟嘟”响,却无人接听。
黑
尖嘴猴腮的的哥,拉着瘦高苦痛的麦根,冒雨伴黑行驶在麦根的归乡之路,内心十分忐忑!因为这雨中的山路实在难行,有几段坑洼路面,泥水积得太深,车陷进去,如一头古怪操蛋的倔驴,怎么也不肯出来,急得那个的哥的三角脸更加三角儿,嘴里连珠般不停蹦出污词秽字,如精神病院跑出的患者,老辣似受惠于高师, 抒情若蹩脚的诗人,内容全是诅天咒地的。同时他还没忘了对麦根大喊大叫,哎,你说管你要那些钱多么多么多么,恩?要知这样,打死老子也不来!几经周折,加上泥猴儿般的麦根助推,车总算如丧家之犬爬了出去。然而在另一处盘山斜坡,车险些滑下山谷。那一刻两个人的心都揪出了嗓外。死里逃生后,车主想调头把车开回去不干了,却又舍不了那笔黑了心的钱,余下的路只好应着头皮了。不过此时的他更加两眼如炬,死盯前方;两手似钳,几乎就要把方向盘攥碎了,不敢疏忽须臾。
麦根的心也依然悬着,一悬路,二悬病危的母亲不知现在什么样了?他不知道母亲能否坚持到他进家那一刻?
可是这时,的哥和麦根都看见了:一股巨大的泥浪从他们眼前的山体疯狂地奔下,瞬间,伴随着轰隆隆巨响,他们眼前变得一片漆黑……
那是山体滑坡,那是泥石流,巨大的泥浪覆盖了他们的车并推向山谷,那声音,如群狮狂吼;那泥烟,若浓雾久而不散……麦根的这次回乡之旅,在最后一程,以一百四十元行驶八十华里昂贵价格和生命的代价,落下了最后帷幕。
数日后,刺眼的阳光照耀着一面青山的两座新坟。一年轻清秀女子,在两座坟前哭得死去活来。哭着哭着,眼前一黑,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苍天立刻举起那架老旧的相机,按动了快门,记录下了这人间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