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的战争
徐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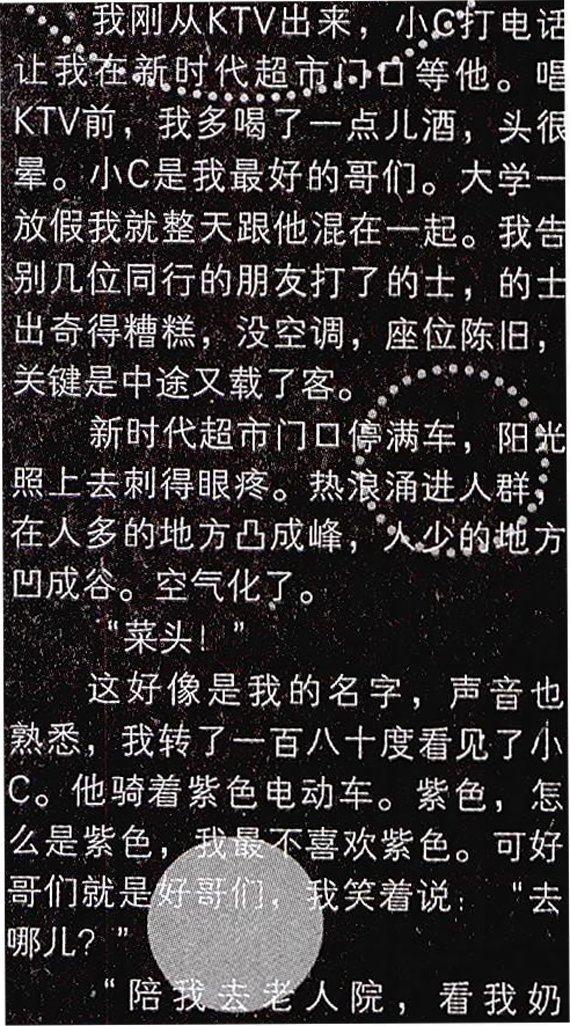 奶!”我明白他说话的内容但不明白他的语气。“我也不想去,我妈非让我去。我放假刚回来,我妈就唠叨着让我去看她,说他们工作忙,抽不出多少时间。”我彻底明白了。
奶!”我明白他说话的内容但不明白他的语气。“我也不想去,我妈非让我去。我放假刚回来,我妈就唠叨着让我去看她,说他们工作忙,抽不出多少时间。”我彻底明白了。
我不知道老人院和敬老院有什么区别。
“老年人进老人院要花钱,而敬老院不花钱。”小C说。我这哥们实在,总能抓住问题的实质。
“要钱还去,为什么不住在家里?”其实我并不想去,只是抹不开面子。
“她眼睛不好,和爷爷也合不来,三天两头地吵架,她总觉得爷爷嫌弃她了。前年,自己提出要求住进老人院。”
老年人还吵架,吵架也不至于分居。真是个怪老太婆,可我没开口。
他奶奶是怎样的人我都不在乎,我只是在乎跟小C在一起能让我舒服点儿。
路口往西是老人院,小c掉转车头往东骑。
“买点儿水果。”他忙说。我跳下车感觉重心上浮脚跟不稳。我们走近水果摊,水果被太阳晒得毫无光泽,就像卖水果的女人,眯着眼,头顶块毛巾,翘起上嘴唇,枯黄的头发拖拉进嘴角。
“苹果怎么卖?”
“买些软的水果,老年人啃不动苹果!”我不注意地说出口,可能是看到卖水果女人带黑斑的牙想到了小C奶奶才说的。
穿过大片的绿荫,老人院里一色的两层小楼。
”别墅呀!”我醉意完全消失了。小C龇着牙说:“别瞎说,什么别墅,就二层小楼。”
“要是在市郊区,那就是别墅!”上了楼,我补充道。
二楼右拐的屋里摆了三张床,屋尽头有张梳妆台看不清什么颜色,灰窗帘里漏进少许的阳光。屋里只有一位老奶奶,佝偻着腰,双手揣在袖口里。我想就是她了。小C走过去,老奶奶脖子往上均匀分布着老年斑,左眼浑浊显乳白色,感觉随时会有液体从眼里流出来。小C问寒问暖之后说:“奶啊,我妈说上周她给你钱,你怎么……”
“哎,这么大岁数,用那么些钱做什么?”
“他们一个月给我五六千,我上学也不花什么钱,给你钱,奶拿着。”小C道。
“你看,”她从枕头下掏出卷着的手帕,打开,里面是几百块钱,缓声缓语地说:“公家发的钱够用了,前天王书记还拿了四百块钱给我,够用了,我还能存一点儿。你们谁来都不要给我钱,常来看看我就行了。“说完,老奶奶转向我,我不敢抬头直视她的眼睛,低头看地上露了缝的布拖鞋。我认真观察它们的形状并未在意她们的谈话。
“这是……”老奶奶用手指着我,我很勉强地笑笑。小C介绍着我时说的都是老人爱听的话。接着,小C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下去。我也沉默了。我猛地想起在哪本书里看到的这样一句话:“代沟,永远是在沉默中被推向极致。”
“您的眼睛……”话说一半,我就后悔了。她平静地看我一眼,似乎并不在意我的话。她艰难地弓起腰,从床头柜里拿出两个苹果给了我和小C。“我来拿刀。”她下了床,想站得更直一点儿却没有办到。我上前帮她,她直摆手说:“你坐,你坐着。”她固执地弯着腰,艰难地一步一步挪到梳妆台那里,取了水果刀。
“我的眼睛看不见哦!”她回到床边说。
“看人很模糊,看不清,总是有重影……”她又重复着说。
“我的眼睛是被弹片划坏的,那弹片,后来部队里的人说,还是美国造的,只听‘轰地一声……“她举高双手在头顶挥摆着,又说,“我的亲乖乖,脑子嗡嗡直响,怎么说呢,就像把整个头扣进马蜂窝里,”说到激动处,她情不自禁地把双手围成圆状套在头上,“我以为自己已经死了,可我还能站起来……一摸脸,满手的血l”老人不自觉地在脸上摸了一把,脸上一时间有了生气的神态,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硝烟弥漫的战场。她握水果刀的手背上突起两根暗黑的血管。
“身边的人全倒在泥坑里,子弹‘啾啾啾地飞跑,咬住一个,人就倒下了。连长一把推倒我,也亏了连长,要不是他我也就被打死了。”
“您参加了战争?”
“我的眼是在朝鲜战争时弄坏的。在一片树林里,遇上了突袭。好些个美国鬼子都抱着重机枪……”她说得很坚定,但丝毫没有愤恨的意思,她眨了眨左边不见瞳仁的眼晴。我以为她会借题发挥,像无数老年人一样不厌其烦地讲自己的风光往事。我做好耐着性子听下去的准备,可她只说到在后方治眼睛就沉默了,转而关心地问起我们的生活情况。
临走时,老奶奶想摸摸孙子的脸,摸完后把手伸向我。我犹豫片刻摘下眼镜,侧过身子握住她的手。那只僵硬衰老的手让我闻到廉价护手油的味道。她先摸我的两颊,我分明感受到手掌间的粗糙纹理,掌心是湿的。我觉得痒,忍不住笑出来,她的手停住了,也笑起来。她在我脸上捏了捏,我忍住不笑。
“痒痒。”我说。她的手指粗硬得像一根朽木棍,她的食指和中指滑过我的额头,滑过鼻梁在两腮处停下。我轻轻地松开她的手,她按了按我的肩膀,又拍了拍,咧开牙齿掉尽的嘴,说:“挺壮的!”
她张开的嘴巴,像一口无底的不再有泉水滋渗的枯井。
几个月后,小C打电话给我,说他奶奶去世了。是在夜里面,一个人静静地躺着,换了一床新的床单,吸进了最后一口气,她是很安详地走的。我当时坐在靠窗的桌子上吃番茄炒鸡蛋盖饭。楼下一群野孩子疯跑着踢皮球。黑幕沉沉地降临了。
我并不感到悲伤,只觉得脸上凉凉的,仿佛她的手又拂过我的脸,仿佛又闻到廉价护手油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