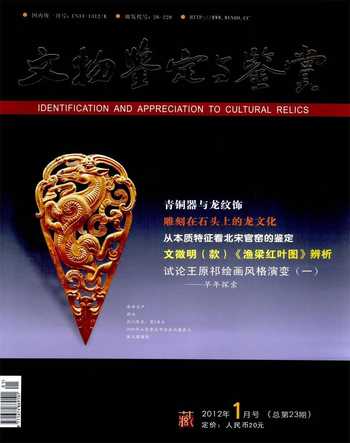修复与“司命”
周丽丽



2003年,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原美术史系)第一次尝试性地将书画修复纳入到研究生教学中,书画鉴定与修复研究相结合,形成一个新的学科方向,导师组为薛永年、冯鹏生、赵力三位先生,我有幸忝列门墙。应该说,修复进入研究生教学在国内实属首创,自此之后,国内多所高校陆续开设这一研究方向,如南京艺术学院、吉林艺术学院、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等。而由冯鹏生先生主持的“书画装裱与修复研究”也成为中央美术学院热门的重点课程。经冯鹏生先生的多次创举,方将书画修复这一传统的、经验性的实践技艺逐步提升为实践与理论并重的研究性学科。当时的课程设置有装裱史概述、历代装裱形制分析、装裱经典原著解读、书画材料研究以及装裱技法实践等,其他如“书画鉴定方法”(薛永年先生讲授)、“美术史学史”(罗世平先生讲授)、“文化遗传学概论”(李军先生讲授)、“明清地方画派研究”(赵力先生讲授)等课程均与之相关联。当然,今日看来,这些课程远不够健全,但冯先生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技艺、丰富的经验使其尽可能完善,而且,在实践操作中,他从大处着眼、小处抓起,严格要求,包括调糊、用糊,执刷、用刷,辨纸、配纸等等,甚至具体到擦案的动作、方向等,具细人微,严格督促初入门学生养成良好习惯,并时常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之句警示修复中可能出现的风险。
回过头来看,书画修复自古便是以家族相传、师徒相授的方式进行。虽然文革之后,国家文博机构也集中开展过一些培养或培训,但要么时间太短,要么仍限于派户之别。在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期,书画装裱与修复行业却因着两个主要原因落人低潮:一是很多经验丰富的老先生相继去世,后继者要么畏于此道艰辛而转行,要么则南于薪酬待遇而远走海外,导致行业后继乏人,青黄不接;二是由于市场冲击,不少人学得皮毛,便偷工减料、批量流水,甚至利用机裱覆膜,使择料精纯、制工细致,并强调人文素养的传统技艺沦为粗制滥造。另外,当代艺术家对于作品装裱、保存缺乏认识,纸绢等材料生产厂家趋于粗简,亦都导致此行业逐渐走向衰退。如今,同内文博机构中精于此业的高手屈指可数,专业行亦不过百人,且年龄断档,承传不力,然而破损待修作品何止千万,书画装裱与修复行业的整体发展不容乐观。可以说,此传统技艺进入学院教育,不仅是应时之举,也是必然之需。
当然,一门技艺成为学科,不仅意味着技艺的传承,更需着眼于学理的探究。在我看来,除基本的技艺入门之外,有三点尤为重要:其一为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与操守;其二为修复理论的广泛研究;其三为学科交叉与综合素质的培养。可以说,这一专业方向服务的对象决定了其人才培养的高端性与综合性,如果仅仅是学校考虑多一个专业方向吸收生源,学生考虑多一个谋生手段,这样的培养方式则另当别论。
谈了书画修复教育,再来谈一谈修复理念。谈及修复理念,众所周知的便是“修旧如旧”的行话。此理念虽在我国文物修复界有着极为广泛的传播与应用,但争论也极大。
坦率地说,修复实践与理论之间的距离实在是很大。长期以来,我们仅仅把修复看作为一种纯技术性的行为,是一种针对残损作品的“手术”操作,而且是少数特定技术专家的工作。日常在面对一件待修作品时,往往缺乏很多的前期工作,包括检测分析、理论论证等,如修复对象保存的现状如何,承载着哪些信息量,是否需要修复,是否复原,是否去除本体以外的附着物,是否需要补强或加固等,这些都是我们修复首先需要研究的问题。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如果复原,复原的依据是什么?复原部分与原物部分是协调还是对比?复原的可识别程度怎样?如果要恢复原貌,那么什么是原貌?如何理解原貌?如果决定要清除文物本体以外的附着物,那么哪些是应该去除的,哪些是有害的附着物,那些是无害的附着物?如何去清除?如果对文物本体要进行补强或加固,那么如何去补强或加固?是用传统的方法还是借用现代科学技术?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将困扰我们。思考得越深入、论证得越透彻,修复实践才可能进行得有根有据、合理科学。
的确,“修旧如旧”这一原则传播与运用相当广泛,但实际的修复结果却由于领会这一原则的差异而不尽如人意,要么是修复主观性过强,所谓复原的“旧”仅仅是修复者个人对“旧”的理解,丢失了修复对象所保存的信息;要么变“旧”为“新”,而修复出来的“新”完全没有道理,成为“假古董”;更有甚者,完全不是修复文物,而是严重的破坏。这样令人痛心的修复不仅屡见不鲜,而且还在不断地发生着。何以至此?简单来说,“修旧如旧”中的“旧”可以导引出“原初的旧”与“现在的旧”两种含义,如果是前者,在修复中则须使文物恢复到最初的原貌或者“当年在造型、装饰最有价值时的面貌”,而最初的原貌到底是怎样的呢?可能是“新”,也可能是无从寻觅,在具体的修复中,修复者总是根据各自不同的理解去想象,“修旧如新”、“金碧辉煌”以及各种不同想象的原状恢复均可能出现;如果是后者,在修复中就应该是“修旧如现”,尊重在历史长河中由于各种自然、非自然力量所形成的一切,这一观念则易导致“反修复”的消极思想。
作为修复原则,不管是总体评价原则还是技术措施原则,“修旧如旧”都体现出自古以来中国人对于完满、对于理想境界的追求,但同时,从概念上来说,它也存在着意义含混,模糊不清,容易引发歧义。对这一原则的分析,并非完全否认其在文化语境中的合理性,只是对经常以此为口号,而忽视具体问题的修复者的一种提醒。在现代文物修复实践中,需要对这一原则进行更加理性、严谨的科学分析,针对不同类型的修复对象以及出现的实际问题采取具体的修复措施,而不是简单化地以此为绝对指导方针。
公众的关注与争论一方面反映出修复原则与具体实践之间出现的问题,但同时也将有利于促进修复事业朝向更为科学、理性的方向发展。对于文博机构的藏品而言,均为大众所共有,在尽可能延长藏品寿命、流传后世的同时,也是为了使公众更好地欣赏。因此,修复不仅仅是保存科学专家、修复专家、艺术史专家、文化学者等等的职责范畴,它还应该具备更为广泛的公共性和透明性。正如有学者指出,“任何修复活动都有可能构成一种对艺术品原状或原意的把握与干预,有可能纠正或复原相关的感知与理悟,但是,也有可能因为热情过头的修复而形成‘破坏性的保护的事实,或者酿成千古遗恨,使得艺术品的面目全非,或者是严重地偏离原作的气象,貌合而神离。显然,艺术品修复的具体效应绝对不能小觑。它所吸引的注意力以及相关的争议往往有可能构成种种文化事件的焦点。”是否能将艺术品修复
当作一种文化事件来对待,既可以见证特定社会中人们的审美趣味的高度、修复的重要程度,也反映着人们对有关重大文化财产的觉悟水平。
那么在古代书画修复中,是否也存在着“修旧如旧”的解读与实践?
明人周嘉胄《装潢志》提及“复还旧观”、
“补处莫分”,与装裱修复界经常谈到的“天衣无缝”,都表明古书画修复也是一种典型的“复原性”修复理念。这一理念在洗、揭、补、全四个主要技术环节中都有着具体的体现:洗淋去污主要是针对书画物质层作辨证地处理,去掉有害物质,保留书画形象层应有的面貌(包括部分色彩由于化学反应产生变化的复原,尘埃掩盖的清除),保留由于时间在书画物质层形成的自然古旧色泽、光泽及气息;“揭裱”是书画载体由于装裱中的粘托需要、在修复中就相应产生的中间技术环节,是补全前的必备工序,在具体的操作中绝对不能损害原书画物质体及书画之意;补是针对书画物质层的残缺及破裂,寻找相似的材料进行补缀,力求完整,看不出破绽,既是出于长期保存、防止再次破裂或扩大残缺的必要措施,也是为潜在的完整书画形象层提供基础;全色与接笔则是在已有的完整物质层基础上,求得形象层的完整及与原书画气韵的和谐一致。整个“复原性修复”的精髓可以归纳为“自然”二字,体现为形象的完整和气韵的和谐,更具体到色泽、光泽、气息之上,如物质层原汁原味的古色、古味及包浆,如补残缺所用的纸绢,在材料的质地、组织结构、老化程度、颜色层次等与原画心的相似上都有严格要求,补缀之后,残缺处内外形同一体,显得自然,其好比“织补”衣服上的破洞,要求修残补缺使之无痕,在接笔补色上顺从原作,所有一系列活动都围绕着“补处莫分”、“天衣无缝”这个理想目标而进行。
古代书画流传至今,大多经历了不同程度的修复,对于一般观者而言,高超的修复技艺的确使我们很难辨别哪些部分是经过了全补,哪些是原来画意,但是,这样的修复难免让观者产生怀疑:即全补之处是否合理,根据是什么呢?
通常我们从展览或画册中领略先贤的妙笔佳墨时,分辨不清哪些地方是后人接添的,顺理成章地误将整个画面都认定为原作。这对传承古书画艺术的真正精神恰恰是一种误导。因此,在全补之前,我们要对两个环节进行辩证地考量:“全补”是否必要?“全补”是着眼于哪些群体的需要?如果“全补”,其依据何在?“全补”后应该达到怎样的效果?
从维护艺术的真实性而言,其弊端为:残缺内容的接补难免会产生一些偏差;不仅在笔墨上容易失真,甚至在内容上也会出现有悖于作品原貌的“标新立异”。当一件绘画作品所描绘的人物形象完全缺失,或一株树木只剩树干,怎么能够准确无误地补全人物、判定树木有几个树枝、几个分权呢?如果一味追求画面完整,并遵此原则,揭裱一次接补一次笔,那么,一件作品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呢?从许多传世古书画作品可以看出问题所在,“全补”到“天衣无缝”的效果使当前的修复混迹于过去艺术品具有的永恒性中,使历史的真实面貌与令人所作含混不清,既不利于今天的文物研究,也完全可能让我们今天的修复成果成为后人的考古对象
对于研究者来说,书画本体所有信息的真实性可能是他们最为关注的;对于一般观者束说,则是“众口难调”,既需要看到书画本体真实的状貌,也许还有着完整性的审美诉求。如果一件书面作品满幅残破,补缀材料的颜色与原画心色泽相去甚远,那么势必会使观赏受到影响,参照“文化遗产”的三种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来说,艺术价值足传统书画承载最多的,因而,审美的诉求也需要得以满足。但书画形象层缺失的情况是多样的,在“全补”时,可以尝试分为“有据可依”和“无据可查”两类。
“有据可依”:可作“全补”,在工作之前一定要对所修复作品的历史文献资料及艺术风格进行研究,绝不能凭主观想象去臆造或创造。“全补”时,尤其要注意与原形象层相接处不可覆笔于其上,“全补”的痕迹与原形象层略有区别,根据修复对象的使用功能,灵活掌握区别的程度。如目前传统书画的展览一般以玻璃隔开距观者约50厘米,“全补”痕迹与原形象层的区别度就可以考虑这个距离。
“无据可查”:则绝对不能“全补”,可以考虑在临本上进行“全补”尝试或利用电脑等科学设施进行模拟复原。
在这种历史信息真实性及审美要求完整性的平衡中,修复后的展观也可以提供一些参考,比如展览的书画作品经过了“全补”,则可以用图片或电子信息的方式向观者展示“全补”前后的状貌,一方面可以满足多种诉求,另外也让修复工作公开、透明。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许多先进的科技设备开始进入修复领域。比如清洗装置、超声乳化修复仪等等。但真正与修复具体操作技艺结合非常紧密的科技设备还是非常有限,主要还是一些工具材料。我个人以为,修复的具体操作更多还是需要以人本技术为主,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更好地提供科学性与便利性,不能盲目依赖。并且科技设备的引入和使用要有明确的针对性和阶段性,比如修复对象的环境监测、监控;修复具体操作前的病理检测、材质分析等,修复后的静态与动态档案建设等,这样的应用在业内多称之为“保存科学”,其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对科技设备要求很高。
前一个月我正好出差去日本,考察他们保存科学方面的设备与技术,感触颇深。在古书画修复方面,他们仍然延承自唐代从我国传过去的传统修复技艺,基本流程与国内大体一致,只不过结合日本和纸、绫绢等材料的特性,在一些工具材料和细节手法上有略微差异,裱式风格上也反映出不一样的审美趣味。但是,在传统修复技艺之外,他们在修复前很好地利用了现代科技设备,例如,文物三维扫描仪、分析走查电子显微镜、X线透过摄影装置、有害生物处理装置、真空冻结干燥装置等等,对于待修作品的病理状况、材料特性等等都有细致入微的分析,并结合电脑设备,做出完整而系统的参考数据。传统技艺与科技手段这样的结合也许正是我国文物保护努力的方向。
我们谈了书画修复的问题,那么修复与当下极热的书画鉴定又是否有联系呢?
书画鉴定与修复之间的关系,早在张珩、杨仁恺、徐邦达等诸位前辈先生的著述中就多有谈及,也举出过许多与修复相关的鉴定实例。简要来说,鉴定与修复两者都是综合性很强的学科,而且两者也相互交叉。学习鉴定,将有助于在修复中对作品整体气韵、风格特征的把握,可助更好地恢复作品的旧观;而学习修复,将最为直接地接触书画材质本身,在修复中与作品的朝夕相处对于鉴定的感性经验的积累大有帮助。如果将鉴定分为物质材料鉴定、理论文献鉴定和艺术风格鉴定三个层次,那么,修复中对物质材料的把握与认定将是第一手的,也是最为科学和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