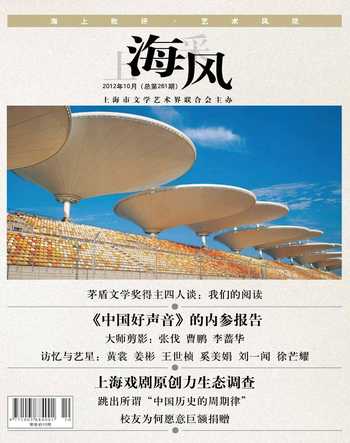李蔷华:未开言思往事慢慢细讲
秦岭



为了完成这次的访问,我前前后后到李蔷华老师家里叨扰了三次。头一回因为路不熟,最后还是劳烦李老师在电话里亲自给我指了方向。电梯刚到24层,就看见走廊那头李老师家的铁门已然虚虚地开了一道,“这边儿、这边儿!”她微笑着站在门口冲我招手。
李蔷华老师如今居住的这套位于徐家汇路上的公寓,是儿子关栋天1999年为她购置的,朝南的客厅十分敞亮,透过薄布细花窗帘间的缝隙,从窗口向外眺望,是现代上海繁华并繁忙的城市风景。李老师拉着我在客厅中间的大沙发上坐下,自己又忙着转去厨房,要给我倒茶。“水总是要喝的。”看到我一脸惶恐地跟了过去,她摆了摆手,果断否决了我的谢绝。“哎呦,小心烫。”回身将白色磨砂玻璃茶杯双手递到我手里的时候,又这样细心叮嘱。一圈忙活停当了,这才端着自己常用的那只红色马克杯,在我左手边坐下。“年纪大了,不好收拾,家里乱糟糟的。”这当然是她的客气。不过面对房间里上上下下摆放着的许许多多拍摄于不同时期的照片,我确实有那么一点儿小小的惊讶,简直像是误闯了奇境,蓦地跌入岁月的长河里。那天李老师的妹妹李薇华刚巧也在,一起坐了一会,拉拉杂杂地聊了不少少年时代的往事,直到俞振飞先生的学生李松年偕同夫人王苓秋前来师娘家探望。临了,李薇华老师还把我送到门口,问我回去认不认得路,叫我千万路上小心。
这第一次的见面,给我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后来跟李蔷华老师聊得熟了,更是在这温暖与亲切之中,又生出些欲罢不能的感觉。一切正应着程砚秋先生在《金锁记》里的那句唱:“未开言思往事慢慢细讲”。后来,我吃过午饭就到了徐家汇路,家里只有李老师一个人在。她还像上次那样端上一红一白两个茶杯,我们也还像上次那样彼此相侧而坐,对着满屋子的相片,从午后一直谈到快要天黑。回想起来,整整四个小时的时间仿佛转瞬即逝,武汉、重庆、成都、昆明、涪陵、南京、上海、长春、台北、香港……我几乎跟随着她的人生足迹,凭着想象将整个中国跑了个遍。那些尘封故事听起来仿佛离我非常遥远,却又似乎相当切近,其中不乏如雷贯耳的伟岸名字,也有早已湮没无闻的孤寂身影。重要的是,正是在她那绵长而细致的叙述里,我又重新认识了那些曾在她的生命历程中留下过重要印记的人,窥见了他们最真实也最可宝贵的那一面。
采访开始之前,我就老老实实对李老师讲过:戏我看得少,不懂,也不敢装懂,要不我们多聊聊人吧。说这话的我,确实也抱有一点微妙的小心思,想着能不能也学着前辈的样子,把那些属于梨园的老底子的片段往事,照着原样整理出来,说给那些不看戏的人听。
幸运的是,这一次,李蔷华老师是真真正正地满足了我的愿望。
[注]本文凡谈及年龄,一概遵循李蔷华老师自己的讲法,用的都是虚龄。
【棠棣与蔷薇】
“我本来不姓李,我姓熊,我叫熊瑞云。我母亲一共生了四个孩子,我们现在的名字都是我继父给我们取的。我大哥叫李棠华,妹妹叫李薇华,小弟叫李棣华。棠棣、蔷薇,寓意兄弟姐妹。”
李蔷华出身的那个熊家,在当年的武汉,曾经也算是一个相当殷实的人家。她的祖母娘家是武汉著名的刘天宝药店的主人,即便是如今的武汉街头,也依然可以见到“刘天宝”的名号。她的外祖父秦朗斋则是当地有名的中医,就算谈不上富庶,至少也是衣食无忧。
“我做女儿的其实不应该这么说,但是我亲父这个人呢,确实不是一个能负起家庭责任的人。”李蔷华的亲生父亲是一个标准的纨绔子弟,没什么本事也不求长进,到了他的手上家道终于败落,慢慢地,连最基本的生活都开始变得捉襟见肘。父亲曾经计划着以200块大洋为价,将李蔷华卖给海关上一个姓潘的人家做童养媳,最后是她的母亲以死相挟,拼着命才把她留了下来。长她两岁的哥哥李棠华便没有了这样的幸运,8岁时候被“写”给了上海杂技团的前身、潘玉珍童子团,从此杳无音讯,直到抗战胜利,李蔷华和母亲千方百计找到上海,这才最终得以母子团圆。“所谓写给人家,命就在人家手上,跑了病了打死了不论的。”李蔷华说,“现在杂技界很多人还都认识我哥哥。我哥哥现在住在台湾,李棠华杂技团就是他创办的。”
为了养家活命,李蔷华的母亲去学了山东大鼓。她带着剩下的三个孩子加入了曲艺队,一路表演,前往重庆。那一年,李蔷华9岁,妹妹李薇华6岁,小弟李棣华只有3岁。
当时正值抗战前期,作为大后方的重庆戏曲演出市场相当红火。通过演出,母亲终于重新积累起了一些积蓄,日子也渐渐宽裕起来。她于是领着李蔷华姐弟三人去照相馆照了一张相,寄给当时尚在武汉的李蔷华的亲生父亲,告诉他她们在重庆生活得很好,让他过来跟她们一起。“我父亲收到信之后,就回信告诉我们会搭什么时候哪班船来,可结果我们却听到消息说,那班船被日本人的飞机给炸了。我们都以为我的父亲死了”——“以为”的意思,当然是事实上并没有,然而这些已经是后话了。
“无论怎么说,他总是我的亲生父亲。可是过去的那些事,一是我哥哥被写出去,二是我父亲要把我卖去做童养媳,这些烙印在我心里是很深很深的,也是很疼很疼的。可以说,它影响了我的一生。”李蔷华说。
就这样,9岁的李蔷华在重庆开启了自己的学戏生涯。那时候也没什么明确的行当,老生、老旦、花旦、刀马旦什么都学,“我没有童年,就是练功唱戏吊嗓子。”12岁的时候母亲改嫁,她在继父李宗林的指点下,专心研习程砚秋的程派戏。1942年,14岁的李蔷华在成都挂二牌演出,半年后又回到重庆,挂头牌。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她和妹妹到处跑码头,继父拉弦教唱,母亲则负责剧团上下的打点,由此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
“从小我就和薇华一起唱。我缺什么,她就给我配什么。我唱花旦戏,她唱小生;唱《骂殿》,她唱老生;我唱《女起解》,她就唱崇公道,来个小花脸。那时候我的戏都是她配的。那时候她还小,比我还矮半个头,刚开始连椅子都够不到,还得抱上去。”而这对以“蔷薇”命名的如花姐妹,后来也终于成就了戏曲史上一道明丽而传奇的风景。
1951年,荀慧生率团来上海演出,李薇华慕名前往,随后便拜了荀慧生为师。1958年,她加入荀剧团,每到一个地方演出,荀慧生总是让李薇华先演三场,接着再由自己出马。有学生登门向荀慧生求教,也一概全交由李薇华代为传授。“她的荀派唱得可好了!”李蔷华眯起眼睛笑着,口吻异常骄傲,“荀先生的四出戏:全本《得意缘》、全本《花田错》,还有《卓文君》和《钗头凤》的录音片段,音配像都是我妹妹给做的。”
【最好的继父】
“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其实是我的继父。他人很温和,也很有修养,是个很好的人。没有他,就没有现在的我。”
李蔷华的继父李宗林是个文化人,拉了一手好胡琴,跟名家高华、言菊朋一起票过戏。对李蔷华来说,“师”、“父”这两个字,在他身上是一体的,“是他培养我开始唱青衣”。
作为“业师”的继父,对李蔷华学戏的要求很是严格。每天天不亮就催她起来练功,开把子,下腰,压腿,一套功夫练完了回来,便拉开一把椅子坐好,架起胡琴帮她练嗓。“我小时候是个‘回笼嗓子,本来吊了两出戏吊得挺好的,睡了个午觉起来嗓子就又闷了。于是我继父就专让我睡完觉起来再重新吊,一定要吊到什么时候唱,嗓子什么时候有。所谓的嗓子实际上就是功夫,功夫下去了嗓子就听你的话。”李蔷华说,除了教唱,他还教文化,“我一天书都没读过,读书写字都是跟继父学的。他教我戏,总是先写了唱词,然后指着,一个字、一个字地讲给我听。于是戏会了,我字也会了。特别是后来学到程先生的那些小本戏,言辞都非常文雅,我继父就一字一句讲给我听,这句是什么意思,那句是什么意思。对唱词的理解深入了,演出来的戏自然就有味道。”也正是在继父十多年的熏陶下,李蔷华终生都保持着读书看报的习惯,因为“只有懂得越多,很多事情才能看得明白、知道判断”。
李蔷华14岁的时候,因为听说成都的演出市场好,他们举家从重庆迁往了成都。在成都,李蔷华挂了二牌,开始了她真正意义上的京剧演出生涯。因为人长得漂亮,戏做得也漂亮,唱了半年,很受欢迎。钱和名声是挣到了,糟心的事情却也跟着来了。“当时有那么一个人,我也不好说他的名字,他想方设法,托人来做媒,跟我妈妈讲价钱,要把我要去。”就像当时的市井小说里写的那样,对方仗着钱势对他们一家软硬兼施。当得知李宗林并不是李蔷华的亲生父亲,便把李宗林单独约出去谈,只要他做主把李蔷华嫁给他,便保他后半生衣食无忧。李宗林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回来果断告诉李蔷华的母亲,成都不能呆。他暗地里卖掉了他们在成都的房子,想方设法找了一辆货车,一家人躲在货车的顶棚下面,趴在货物上,连夜逃回了重庆。
“我的继父对我、对我们的家庭,那真的是有恩的。你想,连我的亲生父亲都要卖我,可他却能完全为我着想。他的人格之高尚,别的不提,就说从我12岁,一直到1953年,我25岁,他脑溢血去世,尽管他对我们姐妹很温和很亲切,却从来没有在肢体上靠近我们一下。连摸摸手,说声‘乖乖儿都没有。为什么我那么敬仰他,永远记住他,就是在这些方面。”
【大风剧社】
“我第一次接触程派的戏,就是我12岁的时候。在重庆,看的是赵荣琛赵先生。感觉很大气,我一下子就被打动了。于是我跟我继父说,我就要学程派。”
那时候重庆的京剧舞台,最为活跃的大约要属赵荣琛的“大风剧社”。赵荣琛是一个演程派的高手,有“重庆程砚秋”之称。他和李蔷华的继父李宗林是好朋友,“赵先生的《朱痕记》就是我继父教的。”而赵荣琛凡有重要的演出,也总会邀请李宗林来为他司琴,继父上台拉琴,李蔷华便跟着过去,躲在一旁蹭戏。
“赵先生本人没有教过我戏,但我记得《三娘教子》还是《汾河湾》,我给他演过一次小孩儿。”
回忆当年混在“大风剧社”的日子,李蔷华忽然想起一件好玩的事情来。那时候剧团里有位先生叫张宝彝,李蔷华管他叫宝彝叔,他是赵荣琛在山东省立剧院学戏时候的同学,后来成为了有名的京剧导演,关肃霜那部荣获全国电影百花奖的电影戏曲片《铁弓缘》就出自他的手笔。当时大风剧社在重庆第一剧场演出,李宗林就让李蔷华跟着在那儿练功,而负责指导她的就是这个宝彝叔。“白天没戏的时候,他就让我们对着台边的大柱子耗腿,一直把腿架到脖子这儿,站成一直溜儿,然后再把你的腿直直地系在柱子上,就这样保持不动,耗腿。系好了,他就转到后台去了。那时候他正跟赵先生剧团的一个叫夏韵秋的刀马旦谈恋爱呢。他去后台谈恋爱了,可我这边正系着耗腿呢。结果我们等了好长时间都不见他回来,都快受不了了,在那边直叫唤。”说到这里,李蔷华终于忍不住掩嘴笑出声来,“印象特别深。宝彝叔人很好的,我把他当自己亲长辈看。他修养也很好,从来没有打过我们,顶多拿块板子轻轻敲你两下,吓吓你。”
【怎么是他?】
“这件事,我记了一辈子。”
1944年,李蔷华16岁,她去昆明演出,挑的是头牌。场子在云南大戏院,而她们一家就住在戏院对面的旅馆里。有一天她刚吃完晚饭,对面戏院催场的人就过来了,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咖啡色褂子,很低眉顺目的一个人。他哈着腰对她说,李老板,您该下后台化妆了。那会儿李蔷华刚到昆明,人头不是很熟,也不知道来人姓甚名谁,只听见继父脱口而出,暗叫一句“怎么是他?”催场的走后,她赶忙问继父那人究竟是谁,“我继父对我说,你不知道,他叫赵、君、玉。他可是上海的梅兰芳呀,厉害着呢!哎呀他怎么会沦落至此!”
这个赵君玉早年曾与有“伶界大王”之称的谭鑫培合演过《珠帘寨》《汾河湾》《御碑亭》等好几部戏,很受谭鑫培器重,又与梅兰芳合演过《五花洞》,更是声名显赫。在上海有过三楼三底的大房子。他好抽鸦片,连烟枪上镶的也都是宝石。
“你想不到吧?给我催场的,就是这样一个人。”
李蔷华在云南大戏院唱了半个月左右,有一天忽然听有人传说,赵君玉死了,就死在后台。那时候,李蔷华在后台是有单独的化妆间的,听到人说,就跑出去看。赵君玉平时就住在后台的一个小角落里,找了块门板做床,边上拉一道帘子也就好了。“那是块白布,脏得都已经灰了,他就死在那后头,而且是过了两天,人家才知道他死了,据说是连瘾带病。”
任你曾经是怎样的好角,嗓子没了,就什么都没了。“这个印象给我是一生的。它给我警惕了,不要染上任何的毛病,养成任何不良的习惯,不然就是自己让自己走上末路。”李蔷华说,“赵君玉,你得记下这个名字。”
【一幅小像】
“大概三、四年前吧,在天蟾舞台看戏,丰一吟刚巧就坐我旁边,看见我还认识我。她跟我提起当年丰先生给我画画的事情,这一提,我就全想起来了。”
那还是1944年,李蔷华16岁,妹妹李薇华13岁。她们在涪陵唱戏,而丰子恺则刚好也在那里办画展。丰子恺的女儿丰一吟是个戏迷,天天拽着父亲过来看她们演戏不算,最后还和父亲一起,亲自前往她们借住的旅馆拜访。
丰一吟曾经在她的那本自述中,讲起过当年的那次相逢。那时的丰子恺已经是有名的大画家,很受当地官员的敬重,而京剧演员却究竟只是下九流的“戏子”。听说丰一吟想见李蔷华,边上的人就说那很方便,叫她们过来便是。可丰子恺并不同意。
“‘不!请你打听一下地址,我们自己去访问。父亲决断地说。”在文章中,丰一吟这样写道,“……先是姐姐出来,我正看入了迷,妹妹也过来了。她从姐姐身后把双手插入姐姐腋下,抱住姐姐的腰,摇啊摇的,好天真啊!”
就是在那间小旅馆的房间里,丰子恺为李蔷华李薇华姐妹一人画了一幅小像,又各题了一首小诗,李蔷华的那幅是大青衣的扮相,妹妹则是小生的行头。继父李宗林是懂行的人,他把丰子恺赠给他们的诗和画裱成了四扇小屏风,放在他们家的案头上。然而人世变幻,数度沉浮,这珍贵的小屏风到底还是失落在了沧桑的岁月里。
“后来还是丰先生的学生胡治均,他那儿也收着一幅,和当初丰先生给我画的那幅一样,大概是丰先生另画的。知道我这边的丢了,特地又为我复印了一幅。”
【周长华】
“我这个人现在是爱说话,过去因为家庭的那些变故,性格是很内向的,我不喜欢唱那些乱七八糟的戏。而程派是很深沉很内敛的,我就唱程派戏。”
1945年抗战胜利后,17岁的李蔷华从重庆出发,沿长江水路来到上海。一年后,她在位于旧上海二马路的大舞台(今人民大舞台)连演了一个月的程派戏,剧目是《碧玉簪》《鸳鸯冢》和《青霜剑》。也就是这一年,在阔别4年之后,程砚秋的“秋声社”重返上海舞台,他在天蟾剧院连续上演了包括《锁麟囊》《春闺梦》在内的诸多名剧。也许正是这个机缘,让李宗林与程砚秋的琴师周长华见了面,彼此言谈甚欢,一见如故,拜了把兄弟,后来李宗林更是把周长华接到家中居住,请他帮忙指导李蔷华的唱腔,这一住就是三年。
“程先生在艺术上发展最高峰的那个时期,就是和周先生合作的这个阶段。当然周先生比程先生小,程先生就带着他。而周先生的智慧和功底,在程先生的唱腔上面,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因为有周先生在,就使得我在程派艺术的道路上,获得了很多有利的条件。”对此,李蔷华显然非常感念。在她的记忆里,周长华平日里喜欢喝点小酒,攒上一碟花生米,配一两个小菜,一边吃着,一边给她说戏或是讲讲北京老梨园的掌故。据说周长华从前最早是唱老生的,后来倒了仓才改拉的胡琴,所以演员在台上的一切,他都清清楚楚。程砚秋的词怎么唱,动作怎么做,水袖怎么甩,他全都说得上来。“周先生太聪明,肚子太宽了”。除了程砚秋本人之外,李蔷华是第一个把程派名作《春闺梦》搬上舞台的人,而这出戏就是周长华帮她排的。
程砚秋的琴师就住在自己的家里,所以李蔷华对于程砚秋的演出动态了若指掌。程砚秋唱到哪儿,她就跟到哪儿,程砚秋唱几场,她就听几场。有时候她自己有演出,她就和妹妹商量着,交换彼此的演出顺序,让妹妹挂头牌,自己唱压轴,为的就是能赶上他的大轴戏,“哪怕听不了全部,能听到一点都是好的。”那种痴狂的劲头,简直就像是疯魔了一样。
1947年,李蔷华在天津看完程砚秋的戏,周长华就带着她去了北京。在他的引荐下,她和有“通天教主”之称的王瑶卿先生见了面,并拜了师。要知道,对李蔷华那个年纪的演员来说,这样的机会本身就堪称奇迹。因为王瑶卿在戏曲教育方面堪称一代宗师,程砚秋能够扬长避短,创造 “程腔”,就是在他的直接指导下完成的。
“这件事过去我从来不提,照片也没给人看过,”李蔷华说,“因为照北方人来说,这个辈儿太大。梅先生也好,程先生也好,四大名旦全是王大爷的学生。”
既然说周长华,那就一定要提一提李蔷华当年的闺中密友,后来成为了周长华太太的“颖若馆主”盛岫云。盛岫云的亲祖父便是大名鼎鼎的实业家盛宣怀,大家都管她叫盛五小姐。盛五小姐的程派唱得极好,后来去了台湾,更是和周长华、高华、章遏云一起被视作台湾程派的代表人物。“过去我看程先生的戏,她陪着我一起追。我1947年在大中华灌《女儿心》的唱片,前面三句小生就是她唱的。”而李蔷华之所以选择唱《女儿心》,则是周长华的建议,因为他告诉她,这出戏程先生灌唱片的时候没有唱过。
半个世纪之后的1997年,李蔷华作为中国京剧艺术赴港演出团的代表,前往香港参加“庆回归京剧大汇演”。得知消息的盛岫云专程从台湾赶往香港与她相聚,只为再看一遍好友的《锁麟囊》。
【转益多师是汝师】
“过去上海有一份叫《罗宾汉》的小报,上面专门写一些文艺界的事情。我继父看到上面说徐碧云先生现在很潦倒,住在很远的郊区的小旅馆里,连房钱都付不起,结果他就找过去,把他们全家接了过来。”
徐碧云是著名的京剧旦角,他的哥哥就是梅兰芳的琴师徐兰沅。当年《顺天时报》发起选举最佳旦角新剧目的活动,最后当选的就是梅兰芳的《太真外传》、尚小云的《摩登伽女》、程砚秋的《红拂传》、荀慧生的《丹青引》和徐碧云的《绿珠坠楼》。见他潦倒,李宗林便同李蔷华的母亲商量,由李蔷华出资,花了八两金子,在当时的善钟路(今常熟路)上为徐碧云顶了一处住所,前后两间,徐碧云夫妇住在前楼,儿子和媳妇住在后面的亭子间。而李蔷华自己的家在大胜胡同,也就是现在的华山路251弄2号,希尔顿宾馆对面,两处相距很近。于是徐碧云就在李宗林的请求下,每天过来给李蔷华说戏,陪她练功打把子。“我继父对我说,徐先生虽然不是唱程派的,可是他的功夫好得很,学了对你整个艺术的提高都有好处。”就这样,李蔷华跟着徐碧云学了一年多的基础戏,打下了非常过硬的表演功底。
“我第一次演《春闺梦》的时候,就是徐碧云先生的儿子给我配的小生。行头也还是根据他的身材,为他现做的。”李蔷华说。
【要的就是名正言顺】
1950年,李蔷华22岁。她在上海国际饭店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婚礼,当时在上海的文艺界人士几乎都请到了。出乎时人意料的是,这场婚礼的另一个主角,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巨贾豪绅,却只是江苏省银行一个名叫丁存坤的普通职员。
那时的李蔷华,年轻、漂亮、才华横溢,甚至可以说是颠倒众生。多少豪富子弟众星捧月一般地捧她,鸽子蛋钻石直接往戏台上扔,可她就是不理。
“那时候的环境坏透了。而且我们唱戏的,总给人一种感觉,好像只要有钱就什么都能得到。我偏不。那些有钱人再怎么追求我,我都不答应。我一想到自己以后走出去,被别人指着说,这是谁谁谁的小老婆,我的孩子也会被人说是小老婆生的,我就觉得受不了。”李蔷华就是这么倔,她要嫁,就必须是明媒正娶。
如今回想起来,那确实是一种要命的骄傲。那种骄傲是过去的那些经历一点一点堆积起来的。李蔷华笑着说没准自己在骨子里其实有点看不起自己是个唱戏的,所以更要拼命把腰板挺得比谁都直,将自己放得比谁都高。她想要赶快将自己名正言顺地嫁出去,好断了那些人的念想,给自己图一个清静。
就在那时候,她认识了身为京剧票友的丁存坤,言谈之下也颇为投缘。听说丁存坤还没有娶妻,李蔷华便认定了丁存坤就是她要嫁的人。“那时候,他家的条件怎样,家里有几口人,怎样的房子,所有情况我都不知道。但我是下了决心的,我就做王宝钏了。”
为了嫁给丁存坤,李蔷华几乎把什么都舍掉了。她不顾母亲的反对,一结束在台湾的演出就只身回到了上海。“我母亲坚决反对我和他结婚。当时她瞒着我签了去台湾演出的约,原本是想就这样不回来了。”李蔷华说。去台湾,她行头道具外加各种物事,足足装了二十个大箱子,可回来的时候,除了手里拎着的两口皮箱,兜里揣着的一点路费,其他什么都没带走。
“我这个人就是个性强、认死理。发生在我身上的怪事多了。不过话说回来,没有这种心性儿也唱不了戏,因为根本熬不下那种苦。”
她说自己后来之所以会和丁存坤分开,理由简单得甚至有些好笑,因为她想重新出来唱戏,而丁存坤不肯。不肯?李蔷华的固执劲儿上来了,不肯,不肯就离。当时周围的朋友都忙着劝,不就是要唱戏嘛,陪她唱不就得了嘛,然而最终他们却到底没能重新走到一起。
“丁存坤懂戏。他唱是真的唱得很好。”李蔷华说,“后来他拜了杨宝森。现在很多人学杨派的都去找他学。天津的张克,在香港的时候就住在他家里跟他学戏。”
【在武汉】
“我在武汉参加国营剧团,拿的是保留工资。人家一个月拿三十二块钱的时候,我一个人就是六百五。也就是所谓的三名三高。”
1953年,告别了上一段婚姻的李蔷华也告别了上海,回到故乡武汉。在武汉京剧团她认识了著名的老生演员、马连良的高足关正明。两人于年底结了婚,开始了另一段全新的生活。
李蔷华坦言自己最开始就像许多从解放前过来的老艺人一样,对于“国有”、“社会主义”之类的概念并没有非常明晰的认识,“那还是后来通过不断的学习,才慢慢领会过来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也确实亲眼看到了变化。”
因为李蔷华自己就是武汉人,于是她就用武汉举了一个例子。1954年,武汉发大水,全武汉的人民群众都被动员起来修堤防,李蔷华工作的武汉京剧院也不例外,单位里的强劳动力都去了。如今依然屹立在武汉长江边的那道高高的江堤,就是那个时候集众人之力建成的。“我妹妹是1932年生的,我妈妈怀着她的时候就是武汉发大水,当时水大到都已经进了市里的二层楼了。新旧对比之下,思想上的触动还是相当强烈的。”
那会儿李蔷华正怀着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好强的她不愿意落于人后。男同志都被派去修堤,可戏总要人演。“我也满泼辣的,怀有八个月身孕,还要坚持演出。当时演的是《汾河湾》,戏里的柳迎春不是穿着一条小围裙么?我穿的还是程先生的围裙。因为一般演出的围裙比较小,遮不住,而程砚秋先生个子大,他的围裙是和褶子一样长的。我就穿着那个唱。该蹲下去的时候还照样蹲下去,只要戏演好,那些我不在乎。”
1957年,李蔷华的第三个孩子关怀(现在改名叫关栋天)出生。1959年,她入了党。
“当时我们家里条件那么好,对两个女儿我也是尽可能的把最好的都给她们,可独独是这个儿子,我对他是非常非常地严格。”说起来似乎有点叫人难以想象,一直到关栋天七岁,开始上学,李蔷华都没给他做过一件新衣裳。“从里到外,从单到棉,一件都没有,完全穿姐姐们剩下的。别人笑话他,我却说怎么啦,哪点破了哪点烂了,为什么不能穿?”
就在前不久,一次接受电视台采访的时候,关栋天突然说起了这段往事。李蔷华坐在镜头外的沙发上听。“我以为他都不记得了……他说当年觉得很委屈,到了现在,终于理解了我的苦心。他是我儿子呀,我当然心疼他心疼得不得了,可我必须狠下心去。就因为我们家当时有钱,我更希望他能吃得起苦。我不允许我的儿子将来像我的亲父亲那样。”
说到这里她忽然就沉默了下去,只是用纸巾不断擦拭着泛红的眼眶。
【恨死了】
“我不准我的儿子唱戏,他一唱戏我就生气。”
当文化大革命的红色海浪席卷而来的时候,像李蔷华这样的“三名三高”自然首当其冲,迎面接受来自“革命”的“文化”洗礼。
“那时候在戏校,我身上背着铺盖卷儿,手里拎着网兜,被几个人这么押着。一路押着走,一路喊口号,一直押到剧场里接受批斗。那种氛围啊,我跟自己说,只要事情搞清楚了,我再也不唱戏了,找个山旮旯里呆下来,我也不叫李蔷华了。”
可偏偏小儿子关栋天却是个戏瘾子。那时李蔷华家住在三楼,每次关栋天一踏进楼底下那个大门就扯开嗓子唱。“我一听他唱戏呀,我就恨死了。我想不通。”
李蔷华的反对所有人都看在了眼里,可关栋天的戏曲天赋所有人也都记在了心上。特别是父亲关正明,对这个天赋极高的小儿子疼爱得不得了。明着不行,就偷着来。关栋天溜去团里,李蔷华的那些老同事们也自发地帮着他练,“四人帮粉碎了我们又重新出来唱,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我儿子已经把功都练出来了。”
然而就像杨绛说的,乌云蔽天的岁月固然不堪回首,可是最终停留在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却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明面上我是专政对象,大家不方便说话,可是暗里,剧团的那些老同事跟我们一家都是很好的。”李蔷华不禁有些动情,“有时候外面贴着批判我的大字报,我站在那里看。那些老一辈的会悄悄靠过来,戳戳我,小声说,你别生气啊。到冬天了,造反派把我们关在牛棚里,还不给我们热水用,烧锅炉的萧嫂子就趁他们不注意,偷偷地给我们运热水。他们对我们都是很好的。”紧接着她又强调了一遍。
【京剧电影《二堂舍子》】
“那时候,我已经有十年没唱过戏了。”
1976年,还在牛棚里接受再教育的李蔷华突然接到武汉军区指派下来的演出任务。“当时说是要留资料,实际上是毛主席要看戏,中央派了一个工作小组下来专门抓这件事”,最开始唱的是全本《宝莲灯》,李蔷华和关正明被安排演出其中的《二堂舍子》一折。
演出在武汉军区内部秘密进行,工作组成员看完之后表示,前后都不要,只留《二堂舍子》。于是,李蔷华和关正明就被带去武汉电台录了音,结束之后,又通知到天津小白楼录像。“这个录像实际上是个样片。录完之后我一看,哎呦,不行。平时的舞台妆都是我们自己化的,毕竟十年没上妆了,手上都没数了,结果耳挖子戴得太下面,太难看了。我想想还是觉得不行,于是我就跟他们说,我就是一宿不睡也要把这个重录出来。”这就是老艺术家的顶真。通过层层审批之后,影片的正式拍摄定在长春电影制片厂进行,李蔷华、关正明,扮演戏中两个孩子的娃娃生演员高德春、高兴瑞,以及负责监督李蔷华关正明二人的工宣队同志,一行五人一起前往长春。
据李蔷华回忆,当时拍摄用的是一种叫做伊斯曼的胶卷,美国货,一卷据说要三万七千块美金。“好在我们拍得很顺利,一点儿也没有浪费。”李蔷华笑着说,“毕竟我和关正明对儿戏演了那么多年了。虽然那会儿我和他的关系已经不好,彼此都不说话,但是演出是演出。我们都不会把情绪带到戏里。”
那时候的李蔷华48岁。戏尾屁股坐子腾空而起,飞起两尺之高,变身盘腿硬落,下场跪步又快又稳,可谓唱做俱佳,十分精彩。她和关正明合作的这部影片,后来也成为了彼此戏曲表演生涯中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我们录完像,就各自回房间,等着第二天看成片。当天夜里,睡到后半夜我就被晃醒了。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可怕吧,我在长春都感觉到了。”
而谈及她和关正明的婚姻,李蔷华却觉得她也应该好好反思自己,“离婚前,我六年没跟他说过话,难道我没有责任吗?他不像别人说的那样。事实上他也是很好的人。他对他的师兄弟都是很好的,人家乡下的房子烧了,他就寄钱给人家,帮助他。我们毕竟一起生活过,这些我都非常清楚。”
【云从龙】
“云”是李蔷华的本名中的一个字,而“龙”则是京昆大师俞振飞的自署。在俞振飞与李蔷华结婚前后的通信里,他一直都使用着这样的称谓,因为《周易》中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云从龙风从虎,而这正是老艺术家的含蓄的浪漫。
追溯起来,李蔷华第一次见到俞振飞是1947年,她19岁,在上海马斯南路121号(今思南路87号),京剧大师梅兰芳的家里。当时梅兰芳最疼爱的弟子李世芳飞机失事意外离世,为了接济李世芳家人的生活,梅兰芳组织了一场义演,找来那时最有名的八位坤旦,联手演出《八五花洞》与《八美跑车》,而李蔷华就是这八分之一。
“跟我一起的是梅先生的女儿梅葆玥,顾正秋、于素秋她们。说起于素秋,她的父亲于占元就是后来香港‘七小福的班主,成龙、洪金宝他们的师父。”
那阵子她们八个女孩子每天都在梅宅练功。梅兰芳的太太福芝芳和俞振飞的太太黄蔓耘是牌友,“我们这边说戏,那边他们在打麻将。俞老穿着长袍子,翻出白色的袖口,两手往身后一背,就站在边上看。”
后来两人还合演过一次义务戏《铁弓缘》,李蔷华演花旦,俞振飞演小生。到了六十年代,梅兰芳、俞振飞在北京中国戏曲学院主讲《游园惊梦》和《奇双会》的时候,李蔷华是课堂底下坐着的学生。
“我是个演员,也是个戏迷。我敬重俞老的为人,也爱慕他的戏。”
1978年10月,李蔷华同关正明离了婚。俞振飞的学生薛正康和关正明是上海戏校学戏时候的同学,也许是从薛正康那里听说了李蔷华离婚的事儿,俞振飞给人在武汉的李蔷华写了一封信,内容大致是知道你离婚了,要保重身体,然后就讲起武汉京剧团当年的当家小生高维廉在文革当中出了事,他非常痛心,并想给李蔷华再介绍一个配戏的小生。
这封信李蔷华交给了武汉京剧团的领导,团领导没有批复,李蔷华便也没能给出回音。后来她回上海看弟弟妹妹,就住在妹妹家,那天刚巧袁美云的妹妹、坤生袁汉云过来,有事想托李薇华问一下俞振飞。“袁汉云原来跟我妹妹在镇江同过班,大家关系都很好的。刚好俞老那封信我没回,不回前辈的信总不太好,我就说那我跟你们一起去吧。”不巧的是,那一天俞振飞身体略有不适,接待他们的是薛正康。
过了不久,薛正康就给李蔷华去了一封信,说想给她和俞振飞做个媒。“我跟他也不客气,就回信问他这是你的意见还是你老师的意见?如果你想给我找饭碗,那就不必,如果是你老师有这个想法,年纪大了,需要有人照顾他,我没有意见。”信去了之后,俞振飞亲自回了一封信给李蔷华,说欢迎李蔷华到上海来玩,最后彼此约在广州见面。
那一年是1979年,李蔷华52岁。
“我由我妹妹陪着,从武汉坐火车去的广州。结果一下火车,就看见俞老由正康陪着在火车站接我们。在广州,我们住在百花园饭店。进门俞老就剥一颗糖给我吃,也没有多的话说,就说哎呀这个事体要是成了,就是委屈你了,还说了两次。”说到这里,李蔷华抿嘴一笑。后来他们在广州玩了将近十天。百花园饭店的花园里,在一丛美人蕉的跟前,他们拍了第一张合影。那原本还是李蔷华的独照,临了俞振飞往她身后一站,说一起吧。
这张照片如今就搁在李蔷华家客厅靠窗的那条矮柜上,彩色的,放在所有照片的正中间。三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颜色也多少有些褪去,可是那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幸福感与满足感,却始终不曾被时光带远。
“后来俞老还给我写过一封信,谈起我准备调回上海的事情。他说,我们都这个年纪了,跑去拍结婚照怪难为情的,这张照片拍得很好,美人蕉前站着一个美人,要是能放大,就算我们的结婚照吧。”李蔷华拿着相片,边说边乐,“可惜这封信的原信被一家电视台要走了,后来就一直没还给我,我也忘了到底是哪一家。”不过她还是拿出了另外一封信,信里俞振飞用清丽的笔迹,口吻轻快地写道:“你也不要害怕,这是你我二人愿意不愿意的问题,他们爱怎样讲就怎样讲,前怕虎,后怕狼,也是白费,你说对吗?”
和俞振飞在一起的十四年,是李蔷华一生中最为舒心的十四年,“一开始也许是同情,后来就变成了爱情。”
“之前我从没管过家。从我懂事,就是学戏和练功。我就会学戏、看戏、唱戏,没进过厨房,连个鸡蛋都不会炒。在单位我倒是什么事情都做,但是家庭的事情我真的不懂。”可也正是这样的李蔷华,在和俞振飞结婚之后,却将这些生活上的事情一桩一桩的从头学了起来。为了能有更多时间陪伴对方,她拒绝了剧团的工作,而是呆在了戏校,因为“剧团有演出任务,而演出又都在晚上,我去演戏了,谁来照顾俞老?”
如果这都不是爱,什么才是呢。
2011年,为纪念俞振飞诞辰109周年,83岁高龄的李蔷华和俞振飞的学生蔡正仁一起,在天蟾舞台演出了程派名作《春闺梦》。这戏她与俞老过去一起演过。长达一小时的演出,唱腔、身段繁难,83岁的李蔷华在台上却是操控自如,拿捏有度。整出戏的末尾,她跑了一大圈圆场,接着站定下来,又气定神闲地唱完成套的二黄唱腔。
然而一下到后台,她就累得吐了,趴在桌上,久久缓不过来。过了整整40分钟,才抬起头,对周围的众人说了声“我活过来了”。尽管如此,李蔷华还是觉得很庆幸,自己终于以一出《春闺梦》,完成了对俞老最好的纪念。
附录:
俞振飞致李蔷华的一封信
(1979年10月俞振飞李蔷华广州见面分别之后)
云:
见到来信,如获至宝。我回沪后精神状态很好,这种状态发自内心,谁也猜不到的。你的两场“锁麟囊”都演过吧,我担心不知你这次的嗓子,和衷气,是不是和过去一样?希望来信告知。
我一定听你的话,在我们暂时分开的时间内,我一定把身体保养得好好的,你千万不要挂念。同时,你自己也要珍重身体,“粉”要每天吃,(你可能早已在吃了),不久我会寄给你的。因为这是上海雷允上产品,比较靠得住。
眼镜你已在给我配了,说明你每时每刻都在想到我,这是我莫大的幸福(带给正康转交可耳)。另外,你还在给我设法买煤油。现在正康打听到煤油可用侨汇购货券买,每两张买壹斤,这就可以放心了,你听到了也会感到放心。
深夜天寒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给我写信。我是带一张信纸在衣袋内,有时间,就给你写几句。你也可用这个方法。
今天《文汇报》上有篇稿子,题目是:“由方竹而想到的”。因给我的手杖是方竹,我拿到手里就认识(说明抽大烟也能长智识,哈哈!),我特地随函附给你看,这就是说,你虽然是竹,而是方竹,更是不同流俗,胸有一成不变之竹。
另外,今年九月29日文汇报有篇文章,题目是“俞〇〇和他的学生”,顺便附给你看看,作为消遣。
你我之事,因为我们那天一同去了“研究所”,这些“鬼灵精”已经看出苗头。结果,正康谈出了我们的问题,据说章力挥非常高兴,当天晚上就告诉了文化局长李太成,他也很赞成……据我看,你也不要害怕,这是你我二人愿意不愿意的问题,他们爱怎样讲就怎样讲,前怕虎,后怕狼,也是白费,你说对吗?一肚子话,说了一成也不到,恐你盼望,匆复不尽欲言。祝您
努力加餐!
龙
十一月廿六
——纪念俞振飞诞辰12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