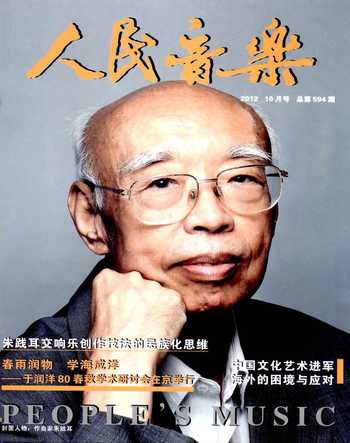交流创新,共促中韩音乐文化的繁荣发展
今年是中韩建交20周年。历史告诉我们,无论对于国家、民族,或者是对于单位、个人来说,建立友好往来关系,通过彼此之间的音乐文化交流,加进自身的创造性劳动,对于促进音乐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是十分有利的。同样,中韩友好往来的历史和现实,对此也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一、乐器和器乐的交流创新
中国与韩国的音乐文化交流大约始于西周初年(约公元前11世纪),有一位叫做箕子的人,被周武王封于朝鲜半岛;此后据《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汉武帝曾“赐鼓吹伎人”给高句骊。鼓吹是从中原西北地区兴起的一个乐种,由吹管乐器、打击乐器组成。结合考古发现可见,当时就有羽葆鼓、箫(排箫)、角、铙等乐器传到朝鲜半岛。
据晋代崔豹《古今注》记载,一位朝鲜半岛的女子名叫丽玉,创作了歌曲《公无渡河》,用箜篌伴奏,结合高句骊第17号古坟壁画中发现的卧箜篌演奏图可知,大约在公元前111年至东汉末年,卧箜篌就已传到朝鲜半岛。
“根据文献记载,高句丽时期的乐器有36种,其中21种见于中国吉林集安通沟壁画和朝鲜安岳(在今黄海道)的壁画(约4世纪)。这些乐器中有的是从中国中原流传过去的,如筝;有的是根据中国中原乐器改革发展而成的,如玄琴。”①
《北史》卷九十四对高丽的记述:“乐有五弦琴、筝、筚篥、横吹、箫、鼓之属。”《隋书·音乐志下》记载的高丽乐的乐器有:“弹筝、卧箜篌、竖箜篌、琵琶、五弦、笛、笙、箫、小筚篥、桃皮筚篥、腰鼓、齐鼓、担鼓、贝等十四种。”《旧唐书·音乐志二》和《新唐书·礼乐志十一》记载的乐器,又比《隋书·音乐志下》记载的多出了掐筝、凤首箜篌、义觜笛、葫芦笙、檐鼓、龟头鼓、铁板、大筚篥等。《北史》卷九十四《百济列传》记载的百济乐器“有鼓、角、箜篌、筝、竽、箎、笛之乐”。
以上这些乐器,有许多都是来自于中国中原,经过朝鲜半岛人民的创造性艺术劳动对之进行改造,而成为自己的富有特色的乐器,并且还逆向传播回中国,丰富了中国的乐器宝库。其中,伽倻琴的产生、发展及其返传中国,就是一个例证。
伽倻琴是流传于朝鲜半岛的古老民族乐器,其音色柔和,琴声深沉,具有浓厚的民族特有的文化风格、韵味,适宜于表达丰富的内在感情。伽倻琴的创制者据说是新罗真兴王时代(540—575)南方的加耶国嘉实王。其来源有两种说法:一是参照中国筝创制而成;一是参照中国的瑟创制而成。
韩国《三国史记》卷三十二载:“加耶琴,亦法中国乐部筝而为之。”“加耶琴虽与筝制度小异,而大概似之。”这是关于加耶琴参照筝而制作的说法。
中国《三国志·魏志·东夷列传》记载,与辰韩杂居的牟辰“俗喜歌舞饮酒。有瑟,其形似筑,弹之亦有音曲。”《后汉书·东夷列传》载:辰韩“俗喜歌舞,饮酒鼓瑟。”这是关于加耶琴参照瑟而制作的说法。
无论是筝,也无论是瑟,加耶琴所参照的原形都是中国乐器。朝鲜半岛的人们以他们创造性的艺术劳动,制作了适应他们音乐特点、音乐审美标准的乐器,创作了他们自己的伽倻琴乐曲。据《三国史记》卷三十二转引《新罗古记》云:“王以谓诸国方言各异,声音岂可一哉;乃命乐师省热县人于勒造十二曲。”由此可见,嘉实王认为,既然各国语言不同,音乐也应该不同,因此,他命令伽倻琴名师于勒创作十二首伽倻琴曲。于勒看到当时的加耶局势将要混乱,就携带乐器投奔新罗真兴王,真兴王命三人传其业,得十一曲,后又简约为五曲。伽倻琴由此流传后世,广为传播,并发展为古型风流伽倻琴和改造型散调伽倻琴两大类。风流伽倻琴也称法琴、正乐伽倻琴,被“正乐”(宫廷音乐)所使用。琴体由桐木刨槽而成,琴尾有羊角状流苏钩,称为“羊耳头”,弦数十二。散调伽倻琴用于散调、民谣、民俗乐,琴身比风流伽倻琴小,“羊耳头”自然盘于琴的尾部,弦数为十二、十三不等。
值得注意的是,伽倻琴于19世纪末,由朝鲜半岛传入中国的朝鲜族居住地区,于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珲春县和延边地区得以广泛流传,为中国人民和专业文艺工作者增添了一件有朝鲜族特色的民族乐器。还在延边艺术学校开设伽倻琴等朝鲜民族乐器专业,培养了一批朝鲜族民族器乐的教员和演奏员,并且在乐器改良和乐曲创作方面有了较大的突破。
在乐器改良方面,将伽倻琴传统的散调调弦法改成七声音阶调弦法;从筝的调弦法得到启示,将传统的拉紧梁尾进行调弦改为在琴的头部按装螺旋钮,用螺旋钮进行调弦;后又改为在琴的头部有可打开的盖,在琴的头部里面安装钢琴用的螺旋钮,用钢琴调音棒进行调音;弦数由十二、十三弦增加到二十一弦,音域扩宽为G—f2;混用不同质地的琴弦,低音部、中音部用丝线编成的传统琴弦,高音部用尼龙弦或钢丝尼龙弦。还借鉴中国汉族筝的演奏法,丰富了伽倻琴的演奏技巧。这种乐器的改良,大大丰富了伽倻琴的音乐表现能力。
在伽倻琴音乐创作方面,出现了《回忆与欢喜》、《瑶族舞曲》、《浏阳河》、《樱》等新创作的乐曲。
从以上伽倻琴由朝鲜半岛人民从中国的筝、瑟得到启示而创制,在当地人民的艺术实践中得以发展,返传中国以后,乐器改良、乐曲创作得以进一步推进,可以看出,伽倻琴是中韩音乐文化交流、两国人民共同进行伽倻琴艺术创新的结晶。
二、乐种、乐曲的交流创新
(一)箜篌引、鼓吹、乡乐
中韩两国见于史籍记载的乐曲交流,到目前为止最早的应推前曾述及的中国近代崔豹《古今注》记述的《公无渡河》,因其用箜篌伴奏,故称“箜篌引”,也就是用箜篌作伴奏的歌。
《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述高句骊县的风俗,“皆洁净自憙。暮夜则男女群聚,为倡(唱)乐。”汉武帝曾经“赐鼓吹伎人”给他们。这是中国中原西北地区吹打乐乐种传入该地区的记载。
统一新罗末期,出现了汉文大诗人崔致远(857—?)。在《三国史记》乐志新罗条的最后,载有“崔致远诗乡乐杂咏五首”,含《金丸》、《月颠》、《大面》、《束毒》、《狻猊》。据岸边成雄先生的研究,崔致远吟咏的五首五绝,“虽然可能是有关唐土的见闻,但如果是‘乡乐,就是在朝鲜音乐的三大类别雅乐、唐乐、乡乐中的乡乐。也许就是朝鲜的俗乐。”②岸边先生在分析了这五首乐曲的内容与价值之后,还指出:“通过崔致远的《乡乐五首》知道了关于西域的散乐是在新罗朝从唐土传来的,至少传来了关于这方面的知识。联想到推古朝时百济的味摩之,把在中国的吴地学的伎乐带来日本的事,不得不考虑在古代朝鲜唐土散乐传播的可能性。伎乐,从《狮子》、《关公》、《金刚》、《迦楼罗》、《波斯门》、《昆仑》、《力士》、《太孤》、《醉胡》的九伎而成,只看其名,也是西域色彩浓厚。不可能认为味摩之在百济没有上演这些。”③
据《三国遗事》中记载的十四首乡乐看,用汉字来记录朝鲜语歌词,即用新罗学者创制于692年的“吏读”文字来记录乡乐;以“风谣”为主的新罗乡歌,在6—8世纪得以广泛流传;乡乐以外的唐乐是从唐代开始传入的中国宫廷俗乐。这些都说明,新罗在努力吸取中国音乐文化来发展自己独特的音乐文化。
(二)国伎、高丽伎、礼毕
正是由于当时朝鲜半岛人民在吸收借鉴中国音乐文化有益成分的同时,勇于开拓创新,所以,使当时的朝鲜半岛音乐得到了飞跃的发展,到中国隋末唐初(约七世纪左右),高丽乐、百济乐大量反传中国。
据《隋书·音乐志》载,隋文帝“始开皇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曰《国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④及大业中,炀帝乃定《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以为九部。”⑤其中的《国伎》、《高丽》、《礼毕》以及百济、新罗等伎,都是来源于朝鲜半岛的音乐。尤其《礼毕》是用在所有别的伎乐表演结束时,作为最后上场表演的压轴戏。在中国,压轴戏是最精彩的终场节目的代称,可见当时的百济乐的艺术性之高。
然而,中国人并不停留在对这种以地区、国家为名的七部伎、九部伎、十部伎的运用和欣赏,而于唐天宝十三年(754)将它们改变成按演奏形式命名的立部伎、坐部伎,成为融合雅、胡、俗三乐而成的一种新的礼仪乐,使九部伎、十部伎中国化,使中国的中原音乐与朝鲜半岛音乐、西域音乐等相互交融消化,形成面貌为之一变的、与原有传统音乐既有紧密联系又多有发展、艺术性更高的“新乐”。
(三)雅乐和词乐
在相当于中国宋(960—1279)、元(1271—1368)两朝的高丽王氏王朝(918—1392),以佛教为国教,大量吸收中国的文化和典章礼制。在音乐文化方面,宫廷音乐大量采纳宋朝的雅乐,并且吸收宋代的词乐。
中国的大晟乐于北宋传入高丽。据《高丽史·乐志一》载,高丽睿宗九年(1114)六月,信使安稷崇将从宋朝回国,宋徽宗曾下诏赐予乐器171件、曲谱10册,乐器演奏用“指决图”10册,以适应高丽王朝宫廷宴乐之需。其后两年(1116)六月,睿宗派王宇之前来中国致谢时,徽宗又赐“大晟乐”乐器、服装、仪仗等。据宣和六年(1124)出使高丽的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载,由于北宋多次赐予乐器,高丽王朝仿照中国宋朝建立了含堂上乐登歌与堂下乐轩架(轩悬)的宫廷“雅乐”演奏形式,成为唯一从中国吸收宫廷雅乐的国家。但是,高丽宫廷中的仪式音乐、祭祀音乐并不是中国雅乐的原样照搬。据《高丽史·乐志二》记载,“祀圜丘、社稷,享太庙、先农、文宣王庙(孔庙),亚、终献及送神,并交奏乡乐。”也就是说,乡乐与唐乐交相演奏。在用宋朝吸收来的音乐作为祭祀乐时,歌词是歌颂王室功德,曲调却用中国俗乐。这些都表现出高丽人按照自己的理解,对宋代祭祀音乐进行改造和创新。
中国词乐于高丽王朝时(918—1392)传入朝鲜半岛。《高丽史·乐志二》记载的词乐存目和歌词达40余首。其中,在中国常见的词调名称有:“《瑞鹧鸪》、《抛球乐》、《惜奴娇》、《万年欢》、《感皇恩》、《醉太平》、《醉蓬莱》、《清平乐》、《水龙吟》、《倾杯乐》、《太平年》、《千秋岁》、《汉宫春》、《花心动》、《雨霖铃》、《浪淘沙》、《西江月》、《挂枝香》、《临江仙》等;在中国比较少见的词调名称有:《献仙桃》、《天下乐》、《行香子慢》、《金盏子》、《风中柳令》、《荔枝丹》、《爱月夜眠迟慢》等。”⑥至今仍存乐谱、由韩国国乐院继续演奏的有两首:《洛阳春》和《步虚子》等。据宫宏宇先生介绍,英国学者毕铿(Picken)的弟子康德特(Jonathan Condit)曾对中国词乐在韩国的流变作过研究?熏“他不但译谱子,而且为《洛阳春》和《步虚子》制成复员(原)再现谱。为了追溯这两首小令的流变过程,他还从一些重要的韩国文献中找出相关谱例和有关文字资料来对比印证。他的结论:《洛阳春》和《步虚子》虽然发源于中国宋代,但是到16世纪时其旋律与节奏已完全高丽化了。不但旋律线中增加了很多装饰音,节奏上也进行了扩展,由4/4拍变为朝鲜人比较喜欢的12/8拍。”康德特认为:宋代词乐“在韩国流传的五百多年间,经过了两种演化过程:一种是韵律上的扩展(metrical expansion),一种是节拍节奏上的均一化(rhythmic equalisation)。也就是说,从宋代流入的词乐,最初的旋律结构要比现在简单的多,演奏的速度也比今天的快。虽然其骨干音仍旧存在,但经过后世的加花变奏以及节拍变化,整个旋律结构都已完全韩国化了。”⑦由此可见,韩国人在对中国宋代词乐的吸收运用过程中,也是加进了自己的艺术审美、文化体验和艺术创造,而使之“韩国化”了。
三、音乐理论的交流创新
在中韩音乐理论的交流创新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有:成伣《乐学轨范》和儒学理论与儒家音乐思想的继承发展。
(一)《乐学轨范》
韩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音乐理论专著《乐学轨范》,是成伣于朝鲜李朝初期,受成宗(1469—1494在位)之命编撰的。成书于1493年。全书共9卷,广泛吸取了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成果,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展现了朝鲜半岛的古代音乐历史、音乐理论和音乐规制。其撰著的缘起,是由于当时“乐院所藏仪轨及谱年久断烂,其幸存者亦皆疏略讹谬,事多遗阙。”因此,成宗命成伣和柳子光、申末平、朴昆、金福根等,进行雠校。“先言作律之原,次言用律之方,及夫乐器仪物形体制作之事,舞蹈缀兆进退之节,无不备载。书成,名曰《乐学轨范》。”⑧
《乐学轨范》的“序”、卷一、卷六,引用了多种中国古代典籍,如《吕氏春秋》、《礼记·乐记》、《荀子·乐论》、《史记·乐书》、《汉书·律历志》、《周礼》、《周易》、《宋史》、陈旸《乐书》、蔡元定《律吕新书》、马端临《文献通考》、王应麟《玉海》等。还从《三国史记》和《高丽史》中吸取养分。其中关于音乐感化人心的社会功能、排斥郑卫之音和君王的引导作用,与中国古代的音乐思想一脉相承。但是在对待本民族的音乐传统方面,提倡尊重高丽王氏王朝以来的实践,将本国音乐分为用于祭祀场合的雅乐,奏于朝会宴飨的唐乐,习于乡党俚语的乡乐,用图文结合的形式对雅部、唐部、乡部所使用的乐器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其律制思想和律制计算在介绍中国传统五行说、按月用律和三分损益法、陈旸反对“四清二变”音乐理论的同时,还从实际出发,主张:“我国用律,雅乐则用七声,俗乐则不用二变,只使五声”,“按我国用乐之声,雅乐则用十二律正声及四清声;俗乐则用十二律正声及十二清声。”⑨记录了当时的雅乐陈设、俗乐陈设、《高丽史·乐志》唐乐呈才、《高丽史·乐志》俗乐呈才、时用唐乐呈才图说、时用乡乐呈才图说、雅部乐器图说、唐部乐器图说、乡部乐器图说、唐乐呈才仪物图说、莲花台服饰图说、定大业呈才仪物图说、乡乐呈才乐器图说、冠服图说、舞童冠服图说、女妓服饰图说等,成为富有民族特色、时代创新的有关高丽王氏王朝的音乐礼仪轨范、乐律、乐理、乐调、乐曲、记谱法等方面的音乐百科全书,成为集大成之作,对后世起了重要的影响。
(二)儒学理论和儒家音乐思想
韩国作为汉字文化圈的一个重要国家,曾经长期使用汉字,接受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中国文化的影响。对于这方面的情况,笔者曾在《世界民族音乐》中做过如下论述⑩。
大约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韩国就已吸收中国的文化:汉字、儒家经典和阴阳五行学说。公元936年建立的独立的高丽王朝,采取中央集权和科举考试制。从那时起,直到1905年沦为日本的殖民地,韩国文化一直与中国文化同步进化。
儒家思想在韩国始终占据正统的地位,并得到朱子学大师李湟的推动。到17世纪,情况才发生变化,韩国开始强调研究现状和实用技术的“实学”,出现了一位大学者丁若镛。随着整个东亚地区发生的变化,韩国也在经历变革。当评论家讨论“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成就时,他们往往强调中国传统文化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有些学者甚至称之为“儒教工业文明”,因为传统的儒家文化和理论范畴仍在发挥调节人际关系、增加凝聚力和提高生产效率的作用。韩国的宗教信仰已经多元化了。儒教虽然已经丧失统治地位,但并没有完全被放弃,韩国至今仍有八百余座文庙,供奉着大成至圣先师,每年都举行盛大的祭孔活动,续家谱和祭祖等其他儒家传统也被保持下来。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基督教教堂在这一地区建立起来,许多知识分子和大学生阅读《圣经》。社会价值观也渐趋多元,西方的物质主义和个人自我实现等价值观念已在许多人心里扎根,但是儒家的重视家庭和教育、积极入世、勤劳节约等价值观念仍在韩国发挥着作用。
以上这些中国儒家文化在韩国的影响及其创新的情况,同样也存在于传统音乐领域。在与韩国的长期友好交往中,这些音乐美学观、传统音乐种类、音乐形态特征,也曾被他们有选择地吸收,并施影响于韩国音乐。但与此同时,韩国人民又根据自己的社会生活、文化观点进行了变化、改造,造就了自己国家、民族所特有的音乐种类、体裁形式、音乐形态特征和音乐美学观。尤其韩国人民在坚持音乐主体性,热爱、传承和弘扬自己的民族音乐,以此作为陶冶美的心灵,增进民族感情,增强民族心理凝聚力的纽带方面,在世界各民族、各国家的音乐界中做出了良好的榜样。他们一方面积极致力于国际间的音乐文化交流与合作,广泛吸收人类音乐文明所创造的优秀成果,提倡理解和尊重世界音乐文化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又坚持民族主体性,坚持传承和弘扬民族音乐,使民族音乐得以永续不断的发扬光大。
回顾历史,中韩人民友好往来,交流创新,共促音乐文化繁荣发展;展望未来,中韩人民携手并肩,合作开拓,共创音乐文化新的辉煌!
参考文献
[1]晋代崔豹《古今注》。
[2]《北史》卷九十四“百济列传”。
[3]韩国《三国史记》。
[4]中国《三国志·魏志·东夷列传》。
[5]《后汉书·东夷列传》。
[6]《隋书·音乐志》。
[7]韩国《高丽史·乐志一、二》。
[8]成伣《乐学轨范》。
[9]冯文慈主编《中外音乐交流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0]岸边成雄《古代丝绸之路的音乐》,王耀华译,人民音乐出版社,1988年版。
[11]宫宏宇《韩国及欧美学者对流传在韩国的古代中国音乐的研究》,《中国音乐学》2002年第3期,第93—104页。
①冯文慈主编《中外音乐交流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7页。
②岸边成雄《古代丝绸之路的音乐》,王耀华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8年版,第152页。
③同②,第156页。
④王耀华、方宝川主编、郑俊晖执行主编《中国古代音乐文献集成》第一辑第二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版,第315页。
⑤同④,第317页。
⑥同①,第139—140页。
⑦宫宏宇《韩国及欧美学者对流传在韩国的古代中国音乐的研究》,《中国音乐学》,2002年第3期,第103—104页。
⑧⑨成伣纂辑《乐学轨范》,古典刊行会1933年发行,第2页。
⑩王耀华、王州《世界民族音乐》,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王耀华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荣英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