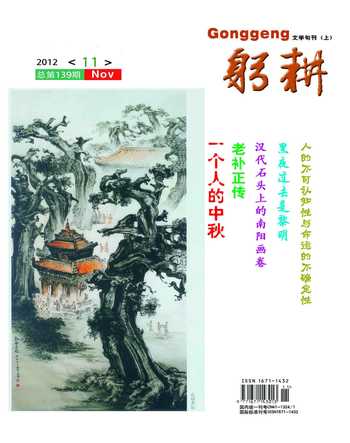书事
罗萧
那年我十四虚岁,有次去称勾赶集,用知了皮换取二十枚分币,拿出一毛二分钱买了本《越南少年抗击美国佬的故事》,回到家早错过午饭时间了,肚子饿得咕咕叫,又不敢跟娘说实话,最后去西院掇开爷爷的小屋门,把箅子里几个薯干面窝头全塞嚅着吃了。爷爷知道后心疼得说不出话,似有泪花在眼眶内打转。
另有一次,兜里装着姐姐卖草帽辫后赏给我的一毛五分钱,坐不住了,趁午休趟过漳河到苏村供销社图书角买了本《张思德的故事》。回家后使劲想,到底也没想出供销社柜台里面有什么玩具,敢情,脑瓜全让图书给占领了。
上初中时我跟爷爷在西院那个低矮的小屋住,书籍随着年龄增添,炕头墙上那个不大的墙窑快摞满了。夜里我读《林海雪原》《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红岩》《红日》《红旗谱》《平原枪声》《烈火金刚》《暴风骤雨》等,煤油灯滋滋啦啦烧出烟雾,将周围的空气涂抹得一滩糊涂。爷爷坐在小桌旁,我看书,他看我,鼻窟窿也被熏黑了。
高中毕业后我当了民办教师,除生产队按棒劳力补给工分外,国家每月发五元钱津贴。那时一元钱就能买一只烧鸡呐!我把第一个月的津贴全用于解书馋了,步行二十余里去县城新华书店买了孙梨的《铁木前传》、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刘真的《三座峰的骆驼》。
然后我考上了地区财贸学校,然后毕业进入粮食系统工作,七零八落在报刊上发表一些嫩豆腐块似的诗歌,甚至有作品上了《人民日报》《河北日报》以及十余家文学期刊。然后到了1988年3月,我成了作家,因为手里有了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证。这都沾读书多的光。书虫子吃进的是书卷气,吐出的却是渊博的知识。我走马观花浏览过许多书,少有倒背如流以及念念不忘的,偶有所思演绎成铅字,也算小有斩获吧。
2002年仲秋去石家庄鹿泉疗养院参加《诗选刊》编辑部举办的“金秋诗会”,有天夜里在浙江诗人庄晓明住处闲聊,眼睛不由为之一亮。我看见了以下几本书:《切·米沃什诗选》《耶胡达·阿米亥诗选》(上、下册)、《保罗·策兰诗文选》《卡瓦菲斯诗选》。自己逛过的书店书市可谓不老少,怎么从没见过这些书呢?我赞不绝口,近似于唠叨。庄晓明时任山东某市某大公司总经理,何等精明样人,说罗老师如果喜爱的话,尽管拿去,我路过南京再买一套。这才是刚瞌睡就有人递来了枕头,我喜出望外,当即合算一下,给他七十元,悉数将五本书收归已有。坐在回邯郸的火车上我沾沾自喜,此次石家庄之行最大的收获当属这几本书了
2004年夏末往市里搬家那天,纸箱满登登装了三十只,一些期刊因年代久远,纸页已经发黄,儿子边拾掇边嘟囔,觉得是累赘。再说邯郸那边的两室一厅地方太窄小,无奈只好当废纸卖,六毛钱一斤,换得钞票一百六十六元,感觉却像割掉了身上的肉,个中恋恋不舍之意,外人概莫能知。
买书的事情依旧计划并落实着。因为买房导致手头拮据,不得已缩减为每月只花十元钱用于买书。我老去旧书市场或盗版书市溜达,鬼才晓得爱书情之切,勉为其难之窘迫况味。平淡中也会迸溅浪花,那天我掏一元钱购得一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乐得只想跳高。
为生存计,我当起了“坐家”,大量写作小说、诗歌、散文以及文学评论文章。稿酬单零零星星飞来,水涨船高,买书量随之递增,并且订阅了《长篇小说选刊》《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人民文学》《散文选刊》《美文》《小品文选刊》《百家故事》等期刊。有所吸取才能有所挥洒,春种秋收,点瓜得瓜,点豆得豆,书事与农事是否雷同?
再说刚搬进市里那会儿,我虽久居下边县城,参加市文联召开的文学创作会却年年有之,与市里一帮知名作家、文学爱好者大多熟识,听说安了新家,隔三岔五难免有人闹着要来暖房,孬烟赖酒粗茶淡饭招待自然是难免的,让我内心不舒坦的事情居然是书。
穷酸这个词,用在历代文人身上,最合适不过了。虽穷,仍不舍那个酸字,仿佛一股气,才气,志气,雄心勃勃之气,盘桓萦绕,经久不散。外表光光面面,言谈文质彬彬,脖梗儿长颈鹿般抑扬顿挫,内里却是蛤蟆支桌子硬撑着。试想,好多人将有限的收入全部用在房子孩子上面,尚显得捉襟见肘,哪儿敢奢望买书啊!缺者为贵,贵者为尊,难免让人惦记。
明借者有之:这类人显得特文明,语气也是那么毋庸置疑。我初来乍到,只能递上笑脸,说拿去看呗,看完再换别的。其实我是想以委婉的方式提醒对方切记归还。但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的事经常发生。别去要,要也是白白伤失和气。一本书能值几个钱,因之掐断一条路,太不值得,太不划算,太小肚鸡肠了吧!但并非没张口要过,尤其旧版本,休想再去买,早被新浪潮给淹没了,又急着想再看看。出门前,我准备好了理由:刚好路过;数月不见,想老朋友了,专程来看看;或曰,咋,咱就不能蹭顿饭,赖盅酒喝?一捱问起那本书,回答者情状各异:还没来得及翻呐;不好意思,大老远的,让您又跑一趟;瞧你这小气劲儿,怕昧了还是怎么着?也许某句话一并代表了闷在肚子里的几层意思,我耳闻目睹着,嘻嘻哈哈着,味同嚼蜡。
有个叫肖伟的文学小青年来我家串门,见桌上有一本《中国当代小小说精选》,翻了翻,爱不释手,提出借阅几天。我说刚买的,还没顾上看呢。肖伟说,反正是您的,以后有的是机会看。我说,书店里有,不贵,才五块钱。肖伟说,懒得买。我说,别介懒得写呀!肖伟面色里泛出些许的尴尬,痞着嗓音说,罗老师,按我的想象,作家应该是些宽宏大量的人,用个不恰当的比喻,你们是富翁,我一个小小文学爱好者,形同乞丐,但乞丐也是有自尊的呀,张口容易闭口难,不就一本书嘛,又不是金子,值得这样拿捏?瞧我犹豫不决的样子,肖伟又说,我只借两天,四十八小时后定当归还!之后肖伟不再露面,也没见哪家报刊上出现过他的大作。那本书无须归还,因为我在两个月后去望岭路书店重新买了一本。没有这样借东西的,还真有这样借东西的。对于书籍,我的原则是,尽量不借,借则好借好还,再借不难。
暗拿者有之:小字辈小就小在金口难开,心里又实在抵挡不住某本书的诱惑,趁我进卫生间或在厨房忙碌或扭脸和别人说话的当儿,怀里可揣,腰里可掖,提包里可塞,某本书不翼而飞。我从未怀疑过自己的记性,又不得不怀疑自己的记性,不得不采取相应措施。譬如将书橱上锁,九把锁,九把钥匙哗啦哗啦响,显得特俗。有一阵子,我就那么哗啦哗啦出门,像个仓库管理员。后觉不雅,只挂一把,其余八把归这把掌管。
然而,书却照丢不误,究其原因,竟出在常来常往的亲戚们身上,这真是出乎预料。某些不爱文学的人,不见得不爱书,现实生活中,把故事当消遣,把小说当催眠剂,满口之乎者也,不是秀才的秀才屡见不鲜。理论性的那些石头似的大部头很少有人愿啃,而鲜橘、蜜柑之类的甜点又当别论,譬如《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古今传奇》《故事会》等等,别往床头放,放就意味着放在了别人手上。单说《三国演义》,我买过四回,至今无有,还得再买。
有一天我打通了侄子的手机,问那本《黑雀群》。侄子说,下次带去。侄子半年后才来,只带着影子,里面不见有什么《黑雀群》,他与某些人一样,压根儿没把我不厌其烦的叮嘱当回事。
然后,我给自己的书房兼卧室安了暗锁,随走随碰门,有客来兮第一要紧的就是碰门,碰书房的门,把尊贵的客人往穷徒四壁的客厅里让。砰!砰却砰出连锁反映,就有一张接一张的冷脸子,释放出闲言碎语,忒清高了吧!忒小抠儿了吧!拜访者随之锐减,正所谓“门前冷落鞍马稀”。
肖伟二番来找我,说近作一篇微型小说,想请老师向熟悉的文学期刊或报纸副刊推荐一下。我说尽力而为吧,如果您的作品颇具功力,有一定档次的话。肖伟拿出了那本书,说对不起啊,本当及时奉还,因事务缠身,延误至今。我说不必还了,这样,我签个名,赠给你得啦!我没说三年前又买一本,时过境迁,何必捅破那层窗户纸呢。
五年前我搬回了乡下老家。远离尘嚣日久,似乎寂寞惯了,又似乎从未寂寞过,有那么多书籍晨昏相伴,不想自得其乐也乐在其中了。越读越写越觉得沉实,淡泊,宁静,别有一番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