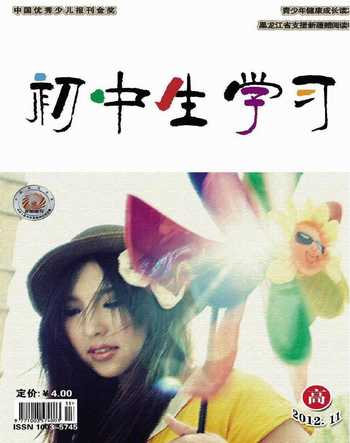鸟类也懂物理学
卡尔
地球上的生命是生物学研究的核心内容。维持生物生存的机制和过程都属于生物学范畴。其实,我们人类也生活在物理的世界里。生物学必须要承认物理世界的规律,并且要找到应对物理规律的方法。比如,大象的腿比人的腿粗壮,那是因为它要支撑起沉重的身体,使之不至于在地球重力的作用下轰然倒地。飞蝼蛄不需要粗腿,因为它关心的不是重力,而是风力和空气,这两者决定了其在自己的世界里如何移动。
这些物理事实常常决定了一种生物最终进化而成的外形,这种外形让它能够充分利用环境提供的机会。不仅如此,物理事实还决定了生物的行为方式,反映出它们对这个日常世界的物理现象的认识。
红颈瓣蹼鹬属于涉禽,喙又细又长,以微型甲壳类生物为食。它利用所在的水生环境采取两种办法捕食,十分有趣。我们经常可以看见这种鸟在水里紧兜小圈子,每过一秒就将喙点进水里一次。它们是要在水下制造漩涡,漩涡可以搅动河床或湖床,把食物翻卷到水面附近,它们就可以顺势把食物捡出来了。
其他一些水鸟,待收集了少量含有食物的水之后,会透过类似滤网的东西将水吸进嘴里,篦出食物。而红颈瓣蹼鹬则是从水里“啄”出食物,然后用长长的喙的尖部一点点地夹食物,像针嘴钳一样。有很长时间,科学家并不知道逮水鸟是如何把捕到的食物顺着细长的嘴一路送进喉咙里吞咽下去的。有的水鸟会向后猛甩一下头,利用惯性把食物“扔进”喉咙深处。但瓣蹼鹬的食物太轻,甩头吞咽是不行的。于是,它们似乎专门挑选不超过一定分量的甲壳类食物来吃,尽管谁都知道,猎物越肥大,吃起来越惬意。
含有甲壳类食物的一小滴水从瓣蹼鹬细长的喙尖一直被移动至喉咙吞咽。有些长喙鸟类靠吸或用舌头来完成这个动作。但是瓣蹼鹬既不靠吸,也不用舌头,而是靠表面张力——液体表面都会有张力,置于固态表面上时,表面张力就会使液体形成滴。
雨滴和窗户玻璃之间有表面张力,如果雨滴不太大,则其边缘的张力就会将它附着在玻璃上。同样的道理,如果瓣蹼鹬的嘴张得不是很大,一滴含有甲壳类食物的水就会“粘”在它的上、下颌的表面上。瓣蹼鹬要想把这滴水顺着喙送进去,就会先迅速张开喙,再非常轻地合上喙。一开始水滴散开,离喉咙最近的那部分水随着喙的轻微开张而向后移动,最靠近喙尖的水跟着向后移,当喙再次合上时,整个水滴就被包住了。含有食物的水滴沿着喙被迅速向上传送,速度可达每秒1米。
在瓣蹼鹬的进化和水的表面张力的交互影响下,有几样东西不知不觉就进化到了最适合这种特殊觅食方式的程度。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喙的表面形状,喙表面的物理性质正好具有“易湿性”,以适应水滴移动的需要,喙的几个固定动作——鸟儿靠它完成水滴的移动,鸟儿对猎物大小的固有感觉,多大的猎物可以轻到能在表面张力的作用下移动……所有这些都是历经千万年进化而来的。
这个例子很小,但它说明,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如何以最佳的方式“调适”一种动物,让它在特殊的环境里生存下来。